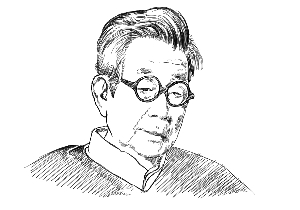
大江健三郎80岁了。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个年龄似乎足够老,更何况,这位日本小说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在21年前——他也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当然,即便年事已高,他写作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
2012年,随笔集《定义集》由朝日新闻出版。
2013年,讲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晚年方式集》。
2015年,新潮社出版了他和古井由吉的合著《渡过文学的深渊》。
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大江健三郎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日本文学的符号,代表了日本文学的某个维度——毫无疑问,他是日本现代文学和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日本文学中少数几个世界“通用”的作家。
大学期间以作家身份出道
如果你感到哪本书实在是一本好书的话,那么就请隔一段时间重新读一遍,而且每遍,都用不同颜色的彩笔画上线,在空白处记下阅读时的杂感。这是一种有益的读书方法。
——《在自己的树下》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生涯,开始于他在东京大学求学的1957年。
在这一年,《东京大学新闻》上刊登了大江健三郎的五月节获奖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奇妙的工作》。同年,他在《文学界》杂志上发表了《死者的傲气》,这本书获得了第38届芥川文学赏候补,川端康成称赞小说显露了作者“异常的才能”。
大江健三郎自此以作家身份出道。
也是在这一年,一位天才摄影家土门拳在《朝日相机》杂志上以“日本艺术家”为标题刊登作品连载,选中了水谷八重子、杉村春子等。在这个系列中,土门也希望拍摄大江健三郎的肖像照,“我很为难……据说土门先生众所周知,人们会认为我不尊重他……他来到我的宿舍,看到我之后表情变得极其忧郁。但很快,他说,‘我想看你的书房’。虽然说是书房,其实只是房间里的书和桌子。在书架上,排列着小说家中野重治和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几乎全部的书。土门先生的心情被修改了,‘中野重治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渡边一夫的书,你为什么会摘译这些?’于是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出生在四国的森林里,高中一毕业就被森林工会预订雇用。但渡边一夫先生《法国文艺复兴断章》一书让我想要去跟随他学习。我回去说服母亲,来到东京,终于可以去渡边先生的教室。不过,我不想成为学者,所以我开始写小说……’然后土门先生为我拍照片,这个事情告一段落……这也应该是土门拳先生和我最初的相遇了。”
重要的问题即使折磨人,也应该认真去思考,并且这种思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但曾经拿出时间对它认真加以思考本身,会让你在将来想起它的时候,懂得它的意义。
——大江健三郎
父亲为孩子
“清除荒地”
1935年1月31日,在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大江好太郎的第四个孩子大江健三郎出生了。大濑村坐落在森林和峡谷之间,这里的习俗和环境对后来大江健三郎文学世界的形成影响颇深。
当然,对大江健三郎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的父母。大江健三郎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生在这样一个庞大而贫穷的家庭,难免让大江健三郎觉得气馁。很小的时候,他就说:“我在这样的森林里面长大,注定成不了什么有名的人啊。”然而,这样的话语并没有让大江健三郎的父母对他感到气愤或者失望。母亲向他讲述了邻镇的学者江藤树如何在穷困中坚持学习,父亲在第二天就带他前往邻镇,实地感受江藤树生活过的地方,在那里吃着好吃的东西,讲着藤树先生的故事。大江健三郎说:“我的父亲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为我清除着‘荒地’。”当大江健三郎说,自己不可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勇敢时,好太郎告诉儿子“孩子不是应该有孩子的战斗方式吗”。
大江健三郎十岁那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很快,学校的教育理念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让大江健三郎非常不解。厌倦了上学的大江健三郎拿着植物图鉴跑进了森林,希望能够认识植物,以便将来“世袭”管理森林的职责。遗憾的是,大江健三郎在森林中迷路,直到三天后才被发现。当时他高烧,医生宣布他已经没救。在母亲不懈的努力下,大江健三郎转危为安。他曾经问母亲他会不会死?母亲回答说:“你不会死的……要是你死了,我也可以再生你一次……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孩子。”
在一生中延续乐观主义
考虑问题的时候,我用日语,也用英语、法语等,它们一齐在我面前晃动。语言是不断运动的,我从其中创作文学。如果说我不拥有日本的传统,那么我一定拥有法国与英国融合在一起的传统;如果说我是国籍不明的人,那么我是生活在地球上创作文学的人。
——大江健三郎
相比于一个作家的身份,大江健三郎更多在做的,是导引者和宣传者。无论是对战争的思考,对子女的教育,还是对青年人的指引。
2006年,大江健三郎在京都律师会的一次集会上回忆了自己高中时代的“自作聪明”,希望能让今天的年轻人有所借鉴。“高中一年级时,在盛行棒球的农村中学里,棒球部胡作非为——至少在我看来,老师们装作不知道,学生们也都在默默忍受。我写了一篇作文,希望他们可以停止‘胡来’。我原本只是想在班级里引起关注,没成想有人将其誊写印制而且到处散发,我因此成了被‘暴力制裁’的对象。每天午休时,我都会被叫到学校后面,这种苦难一直持续着。我不得不假设‘自己没有每天都被殴打就好了’。”这种恶劣的情况加上老师的嘲笑让大江健三郎决心反抗,“决心显示出即便被殴打也绝不屈服的勇气”,这样的坚持虽然让打击报复更加恶化,却为大江健三郎带来了支持者,“其他教师甚至为我联系了转学的学校”。
步入老年的大江健三郎说:“我已经进入了老年。自己原来做过的事情,比如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核武器,或者帮助有障碍的孩子自立,又或者讲述自己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现在的我可能说不出口。但我不知不觉进入了晚年,还有什么是我可以解决或者考虑的呢?人做事情就希望它能够朝好的方向前进,我从内心里希望和相信美好,我会尽力而为。我们将乐观主义的精神在一生中延续下去,我带着这样的心情,考虑自己的文学创作。”
北京晨报记者 何安安 综合编译
无论怎样控诉恐怖、怎样发怒都没有成效,(作家)却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发出声音……也许明天,愤慨多少沉潜下去;后天,重又开始控诉恐怖,而他将选择黯然沉默,恢复往昔的日常生活。然而,侮辱是一股酸性侵蚀力量,它在自己的内心深深挖掘着伤痕,无止无休。
——《冲绳札记》
孩子为什么上学
25岁那年的 2月,大江健三郎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婚。
“不久我结了婚,生了孩子。那个孩子有智力障碍。我认为这是我人生非常黑暗的时候,无论如何,和这个孩子一起活下去。”为了找到信心,在广岛遭受核打击后,大江健三郎去了广岛。他在那里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创作《广岛笔记本》。也是在广岛,他接受了医生的建议,“作为父亲的你必须接受他,尽量拜托其他医院进行治疗”。这次工作结束回到东京后,大江健三郎接受了手术治疗方案,“然后,我和我的爱人、孩子三人的生活开始了”。
在大江健三郎的其他描述中,有更为详细的介绍:“我的长子出生时,后脑勺有一个看上去和脑袋差不多大小的包。医生把它切了,尽可能使大脑不受影响……光很快长大了,只是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相反,他对声音的高低、音色的厚薄特别敏感。比起人的语言,他首先记住的是许许多多鸟儿的叫声;而且他一听到鸟的歌声,就能说出鸟的名字来。鸟的名字,他是从唱片上学来的。这是光说话的开始。”大江光7岁开始上学,进入特别班,“集中在那里的孩子,身体上都有不同的残疾……从窗户望进去,看到光总是用手捂着耳朵,身体呈现僵硬的姿态。”这让大江健三郎对教育产生了怀疑,已经是成年人的他又问自己孩童时期的那个问题:光为什么一定要去上学呢?他一度想要带着孩子回到村子里,“解决了这个摆在我面前的难题的竟然是光”,光在班里发现了一个同样不喜欢噪音的孩子,渐渐的,他们可以一起听广播里的古典音乐了。
在结束了智障孩子的学习教育以后,从小跟随母亲学钢琴的光,已经可以自己作曲了。大江健三郎把这段经历写进《孩子为什么上学》一文里,通过他与儿子大江光的经历,讲述了上学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