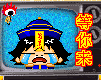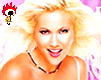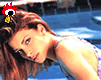| 江南小镇上市公司云集 “杨汛桥现象”大揭密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2月03日 12:02 南风窗 | ||||||||||
|
2003年,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测算,浙江绍兴在全国百强县中位列第八,而杨汛桥镇,在浙江的百强镇中排名第一。正是在这个江南小镇中,涌现出10多家民企上市公司,这在全国绝无仅有。 “杨汛桥现象”不仅是一部财富的成长史,也是一部规则的变迁史。从潜规则的环境中挣脱出来,引入更规范的制度力量。这一过程中,当最有实力的政府与企业两大层面开
新样本 “如果运气好,展望集团在去年12月就已经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了,绿洲生态农业紧跟着就在今年,而精工科技2004年排队在内地A股上市……”2003年12月19日深夜,杨汛桥镇主管工业的副镇长唐东华一边应付着县里打来的要求检查用电线路的电话,一边如数家珍地对记者说。 杨汛桥,这个位于浙江绍兴县西北部的普通小镇,在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已经声名鹊起。自从2001年12月,“浙江玻璃”一举登陆香港H股,在1年半的时间里,前后有3家杨汛桥的民企登陆香港股市。另一家企业,在国内控股了两家A股上市公司。紧随其后的是数量可观的“后备军团”。 在浙江省农村经济调查队公布的浙江省百强乡镇排行榜上,杨汛桥镇迅速攀升到第一名。上市让这个只有6万人口的浙江小镇迅速闯入主流的财经世界。人们惊呼的“杨汛桥板块”、“杨汛桥现象”横空出世,被视为浙江民营经济的“新亮点”。 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能够预示杨汛桥能够达到今天的高度。 在绍兴“三大”全国知名的品牌—黄酒、“鲁迅”、轻纺工业和纺织业市场中,杨汛桥曾经都不占什么优势地位。即使到今天,以产业背景而言,整个绍兴仍是一业特强,轻纺业知名天下,为整个产业的80~85%,但相当有意思的是绍兴的非纺产业主要集中在杨汛桥。在绍兴,其轻纺业以1997年轻纺城在A股上市,成为一个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但这一高度4年之后就被杨汛桥的企业集体性地超越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其喷发了中国民企迄今为止最为迅猛炽热的上市火焰? 在以上市为火山口的“喷发”之前,这里蛰伏的是民营经济几乎20年的积累。但所有的事实都在表明,这是一道历史的分界线。它所标定的是民间经济力量,从混沌走向清晰,从边缘走向主流的坐标。 两次改制 让杨汛桥从边缘杀入主流,一个重要的原点是20多年前,一批杨汛桥的木工和泥瓦匠被铁道部武汉大桥局招工到武汉搞建筑。 那些第一次乘坐火车,经过上海,到武汉闯世界的杨汛桥农民建筑工,返乡后,80年代初,开始在杨汛桥自己创建企业,或者参与乡镇企业的创办,摇身变为“红帽子”企业家;整个90年代再变为开始“赎买资产”的半集体半私营的企业家,最后变身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国内A股市场上令人惊异的民间力量。 这样复杂多样的变身催生的“裂变”,留下两个相反方向的线脉:一方面是民企在“集体”的面具之下,不断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今天,在杨汛桥大名鼎鼎的企业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前身。杨汛桥的企业群落以建筑起家,而后又裂变出众多的企业,曾闯荡武汉的人们,进入了许多自己根本不熟悉的行业,起起伏伏,形成了一个企业群落。 从1993年发端的两次改制贯穿了90年代。在长达10年的政经互动路线下,不断摘下“红帽子”。绍兴县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两次企业改制的试点都在杨汛桥。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都是杨汛桥的企业主动争取。从政经共谋财富,到政经分野。如何最后分手?方法是“赎买”。政府半主动地顺应了潮流。 1993年的改制,被企业私下叫做“花钱买了半个发言权”。当时改制的办法是,集体企业评估资产后,切出其中的20~40%,量化到个人,其中企业经营高层、中层、一般员工各占1/3,以现金购买股份,并按1∶1的现金进行配股,但个人只是享有股份分红权,没有所有权。但即使这样,“为自己干”的原始动力,已经具有不小杀伤力,促使杨汛桥成立了11家企业集团,成为“杨汛桥板块”的主力。 1998年,受企业极力主张民营化改造的推动,杨汛桥第二次改制。思路是主要经营者持大股,控股企业。政府退出过程中,镇集体所属的50%股份里的30%以上奖励给经营者。企业中一般集体股只保留20%左右。企业变身为民营控股企业。1998年改制,留下一个“红帽子”企业时代的鲜艳尾巴。 如果就此而止,杨汛桥的故事或许也只是浙东苏南的一个版本,但海外上市让一切都喷发出来。 “浙玻”第一炮 让“杨汛桥板块”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一炮打响的是浙江玻璃。第一个走进香港联交所气派非凡的股票交易大厅的是浙江玻璃的老总冯光成。 冯氏身材高大,颇有北人之相。这个出身泥瓦匠的人物,是杨汛桥诞生的典型企业强人。民间版本的浙江玻璃成长史,恰好体现了小镇主人公们的商业素质:对宏观利好和市场机会的惊人直觉,冒险的胆量和坚韧。 早在1994年,冯就以上马第一条造价高达4亿的浮法玻璃生产线,令人震惊。冯的“冒险”源于他看到邓公南巡之后,中国已成为大工地,玻璃价格疯长,这个行业却没有什么乡镇企业。但1996年浙江玻璃投产之日,就遭遇低谷。冯咬牙挺过。1997年坚持上马第二条浮法玻璃生产线时,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冯坚信以后市场肯定大,另外他们的成本比国企有竞争力。 1998年之后,建材价格大幅度回升。冯的坚持赢得了回报。到2000年,浙江玻璃已经成为全国第五大玻璃生产企业。冯成功地由建筑企业退身,一举在建材业立下基业。走到这一步,冯的“成功”套路并不令人意外。但他怎么会成为杨汛桥第一个踏上国内公认成熟和规范的香港资本市场的人物? 在浙江玻璃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变身故事。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物张德雄。2000年5月,张德雄来到杨汛桥任镇党委书记,下乡之前是县委办主任,对当地经济有一些研究和感受。当时,绍兴县是中国百强县前10位,但只有轻纺城一家上市公司。一心到下面的乡镇施展抱负的张德雄,有一种将杨汛桥镇变为“中国第一镇”的冲动和抱负,其中一个想法就是以上市为契机促进经济发展。 当时,冯光成脑子里也有这个想法。冯通过证监会的朋友,了解到如果在国内上市,要排队等上好几年,但到境外上市冯没有什么途径。当碰到“中国稀土”的老总蒋泉龙时,他觉得找到了一个近在眼前的榜样。蒋的企业是浙江玻璃原料供应商之一,在1999年通过借壳在香港上市。后来经过与香港方面的接触,浙江玻璃决定以H股在香港上市。 但海外上市,对于一个以乡镇企业起家的公司而言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一个真实的细节是,在获得香港联交所上市资格认定的过程中,许多次,冯光成打电话给张德雄,一个大汉在电话里痛哭失声,说上市非常难,不想干了。 为什么这样痛苦?因为,这实质上是对一个民企积累财富的历史进行规范化和合法化的过程。其间的难度可想而知。2003年12月,坐在本刊记者面前的冯,已经有了一个香港上市公司老总的风范。但你仍能从他的讲述中感受到当年迈出那一步的艰难。 当年上市,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要求规范。尤其是项目审批,香港联交所要求,一切经营项目都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因为,当年民企自己上项目,在审批上,都存在“不合法”的东西。浙江玻璃这个项目,本来应该得到国家的批准,但当时只是获得浙江省的批准。如果项目审批的法律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上市。浙江玻璃海外上市,获得省里的支持,采取补救的办法,出具有关证明手续,表明不可能追究当时的法律问题。当年以乡镇企业起家时的房子、土地,大多是镇里的批条,没有有关部门的审查。现在要合法化,冯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为此搞得筋疲力尽。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是,尽管经过1998年的改制,但镇政府在浙江玻璃仍持有20%的股份。所以,如果杨汛桥镇政府真正支持企业上市,就必须有所行动:集体的股份必须从企业彻底退出。 彻底改写历史的时机出现了。杨汛桥镇政府几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商讨此事。最终取得一致意见:退出!但怎么退?最后的办法是将20%的股份变现,企业买单,政府退出。这随后引发了2001年杨汛桥的第三次改制,割掉了红帽子企业史最后的尾巴。 经过这些不为人知的艰难过程,“浙江玻璃”最终在香港资本市场一炮打响。 “剥了一层皮” “浙江玻璃”在香港成功上市,在当地震动很大。 “浙江玻璃”拿到香港联交所允许上市批示的那一天,镇里刚好在开一个季度的经济会议。晚饭定在“浙江玻璃”那里吃,镇里准备让冯光成讲一讲香港上市的感受。冯说,“我已经拿到了香港上市的指标。”那顿晚饭,杨汛桥镇最好企业的老总都在座,但大家没有什么话,不知回去后老总们是否一夜无眠。 据说,从那天开始,杨汛桥企业满脑子想着怎么赶上去。 随后发生的事情充满了戏剧性。永隆实业的老总孙利永,是杨汛桥第二代企业家,1993年创办永隆实业,以加工生产T恤衫的面料起家,历史包袱相对较轻。孙本来是陪同去参加“浙江玻璃”香港上市仪式,但站在香港联交所那种跻身国际舞台的感觉,成为一个致命诱惑。再加上后来接触到的香港券商对他说,“你这个企业也不错,可以上市。”于是从萌发念头到上市,孙利永只用了11个月。 但轻喜剧式的插曲绝不是杨汛桥企业香港上市之旅的主轴。2003年,宝业集团将杨汛桥这一幕海外上市的潮流推到新的高峰,也将企业变身的痛苦程度推到新的高度:其掌门人庞宝根声称是被“剥了一层皮”。 宝业的上市之旅,遭遇了2003年最为恐怖的“非典”。国际社会对中国一片指责之声,香港疫情严重,股市低迷。要不要上?真是一个大问题。 站在上市门口的宝业集团,已经以民企的身份跻身国内建筑公司50强。面对国企老大们打造的游戏规则,一直谋求企业改制的庞宝根,据说10年前就曾为了争取改制机会而直闯绍兴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上市拿几个钱,并不是庞宝根所愿。海外上市的动机,来自于这样一种认识:以前改制所产生的机制力量在弱化,企业要进入更高的平台,用庞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自己为自己设置一道障碍”。这是宝业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上市的根本原因。 但庞宝根和宝业为此付出不菲。在此之前,香港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压力,已经通过普华永道审计等多种管道传递了过来。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是,国际投资者认为国内建筑行业流行“暗箱操作”,所以宝业集团经常被询问的是,“你们这个工程是否经过投标?”业界观察家早就指出,中国的建筑市场已经变成项目经理市场,利益在一张关系大网中流动。宝业能做大自己的民企招牌已属不易,此番想继续突围只有借助外力,引进成熟市场规则。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庞宝根对自己权力的“剥皮”。 当时宝业的上市团队戴着口罩,穿梭于内地与香港。情况也不允许海外基金经理赴杨汛桥考察。一开始负责承销的荷兰投资银行,因为拿不准非典什么时候过去,突然放弃了这项业务。宝业的愤怒可想而知,但不管怎样,决心争取在6月份上市。在6月最后的一天,宝业在欧洲基金经理最后的询盘中,定下了发行价格,结果为了等待瑞士银行这个战略伙伴,定价从每股1.6港元降为1.43港元。 因为非典的影响,这个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建筑企业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庞宝根说海外上市是剥一层皮,并不是空洞的套话。 新玩法 另一位实力派人物金良顺,却抓住“国退民进”的时机,以在国内A股新的玩法将杨汛桥民企在资本舞台上的表现,推到新的高潮。 轻纺城,一直作为绍兴在资本市场的标杆,显示着这个区域经济曾经达到的高度。2002年9月,金良顺旗下的精工集团,参与轻纺城股权重组,并以收购绍兴县彩虹实业有限公司的方式,成为轻纺城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国有股退出,金入主轻纺城。 金是杨汛桥企业家中,较早谋划上市的人物。精工集团旗下的精工科技,在1997年就完成股份公司的改造,准备在国内A股上市。显然金起了大早,赶了晚集。但随后在短短一年间,金良顺接连掌控两家上市公司,在国内A股风生水起。据可靠的消息,精工科技在2003年6月已经获得证监会批准,今年3月将在国内主板上市。果真如此,金良顺将掌控3家上市公司。 杨汛桥的民企在资本市场涉水越来越深。既忙于上市,思考怎么组建第二家上市公司和掌控更多的公司;又利用“国退民进”的宏观利好,收购兼并,迅速扩张,展开“造系运动”。这些人物的抱负显然不只是当一个资本玩家,掌控上市公司背后的动机是企业在战略上的扩张。这让他们再次成为浙江资本对外扩张中的一股力量。 2003年6月,金良顺旗下的精工集团以55.5%绝对控股长江股份,显露的就是其“造车”的战略。长江股份,是安徽长江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位于安徽六安市,是国内最大的手扶拖拉机生产企业之一,拥有国家认可的手扶拖拉机目录,可以生产有方向盘的手扶拖拉机。在这之前,精工集团已经参股江苏镇江汽车制造公司、苏州客车厂,以及杭州汽车底盘厂。 宝业集团也进入了安徽,收购了一家拖拉机厂—安徽拖拉机厂,这是安徽和浙江政府高层主推的“皖浙经济合作推荐会”的一个大项目。宝业准备由此开始从建筑到制造的跨越。香港上市的钱全部用于制造业,主攻建筑机械。 但杨汛桥民企的玩法还不止于此。 永利集团在2002年11月已经获得证监会批准,允许到香港上市。但老总周永利这个当年在杨汛桥一度执掌最大的企业,最早被称为“老板”的人物,认为自己的公司价值被低估了,因此做出了一个相反的决定,转向国内上市。而周永利在资本市场的故事,并没有就此而止,他涉足民间金融业。在介入当地信用社的重组之后,周参股了一家民营银行。这是一家据称规格与广东发展银行相同的浙江民营银行,已经被央行批准。 政经界的“双洗” “杨汛桥板块”喷发所产生的裂变,与政经界的良性互动不可分离。 2001年3月2日,集体股份彻底退出浙江玻璃之后,杨汛桥镇政府决心将1998年改制所留下的“尾巴”,从企业全部割掉。随后才是杨汛桥民企大面积在海外上市或掌控国内上市公司。这个时间上的前后关系相当重要。 对于杨汛桥蛰伏20多年的民间经济力量,海外上市,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洗刷”过程。民企最终转向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摘掉当年红帽子,将历史的根子洗刷干净,修得正果。对于在乡镇企业时代操作不规范的东西,政府鼓励企业按正规政策,不用暗箱操作,将产权、物权合法化。企业从中国环境下的潜规则中挣脱出来,遵循更成熟的规则。 从冯光成开始,杨汛桥的企业家正在熟悉怎样做一个公众公司,正在接受“股东价值”这样的理念,重新思考企业和自己的角色。冯曾经很不习惯与香港的审计师为企业的担保问题争吵,因为信息披露延误的问题,被香港联交所起诉、罚款……去年,浙江玻璃股价波动,冯耐心地接听一些投资者不讲情面的批评电话,很难想像,出身草莽的冯光成接受了这一套规则。 但这是一个“双洗”的过程。政府彻底退出企业,资本的纽带断开后,政企双方开始建立新的关系。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1年杨汛桥的第三次改制,政府的举动不仅是形势所迫,也是新的思考使然。90年代以来,民企急剧变身的现实,迫使张德雄这些镇一级的官员,不得不深入思考新的政经关系。在红帽子企业时代,政府以集体名义保留在企业里面的资产,企业好的时候,你不能得到多少股权分红,它出问题,你承担风险。“我们为什么留在哪里?应该想办法把钱拿出来。” 但“把钱拿出来以后怎么办”?当时的镇政府,对政企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张德雄他们发现,将企业完全交给企业家之后,政府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着力于公共事务和公共空间的塑造。张当时做了两件事,一是请清华大学为杨汛桥镇作了一个整体的形象设计,引入CI体系,将紫薇花定为镇花,杨汛桥统一标识。另一个是引进地理信息系统,期望把杨汛桥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污水井、每一条路都放到信息系统里管理。 兴建紫薇广场成为一个新的标志。对于兴建紫薇文化广场这样的公共事业,没有再按照以前的惯例,向企业收取捐款。按以前的经验,企业不会白给政府好处。公益事业,让企业捐款,企业要政府从其他地方加倍还回来。就此在政企之间建立了新规矩,政府的事情,自己出钱,但企业应该交给政府的钱,分红,土地款,纳税,每一分钱都要到位,这些钱用于公共事业绰绰有余,而“以前是把事情颠倒做了”。 随着浙江玻璃等接连上市,整个杨汛桥企业投入很高,纳税很大,财政收入猛增。2000年是1.2亿,2001年为2.2亿,2002年为3.2亿,2003年据说要突破4亿。杨汛桥镇政府的钱袋饱满了,足够保证对公共事业的投入。 在满目青翠的牛头山下,两个标志性的建筑比邻而立。一个是紫薇广场,一个是高尔夫练习场。这是杨汛桥新的标志,标志着这个镇在公共层面有了各方共享的空间,是新的小镇政治的转向,是政府对公共空间的塑造。这都是企业上市之后出现的新东西。 官员入民企的冲击波 但民企海外上市的冲击波,依旧没有就此而止,一批政府官员随后下海进入上市民企。 2002到2003年间,前杨汛桥镇党委书记张德雄,来到永隆实业的管理、控股公司加佰利集团做总经理、副董事长;前绍兴县财税局长鲍永明,到精工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轻纺城做总经理;前浙江省外事办副主任魏法林,官至副厅级,到宝业集团做总经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是地道的杨汛桥人,或者在杨汛桥做过时间不短的政府工作。 张德雄做了3年镇党委书记。鲍永明是杨汛桥人,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在绍兴县财税局有很长的工作经验。魏法林是钱清镇人,紧邻杨汛桥,1989年浙江林学院毕业后,主动要求到乡镇工作,有7年半乡镇工作经验。他一开始就在杨汛桥镇工作4年,做过团委书记,工业助理,跑了很多工业项目,包括冯光成当年的强地砖项目。后来,魏在其他乡镇做镇长、党委书记,后来,在“双推双考”中,进入省政府。这显然是一些颇有才华的政府官员,他们或许在政治上还有更大的前途。 据说,张德雄和鲍永明都曾经面临一个机会:被提拔为副县级。在一个县域,这应该是一个官员不错的前途。张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自己期望将杨汛桥变为中国第一镇的梦想还没有完成,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把自己的东西做出来,但这显然并不现实。看重做事情的张,最终选择辞职下海。而鲍永明笃信,最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发展,自己到企业的创造力更大。 显然,他们相当了解杨汛桥这些不断裂变的企业和企业家,而企业家也相当了解他们,从人品到才能,还有专业。双方都拥有共识和信任。 在这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中,杨汛桥这些由乡镇企业裂变为上市公司的企业,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想要寻求管理上新的突破。以前因为信任的问题,基本依靠家族管理。现在企业迅猛扩张,自己培养人才都来不及。在现实的环境下,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管理自己的企业,还不能放心;最好能找到既熟悉又有能力的人,当地富有才华的官员于是成为一个容易接受的选择。这种明显带有地域乡土色彩的用人机制就这样建立起来,为职业经理人文化注入了中国特色。 就这样,由“杨汛桥板块”裂变,所引发的一系列变身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从民企,一直蔓延到当地的政经两界,关涉政企关系的新变化,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可以这样说,整个变身还在进行之中,它正在改变和塑造着这里新的民间社会。 本刊记者 袁卫东 发自浙江绍兴
|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证券要闻 > 财经杂志秀之《南风窗》2004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