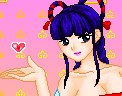|
杨 波
英国即兴爵士乐吉他演奏家德里克·拜雷于去年12月25日去世,死在西班牙,75岁。按人的自然年岁计,他的死可释然地归于天命;但对爵士乐而言,这个人再活一百年或许都不够——于是更悲哀。
不客气地说,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爵士乐在本质上再无进步。摇摆、酷爵士、后波普等传统派系变得日益慵懒无力,似老妓脸上的粉垢般令人厌烦,这或许源于现今时代的做作与50年前时代的做作再无关系。但是,却有太多迷恋着爵士乐的后辈音乐家去即兴、去先锋,以至于十多年来出品的爵士乐唱片,在绝对比量上竟是前卫作品占了多数。这有些像如今泛滥的网路博客,暗藏鬼胎地以看似完全私己态度的发言示众,并一发不可收。灵魂与底裤的区别,人们并非搞不清楚,不过自缚其中罢了。
我一点都不觉得,自约翰·考川、查里斯·明格斯、桑·拉等划时代的大师之后,有关爵士乐的自由即兴或先锋编作在方法上有任何倒戈式的革新出现;另一面,我却深深觉得,那些在60年代末崭露头角的先锋者,他们迄今不止的工作令爵士乐的先锋性和自由度更加地纯粹、精到、极致——这样的人物,除去拜雷之外,还有安东尼·布拉克斯顿、伊文·帕克等等——他们,连同后来寥寥可数的如约翰·佐恩、大友良英等音乐家,是真正维系住爵士乐根脉的人。
其实,若说拜雷弹的不是爵士乐,我想他也不会怎么生气——尽管他说自己惟一崇拜的音乐家是30年代末的传统爵士乐吉他手查里·克里斯汀。克里斯汀确切的唱片只有一张传世,他出现在公众面前也不超过两年,却为以后爵士乐中吉他演奏发展的一切可能埋下了种子。想来,这位在25岁时死于海洛因的青年与那时多数希望拿出自我见解的黑人音乐家一样,心里面很苦——假如他那个时代没有流行的摇摆爵士乐、没有气粗的乐团领班班尼·古德曼,甚至没有阻碍他生计的黑皮肤——他与吉他的关系仅如太阳和花一样。
果真明白音乐为何物的人,会否认流派与风格之间的任何关联——因为前者是社会的、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自我的。那么,个人与社会的主宾关系正如风格与流派的从属一样,若非归附,即为归纳——一个人是否生活在社会之外,与他所属社会的强权程度并非息息相关。一个人要有让灵魂站在最前面的勇气,这其实是一种不需强求就可得到的本能,就像不管秦朝或现代的男女都会恋爱一般。
以上,应是拜雷的艺术哲学。
拜雷认为,音乐是人与自然及人性关系的综合体现——这种音乐,他称之为即兴;这种关系,他称之为灵魂。
即兴已不是美学,它可能是惟一的艺术体现——因为艺术作为美学呈现的谱系已经终结,仍然不放弃革命念头的艺术家都会这样认为。即兴并非发疯,它甚至不回避规则,就像四季轮转,每一季的河流都泛滥在那个月,但或在这一年干涸了,那一年却凶狠地冲破堤岸。
另一面,灵魂若仅人类才有,难道是因为我们有火和社会——当一个人以一只猫或一朵花的角色去体味灵魂,或会惊讶地发现自由离自己竟然那么近。只要身处文明之中,灵魂就是人的悖论,懂得拥抱这悖论之人,或者绝望,或者亢奋。
以上,应是拜雷的音乐体现。
若说这世上的音乐都很难用文字描述,那么像拜雷之类的音乐,则干脆是无法描述的。这个人的独奏作品尤其风格化,音与音之间冷漠而干净,是一点事故人情都不愿藏着的。他一直喜欢与人合奏,奇怪的是其弦音竟从合奏中消失不见,就像脊骨从身体的外表看来似不存在一般。他是一个懂得如何回答,并让答案迅速被提问者忘记的人。
以上,应是拜雷的75年。既自然又人性的东西,谓之灵魂——而灵魂不一定总是寄居体内,它更多时候像鸟一样,在天上飞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