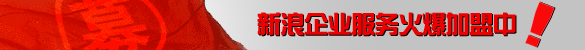一场大火改变了我的人生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18日 18:13 经济观察报 | |||||||||
|
采写:刘小萌 口述:小月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某市属单位一
我父亲当初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跟李政道是同班同学,原来是学物理的,一个挺有天赋的人。在学校的时候,大家给他起的外号叫“百科全书”。在解放区,他也算是很有文化的干部了,一解放,就被分配到人民政府办的第一所大学里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个“黑典型”、“反动学术权威”,父亲受过多次批斗。即便是这样,但父亲认为自己一生坦荡,党和组织定会还他一个清白,他多次表示,绝不会自杀。 被父亲株连,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无一例外,全都插队。 我是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当时心里非常明白,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留城。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绝对是黑帮,而且我想通过下乡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以前我每次填出身都填“革干”,因为父亲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但是在东北农场,出身按爷爷算。我爷爷是经商的,没办法,只好填了资本家。为此,贫下中农会也不能参加。我总这么想:偶然成必然,正是因为这么个出身,正是因为我们这种非常纯洁的心灵,所以总是积极向上,努力想洗刷自己。 1969年10月19日是个极普通的日子。我们正在喂猪,“不好了,草甸子着火了”!只见西北方向浓烟滚滚,晓军抄起扫把,我拎条麻袋冲了出去。考验我们的时刻终于来了。没人组织,没人号召,面对一片火海只有七个人,五个北京知青,一位本地青年和一位大嫂。 大火即将吞没2400亩大豆,也威胁着村舍住地。我甚至为能有机会向党和人民表示自己的忠诚、以青春和热血洗刷凭空加在我身上的耻辱而感到庆幸。 浓烟呛得喘不过气,烈火烧得睁不开眼,几百度的高温使人窒息难忍,烈火烧身的痛苦使人本能地后退。我听见晓军在鼓励我:“小月,坚持住!”我感到她是在向我暗示,只能用行动证明我们不是“狗崽子”了,关键时刻我们有和工农后代一样的热血和肝胆。往日的屈辱、压抑一起涌上心头,我忍着难言的痛楚疯狂地抡着麻袋,甚至感到一种洗刷灵魂的快乐。晓军一下又一下挥动扫把,烈火燃着了掀起的衣角,烧秃了手中的扫把,她好像全然不知,奋力高呼“下定决心……”我随着她一起呼喊“……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无情的火舌窜入口中,我不知自己是怎样喊出来的,声音是那么凄厉吓人。想用死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可能是阶级斗争年代我们惟一的选择。 突然,晓军身上起火了,我拼命地朝她喊:“李晓军,快打滚!”她倒在滚烫的大地上,我知道她是在为父亲赎那并不存在的“罪”。我的手、脚、脸已全部烧伤,好像有无数把利刃在割着。我不顾一切随着翻滚的晓军奔跑,却不知该怎样帮助她。 远处传来大嫂悲痛的哭声:“小张不行了!”晓军用严重烧伤的双手推着我们说:“不要管我,快去救火!不要管我,快救小张!”没人注意到大火卷过之后,张梅玲已经倒在焦黑的土地上,没来得及实现她救火的愿望,甚至都来不及哼一声。她的皮肤烧焦了,肌肉炸裂了,一截短辫散落在身旁,全身只剩下一条腰带和一双鞋底,她全身赤裸洁白刺目,四肢挛缩着一动不动。可当时我以为她还活着,我觉得很害羞,一个姑娘就这么赤身裸体地躺在那儿,可我又找不到什么可以盖在她的身上。 闻讯赶来的人们背起我和晓军。梅玲已经不能背了,伸手只有抓落她剥脱的皮肤,人们脱下衣服套在锹把上抬起梅玲,烧成液体的脂肪从她身上流淌着,点点滴滴洒在长满毛刺的苍耳草上,脱落的皮肤随着担架的起伏晃动。多少年过去了,一位当年抬担架的哈尔滨知青对我说,在那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他都不能吃肉,端起碗,就是肌肉烧焦的气味,那惨烈一幕给他的刺激太强烈了。 几个青壮年男职工轮流背着我,踏着齐腰的荒草,深一脚浅一脚走几步就要换一下,我伏在他们的脊背上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身子软软的不断从背上滑落,稍一用力好像全身的血管都会爆裂开,肿胀的脸封住了眼睛。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只能听见沉重的喘息声,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知青们目睹这种惨状不禁失声痛哭,一位男知青怒吼道:“哭什么,我们首都的红卫兵,决不给毛主席丢脸。”四周一片沉寂,烧灼的痛苦如万箭穿心,我更牵挂着晓军,因为只有我才知道她心里比身体更重的创伤。我问:“晓军,你痛吗?”她回答:“不痛。”那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到,只有经过烧伤的人才能体会到那是怎样一种痛苦。 尽管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火势并没有丝毫的减弱。那火又烧了几天几夜才在拖拉机翻起的防火道前熄灭。大火卷起灰烟随风飘出几十里以外,或许历史和我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那场使我们生离死别的大火竟是一个牧牛人在百无聊赖之际点燃老鼠取乐引起的。 数月后,我偶然在与病友聊天时听到晓军、梅玲牺牲的消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眼前还晃动着她们的身影,耳边还响着她们的说笑声。长期以来遭受歧视的压抑,烧伤带来的心灵、肉体的痛苦,失去同学、朋友的悲哀如同决堤的洪水,我号啕痛哭,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病房门口挤满了人。 我的同学、战友李晓军和张梅玲就这样去了,她们去得太早,她们还年轻,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带着对理想的追求,融入她们所热爱的黑土地。她们同生于1949年10月,与我们的共和国同龄。 事后,贫农出身的张梅玲荣立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李晓军却因为她的出身而无声无息,没有得到任何荣誉。她静静地长眠于地下,白桦林成为她永恒的背景,她不知道死后社会是怎样不公正地对待她。知青们对此愤愤不平,难道洒尽鲜血也不能抹去笼罩在她身上的阴影?献出生命还不足以证明她的真诚? 晓军的母亲从北京赶来了,当她掀起晓军身上的被单,看到被烧成焦炭无法辨认的脸时,大家的心猛然抽紧了,母亲竟然没掉一滴眼泪,只是用手抚摸着晓军僵硬的脸,喃喃地说:“孩子,你不是常说要向刘英俊(因抢救儿童光荣献身的解放军战士)叔叔学习吗?今天你做到了,妈就放心了。”追悼会上,母亲望着眼前与女儿年龄相仿的知青,把悲痛深深埋在心底,怎么也不肯接受抚恤金,说:“孩子是为国家牺牲的,我不能在女儿身上沾光。”那时的领导有一个观念,“右派”家属不许接近,不让大家去看她,可是因为晓军这个人太好了,知青把对晓军的那种感情全给她母亲了,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去跟她亲近。她妈妈也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从头到尾没掉一滴眼泪。许多年后晓军母亲回忆说:“当时心里难过,可又没有泪。一拨儿孩子来看我,他们又不让接近。孩子已经牺牲了,再闹出别的事,也没有什么意思,是不是?”晓军母亲一个人默默地走了。 那场大火使我失去了朝夕相伴的同学和朋友,也使我原本光滑圆润的脸斑痕满面,从此走向坎坷的人生。我不知用怎样的语言描述一个19岁风华正茂的少女当时复杂的心境,但我从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也不乞求人们对那个时代行为的理解和同情。 我怎么也没想到,烈火在一瞬间会改变一个人的容貌。那时候我没有镜子,也不觉得奇怪,病房里谁给你搁个镜子啊?医生怕我接受不了现实,几次换药时都对我说:“你脸上可能要留下伤疤的。”我天真地以为,出院后会和从前一样,只是留下点儿小痕迹,笑着说:“没关系,留了疤不是照样为人民服务吗?” 烧伤后大夫不让探视,一是怕病人感染,二是怕外界的刺激,因为烧伤病人的感染是致命的。好多同学来看我,大夫就是不让进。 有一天,队里一个宁波知青把门推开一条缝,我这是第一次看见连队的人,心里挺高兴。可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她就“啊”的一声尖叫,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怎么了,在我心里,我还是从前的模样,发生什么事了?救火事件在农场影响挺大,当时团里领导都来了,说“一定要尽力抢救”。医生、护士对我都非常好,我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异常,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吓着别人,也被别人吓着。 我第一次照镜子是烧伤以后很久了。我上医生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好多面镜子,是患者送的“救死扶伤”呀、“医术高明”呀那种。当我从镜子里看见自己,头肿得很大,当时我就傻了,木呆呆的,不认识镜子里的人是谁。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夫老跟我开玩笑,管我叫“大头翁”。脸上的皮肤烧焦了,只有坏死的肌肉和皮肤脱落后才长出鲜红的嫩肉。我觉得自己的脸像铁面人似的戴着一个硬硬的假面具,难受极了,可也拿不下来。翻着的皮肤,渗出的体液,涂上的药液,脸上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斑斓”,坑坑洼洼,耳朵也烧卷了。虽然理智上知道镜子里的人是我,可从感情上怎么也接受不了。 烧伤后许多人都认不出我,到处盛传我烧得像鬼一样。在烧伤之后,为了我自己,我一滴眼泪都没掉过。那时19岁啊,一个19岁的女孩子……后来,我吓过很多人,那么多的人也吓过我。我不敢天黑的时候出去,只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出去,让人家在很远的地方就看清楚我,为的是不让人家吓着我。因为有的时候,人家发出的那种尖叫,常常把我吓一大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我记得,那时八个样板戏老是演,每次,当小常宝一唱“早日还我女儿装”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 负伤后,我被批准加入了渴望已久的共青团。出院后农场办了一个张梅玲事迹展览,我成了展览馆的讲解员。出于宣传的需要,人为地把李晓军的壮举全部加在张梅玲身上。在展览中,晓军只有一个画面,我的名字也只出现了一次,就一句话:“张梅玲、李晓军、小月一起救火。”这个展览馆大概保存了三年。 其实我心里不愿被展览,毁容对我的打击已经够大了,尤其是让我讲一些并不真实的东西,可我又能说什么呢?上面定好的东西强加给我。让我讲解,我曾经进行抵制,但不讲不行。后来我采取一种什么措施呢?上讲台的第一天,我侧着脸对着讲台,故意嘟哝着,谁也听不清我说的是什么。我觉得那时候我没有任何权利,我的权利就像鲁迅说的:沉默是最大的反抗。我从什么时候产生反抗意识的呢?就是看他们对晓军不公。现在我不能说这是不是叫反思,有没有这种觉悟我不敢说。 烧伤以后我没有写入党申请书,营长找我:“你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也许跟我的家庭背景有些关系,可能比其他出身不好的人多一点政治承受能力,我其实心里很明白,即便写了也未必会发展。但最后我还是写了,也确实没发展,多少年也没有发展。 二 1973年开始推荐我上大学,但因为父亲的缘故,哪个学校都不要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好多人都不愿意当老师。我想,干脆报师范吧。最后给我答复:“老师要五官端正,您这样怎么能当老师?”连着两年,都没上成。第三年,也就是1975年,我已经25岁了,按照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25岁是最后年限,超过这个年龄就没戏了。那一年也不知怎么的,忽然改成自愿报名、群众推荐,一律要票数,你够了票数才能推荐上去,领导也很难做主。我觉得是最后一年了,又报了名。 上学期间,我在班里的成绩以及各方面都是很出色的,同学们公认这一点。毕业分配把我弄到环卫局,也不明白是干什么的,报到后才知道,敢情是个“垃圾站”。当时“垃圾站”占了一块农民的地,刚开始盖房子,他们告诉我今后的工作,就是处理粪便和垃圾。那个时候中国对垃圾的处理,研究和机械化都谈不上。 后来有个同学给我透露了消息:我被“调了包”。我听了后如五雷轰顶。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忍受屈辱、磨难,无休止地挣扎。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惟一拥有的就是聪明才智,我用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么一个水准本来挺好的,想凭自己的努力体现人生的价值,可社会连机会都不给我一个。 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因烧伤毁容的脸总让人家觉得奇怪。我又开始跟人解释,但跟上大学时就不一样了。上大学时,同学们都知道,你不是有背景,就是表现好,都是挺特殊的人。可一到工作单位,你这么怪里怪气的人,别人就觉得:你这事儿,怎么档案里没有记载?我就跟一个说谎者似的,喋喋不休地去跟人解释。人们总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觉得自己就像祥林嫂一样。无奈,1983年我回了一趟农场,要求给我落实政策。农场的人事干部觉得很奇怪:“你现在不是国家干部吗?也有工资,还想要什么?”我说:“不是想要什么,而是我应该有什么!因公受伤就不应该有个记载吗?” 农场为此发了一个文件,文中说:“小月同志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英勇救火中被烧伤,实属英雄之举,定为因公负伤,为妥善处理,农场根据立功批准权限给予补办立三等功一次的手续。”到此为止,事情似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张梅玲、李晓军的烈士称号是黑龙江省政府授予的,而我的三等功是农场批准的,社会上根本不承认。烧伤后我曾先后六次住院,做双足植皮、面部植皮、疤痕切除、植眉等大小手术数次,离开农场后许多手术都是自费,不仅要独自承受烧伤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手术的身心痛苦,还要被扣工资、奖金。 为改变自己的艰难处境,万般无奈,我只好与农场联系,希望能得到使社会认可的结果。他们说:“你看,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农场的能量有限,我们实在力所不及。”他说这个,我也相信,但是我怎么办呢?我都五十多岁了,人生不过两件事,一个是家一个是业,我是既没有家也没有业。什么我都没有,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记得佛经中有句格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是说佛为普度众生要承受世间的一切苦难,或许我就是该下地狱的人。 回到单位,把那些资料装在档案里,单位领导不能不承认这件事,但承认没有任何用,从来没有给过什么关照。在单位,人家看你这个样儿总是不顺眼。但是这种事谁也不会说,包括出差、进修任何机会都没有。上学的时候我是班里的佼佼者,后来对工农兵大学生进行补课考试,我在单位里每次考试都是头几名,就是这样,任何机会都不给我。 我这个人挺要强的,工作上也很努力,烧伤后我知道自己只剩下勤奋和才智了,可无论我怎样努力,都得不到与他人一样的平等,我从来就没奢望过组织对我有所关照,但连起码的平等都没有。我工作后先后换过几个单位,每到一个单位好多人都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有几次党员开会,人家特地来通知我,说在哪儿哪儿开会。我问:“开什么会呀?”人家说:“党员开会没通知你?”我就笑了,说:“我不是党员,但是你通知我,我很高兴。”最起码我明白,在大家的心目中我是个党员,有这点我就知足了。 上山下乡彻底改变了我这个阳光女孩的命运,付出的比常人大,却享受不到常人的生活。独身好像对社会欠了债,人们觉得你没有家庭之累,每逢单位义务劳动或者加班,我都是首选,生活遇到困难却无人分担。甚至独身也成了不分房的理由,许多工龄短、职称低的小青年只要一结婚就可以分到房子,但我如何申请就是不行。快50岁了仍与70多岁的父亲、继母挤住在一处,我常担心到年老时无安身立命之所。世纪末,在福利分房即将结束时,我终于分到了一套远郊的房子,虽然每天路上至少要花费三个钟头,其中还有一段路不通车,许多人嫌远不去住,但我倍加珍惜,这是我年近半百才有的“窝”呀! 我与普通人一样渴望有个家,我参加过电视征婚,虽然一开始我就明白很可能没有结果,但追求生活的幸福就像攀登山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峰顶,但每前进一步都比原来站得高。只要自己努力过,当生命结束时心里也不会留有遗憾。 知青是背负沉重十字架的一代,永远在替父辈、自己甚至是后代偿还债务,身上有着抹不去的悲剧色彩。 没人去追寻历史的责任,忘不了这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同赴火海的知青。纵然我们对历史有过怨言,也在挫折里将一切看淡,然而内心深处还是忘不了那生与死、血与火和那片黑土地。我喜欢一首叫《小草》的歌,它唱出了卑微中的顽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株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应口述者要求,本文主人公小月使用的是假名。)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
|
不支持Flash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生活 > 正文 |
|
不支持Flash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市黑马:今日牛股! |
| Excel服务器功能强大 |
| 戒烟让男人暴富项目! |
| 韩国亲子装2.5折供货 |
| 1000元小店狂赚钱 |
| 联手上市公司赚大钱 |
| 一万元投入 月赚十万 |
| 18岁少女开店狂赚! |
| 99个精品项目(赚) |
| 治帕金森—已刻不容缓 |
| 夏治哮喘气管炎好时机 |
| 痛风治疗新突破(图)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Ⅱ型糖尿病之新疗法 |
| 高血压!有了新发现!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