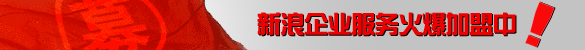蒙古长调: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10日 17:45 经济观察报 | |||||||||
|
本报记者 刘溜 内蒙古报道 描述歌声之美是困难的。记者在呼和浩特的五天里,多次听到蒙古长调那悠扬、深沉而宽广的旋律,不管是在斗室之内,还是在人潮汹涌的新华广场,只要听到一曲长调响起,马上就能被带到那辽阔的草原,那发自胸臆的歌声,在天地之间飘荡,仿佛能传到无穷的远方。
6月3日,我们驱车去呼市北边八十公里外的希拉穆仁草原,这个草原和西北方向的锡林郭勒草原、和更远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及更为遥远的外蒙草原都是连成一片的。6月初的草原,草还只有寸余高,无名的黄色、蓝紫色小花点缀其间,大风挟带着沙尘直扑人的眼睛。 牧民们牵来马,我们纵马在草原上飞奔,从小在牧区长大、来自狮子王旗的小伙子布仁白依尔一边唱起长调《摔跤歌》,一边策马绝尘远去,自由挥洒的长调、撒蹄飞奔的骏马、辽阔无边的草原,三者融合无间。布仁说,他偶尔也听流行歌曲,但与长调相比,太没有味道了。 中午在蒙古包里,女主人托娅端来烤羊排和草原白酒,同行的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朝克图老师唱起了长调名曲《小黄马》,歌者端坐着,神态肃穆深沉,布仁白依尔配以低沉的呼麦,虽然听不懂蒙语的歌词,但那苍凉悠远的歌声,足以让听的人肃然起敬,暂时忘掉自己,与身处的这片草原融为一体。 如今,一直在草原上自由回荡的蒙古长调获得了世界性的声名。去年的11月份,蒙古长调入选为联合国第三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中国和蒙古国联合申报,在此之前,同为草原文化精髓的马头琴已由蒙古国独立申报成功。 联合申遗 内蒙古艺术研究所所长乔玉光说:“长调和马头琴是蒙古文化的典型代表,独一无二,蕴含着草原文化的精髓。如果这两样消失,蒙古文化也就消亡了。只有草原才会产生这种文化,但草原又不一定会产生这种文化,草原民族那么多,但只有蒙古族有这两样。” 长调申遗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悬念和紧张感。 2004年7月,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第三批的申报,蒙古长调本来也想单独申报,但中国的申报项目最终选择了新疆的十二木卡姆,按规则一个国家最多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多国联合申报,但必须是同质文化,内蒙和外蒙符合这一条件。这时,蒙古国已经单独申报了长调,之前他们已经将马头琴申报成功。蒙古国能否同意联合申报长调,把握并不太大。 乔玉光负责申报文本制作,12月30日前必须上交。但蒙古国迟迟没有回音,蒙古国内正在进行第4届国家大呼拉尔选举。11月底乔玉光单独去了趟乌兰巴托,拿到了对方的文本,12月17日他终于见到了他们的文化部长,部长认为“内蒙的民间长调没有了”,乔玉光建议蒙古国派个专家考察团到内蒙实地考察,部长同意了。 2005年4年,蒙古国由5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到了锡林郭勒,这个地方是代表团自己挑的,他们到了牧民家里,听到了民间长调歌手的演唱。此行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看法。 6月8日,两国的乌兰巴托签署了合作协议,同意两国联合申报。 接下来是合成文本,这项工作难度颇大,因为两国的文化、社会背景都很不一样。本来应该双方的专家坐在一起讨论,动手完成,但时间太紧迫,加上之前拿到了对方的文本,于是乔玉光先合成了双方文本,“对一些观点冲突的地方进行了处理”。 13日约见蒙古国首席专家,对方说来不及了。乔玉光拿出已合成的文本,“当时很紧张,万一对方提出重大的修改意见,就真来不及了”。14日再次见面时,看到首席专家“面色轻松,就放下心来,对方只提了一个小修改意见,半天就可完成”。修改完文本,再转成电子版,还要准备十分钟的申报录像带,“每天只睡两小时,到17日巴黎提交给教科文组织时,比截止时间只提前了一个小时。” 11月25日,由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长调获得通过。 “下一步就是具体措施了”,乔玉光说,要按照申报文本的十年规划来做事,目前正在着手组建两国联合机构。将与蒙古国联合开展田野调查,共同进行理论研究,联合制定长调民歌传承人的普查和评价体系标准,并进行长调的宣传与培训,举办国际长调比赛等等。 “学校教育下的传承是一方面,非主渠道,学校教育会学院化,而原生态的文化重要的是在民间,在于对传承人的保护,将会在牧民居住地建立保护区。如果没有这一点,没有牧区的传承,就该进博物馆了。也会搞培训,但不会搞学院派。”长调的魅力 “为什么在茫茫草原上最受人爱戴和敬重的是歌手和摔跤手?为什么失去子女的母亲不是悲哭而是悲歌?为什么在草原上连牛羊骆驼也听得懂《劝奶歌》?为什么在流行歌曲畅销无度的当代,民歌在蒙古人心中依然牢牢地占据着统治地位?”克明和朝鲁在一篇文章中这样问道,“蒙古民歌说到底,是一个民族对生命感悟的整体性审美体验。” 蒙古长调究竟有多大的魅力,“长调歌后”宝音德力格尔曾经讲过她亲历的一件事:她七岁多的时候,有一回父女俩被几头野狼围住,情急之下失明的父亲拉起了马头琴,女儿唱起了《辽阔的草原》,狼群停下脚步聆听,而后慢慢离去。 蒙古人相信,长调是伟大的,又是神奇的,它不仅能感动人的肺腑,而且能打动动物的心灵,这不是夸张之词,也不是偶然的传说。著名的长调作曲家、研究家莫尔吉胡对此也有过亲身经历,“生第一胎的母骆驼和母羊往往不知道去奶孩子,这时牧民们就要唱起劝奶歌。我收集过许多劝奶歌,都没有歌词,一个牧民一个调,悠扬、温情而哀婉,我亲眼见过母骆驼听了劝奶歌后终于回心转意,掉下泪来,那场面真是感人。” 有一首《孤独的驼羔》唱道,“寒冷的风呼呼吹来,可怜我驼羔在野地徘徊;年老的妈妈我想你啊,空旷的原野上只有我一人在!”在马头琴的伴奏下,长调唱出了草原的辽阔、自然的永恒、岁月的漫长、人生的短暂与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歌手则是草原上的牧师,用歌声抚慰着人们的心灵,让灵魂回到本质的状态。 长调为什么如此悲凉,为什么能直接穿透人的心窝?有人说,蒙古人曾用铁蹄和马刀敲开了中世纪黑暗的大门,把东方文明之火带到了欧洲和世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版图的帝国。后来它衰落了,灭亡了,强悍的蒙古人带着对往昔辉煌的记忆重新回到了这片草原,这种落差无疑会在整个民族的心理上蒙上一层阴影,形成了一种无言的巨大悲哀。 在蒙语中,长调称为“乌兰图道”,意为长歌,相对于简单的短调而言,除指曲调悠长外,还有历史悠久之意。在申报联合国“非物质遗产”的文本中,是这样描述长调的久远历史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长调或长调的早期形态,就已经在匈奴人中存在了”。一些有名的长调曲目从成吉思汗时代传下来,至今已经被诵唱了800年,《天上的风》就是其中之一,“天上的风往来不停,世上的人哪能永存?趁此机会,奋斗吧!”曲调激昂雄浑,苍凉悲壮。 心灵的自由 一直以来,长调的传承主要靠一代代歌手们口传心授,有关长调的文字资料非常之少,最早记录长调的口头传说、歌曲音乐和庆祝活动的资料可在《蒙古秘史》、《黄金史》以及13世纪欧洲和亚洲前往蒙古游历的旅行者的记述中找到。歌手是蒙古人特别尊重的,在那达慕、宴会以及各种庆祝活动中,长调歌手及伴唱音乐家,都被安排在尊贵的位置上。 1950年,在锡林郭勒盟国庆一周年大会上,莫尔吉胡听到了哈扎布与他的老师特木丁的演唱,“唱得非常好,比他的老师还要好,气息的运用、唱歌的心态都很好,感情醇真、意蕴浓厚,听了让人震动不已。我当时是内蒙文工团成员,我激动地向布赫团长推荐哈扎布”。不久哈扎布成为内蒙古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开始了四处演唱乃至出国演出的生涯。他是蒙古长调的集大成者,无论是在演唱风格、技巧运用还是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方面,都把长调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1995年他被内蒙古自治区授予“长调歌王”的称号。 不久后,莫尔吉胡又发现了另一位长调大师照那斯图。 二十来年前,哈扎布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莫尔吉胡说,“蒙古人不喜欢城市生活,草原才是家”,哈扎布晚年的境况不是太好,生活有些艰难,又不无孤独,经常唱起《苍老的大雁》,歌词有“秋末寒冷已来临,芳草枝叶调谢失颜。啊,我那可怜可爱的七只雏雁,想必已飞到温暖的地方安居欢乐。年迈的老雁,我呵,只能留在山河上空盘旋。”去年哈扎布在草原上去世。呼市的大青山公墓新建了一座哈扎布铜像,以纪念一代大师。 长调歌后宝音德力格尔的名字在蒙语中的意思是“幸福像花朵一样绽放”,然而她的早年极其不幸,两岁时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失明,她跟父亲在草原上到处唱歌,对着草原的日出而唱,对着草原的日落而唱,十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1955年,二十出头的宝音德力格尔在第七届国际青年联欢节上以那曲《辽阔的草原》获得金奖,是第一位把长调带到国际上的歌手。 照那斯图和宝音德力格尔后来都在学校任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在长调歌手的名单上,还有一长串名字:拉苏荣、扎格达苏荣、莫德格、德德玛…… 长调的旋律悠长、宽广,有如不断流淌出来的河水。其声调变化多端,悠长宛转的旋律包含多种节奏性很强的变化;音域宽广,创作形式自由。长调演唱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风格特色的演唱技巧是称为“诺古拉”的颤音,像草原、水波一样起伏,是长调的华彩部分,“诺古拉”意为“折”,即弯、曲的意思,诺古拉的唱法有许多种,既有柔美如丝般的折音,又有如颠起的马步一般爽脆的折音,这些微妙的变化和处理在曲谱上很难体现出来。哈扎布被公认为惟一的、掌握了所有“诺古拉”技巧的歌唱家。 长调歌词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对草原和骏马的赞美,有对家乡的思念,有婚礼歌,有宴歌,还有对季节变化、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长调都表达了一种延伸的时空感,这种感觉源于文袤、开阔的大草原,长调与草原是浑然一体的。 演唱长调是自由的、即兴的,一首歌在不同的歌手那儿有不同的演绎。哈扎布曾介绍说,他年轻时对每首长调都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演唱,根据听众的反应和欢迎程度最后定下一种方法演唱,听了其他名歌手演唱某首歌后,他自己想尽办法再加入别人没有唱过的技巧和风格韵味,努力超过别的歌手。 莫尔吉胡说:“唱长调时的心态比较独特,不是唱给别人的,而是唱给自己的,没有交换的意识,也可以说是内向的。蒙古人是音乐的民族,也是内向的、沉思的民族。过去的歌手往台上一站,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长调的音调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草原,其实是人的内心一种松弛、舒展、空旷、无疆界的状态。” 土壤在退化 因为长调唱法和美声唱法比较接近的缘故,年轻一代的歌手们有不少人借鉴了美声唱法,扎苏荣、德德玛在学长调后又学习了美声,潮鲁、阿拉泰等人则是先学美声再学长调,内蒙古大学以及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长调专业,很多老师都兼教长调和美声。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格日勒图1999年曾赴蒙古国学习,在那儿获得博士学位。他说,蒙古国的长调与内蒙相比,更加强调原生态,大学里的长调教学仍靠口传心授,基本上没有引入美声的方法和理论,但他私下里问过他们的女歌王诺日布班孜德,后者在宝音德力格尔后一年,于1956年的国际青年文化节也获得金奖,女歌王说她多少借鉴过美声唱法。 潮鲁说:“原生态是好的,但要发展。要有理论化、体系化,更便于其他民族了解学习,教给人家得有理论基础。如果光是口传心授,适应不了现代化要求,外地人、外国人来了怎么学?”朝克图则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歌手和研究者们的担忧集中于一点——那使得长调得以产生的根和土壤正在消失。莫尔吉胡说:“长调是有人文背景的,它和草原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自由的游牧生活,辽阔的草原,无拘无束。和这种生活对应的,有摔跤歌、赛马歌,有对马、对草原的热爱。”蒙古国著名演奏家洛桑也说过,蒙古独特的生活和环境,需要并创造了旋律悠长的歌曲。 然而,这种生活方式正处于分崩离析之中。朝克图说,八十年代把草原按户分了,每家用铁丝网分开,游牧民族从此定居下来,成了笼子里的鸟,不能再自由地迁徙了,人们之间来往少了,关系也大不如前。 莫尔吉胡说:“这些年来草原的生态环境变化很大,沙化严重,让人心惊沉痛。几十年前,都是水草丰美的美丽草原,后来在草原上开矿,大卡车把草原压得乱七八糟,还有很多其他民族的人跑到草原来开荒,进行耕种,对草原的破坏很严重。现在不得不禁牧,有些地方则辟为旅游区。” 他对此深为担心,“草原没了,牧人渐渐离开,过去的节日一旦没有了,长调最后的平台就没有了,长调人才的自然冒出就没有了,现在看不出来,三五十年后肯定会看到后果。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积极主张长调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潮鲁也认为,没有草原生活经历的人确实很难学会长调,即使学会了也很难唱出长调的韵味。 对于申遗成功,大家的心情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长调的知名度提高了,忧的是长调跟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如果没保护原生态的环境,只保护几个老艺人,长调能否保护下来还很难说。 有一首古老的长调是这样描述牧民的迁徙生活的,“沉甸甸的银佛龛/脖子怎么受得了/要走到遥远的胡日策格萨麦/辕中的牲畜怎么受得了。纯纯的白银镯子/手腕怎么受得了/要走到遥远的胡日策格萨麦/拉车的犍牛怎么受得了。”不知这悠久的长调能否受得了这草原的沙化、生活的变迁。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
|
不支持Flash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生活 > 正文 |
|
不支持Flash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市黑马:今日牛股! |
| Excel服务器功能强大 |
| 21世纪狂赚钱--绝招 |
| 韩国亲子装,卖疯了! |
| 1000元小店狂赚钱 |
| 联手上市公司赚大钱 |
| 一万元投入 月赚十万 |
| 18岁少女开店狂赚! |
| 99个精品项目(赚) |
| 治帕金森—已刻不容缓 |
| 夏治哮喘气管炎好时机 |
| 痛风治疗新突破(图)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Ⅱ型糖尿病之新疗法 |
| 高血压!有了新发现!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