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好友苏东坡9
来源:秦朔朋友圈
我最近看到了东坡的弟弟苏辙写的《榆》,内心深处被感动到了,于是这一篇讲讲苏东坡与他弟弟的故事吧。
《榆》为什么让人感动,因为它让我泛起了生命记忆。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榆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内心里就开始不自觉地长了一个孤独、自由、宁静的灵魂。在红彤彤的落日底下,我一个人捡着暮春里飘落下来的榆夹,仿佛是捡起来了诗意和创意的种子,这让人永生难忘。
从那时候起到现在我算是写了二十年了,写报告、论文、诗歌、散文、小说、广告,什么都尝试什么都敢写,虽然没写出什么名堂来,但这显然是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了。我的生命底色再苍凉、寂寞,现实里再有什么动荡和打击,我都始终还有一个稳定的自我认知,永远可以回到那个场景里,获得生命力。
苏辙是这样写的,“凛然造物意,岂复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问直与曲。青松未必贵,枯榆还自足。”
这首诗是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在御史台狱中经历磨难,有了人生中最强烈的对于死亡的恐惧时,他的亲弟弟为了抚慰他的心灵而写作的诗歌。
东坡被捕之后,苏辙马上上书说愿意代兄坐牢。他相信东坡是无罪的,便一直为他鸣不平,又不断用书信诗歌鼓励劝慰他哥哥。东坡在狱中最想与之交流的也是弟弟苏辙,就怕与他就此诀别。还留诗(类似遗言)交给了狱卒。他们两兄弟第一次有了生离死别之感。
解析一下《榆》,其含义是:“秋风吹过,万物凋零,所谓贵贱荣辱就是地势造成的。这只是大自然的规律。青松虽然在秋冬依然翠绿,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高贵,而枯榆在凛冽的秋风中依然可以自足,等待来年。”
身处困境的时候,不要对未来灰心,不要自暴自弃,在逆境里怎么也能活下去,甚至活出尊严,我们要处贱不辱。
苏辙不仅写了《榆》,还写了《槐》——“草木何足道,盈虚视新月。微阳起泉下,生意未应绝。”
好一句“生意未应绝”,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肯定也没那么坏。东坡后来果然在多方迎救下出了狱,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那一年,东坡42岁,苏辙40岁。中年人的人生,是莫测的,若有一人相互扶持,始终相依相伴,心靠的很近,该多好啊。

东坡真幸运,在他64年7个月的人生中,弟弟苏辙陪伴了他33年2个月。一半以上的生命有这个弟弟陪着。如果说现代人生二胎有什么好处的话,大概就是,若是像苏氏兄弟这样做到极致,真是人生之大幸。
他们的相伴真的是长长久久,即便是东坡的人生伴侣(妻妾)王弗、王闰之、王朝云都没有这么长的。最长的王朝云,也只有22年。把周围的几乎所有“可用”“可陪”之人都培养成了知己,恐怕只有苏东坡有这个能力。他的身边从来没有“最熟悉的陌生人”一说,因而不用戒备森严,不用怀疑质疑,该是多么有安全感、信任感的踏实一生。人生的实质和内容,大概就是这样的形态。大部分人对于身边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想的起来的“符号”,然后涂上一层所谓“人生意义”,其实很容易就褪色。
苏轼与苏辙,相差两岁(分别1037年和1039年生人)。他们有好父亲,也有一个好母亲,都辅导他们读书。而且由于家境优渥,父母供得起两兄弟的理想和追求。
苏辙曾回忆,“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两兄弟一起度过了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也有了一起成就功名的美好时刻,成家之后刚开始的生活也是无忧无虑的,他们就这样彼此相伴20年7个月。这个20年是少年时代、青春期,看起来真是不错。人生的底打得好,怎么都够了。
他们第一次分离,是嘉祐六年(1061年)辛丑,东坡去了凤翔府(位于今陕西)任判官,苏辙留在汴京侍奉父亲苏洵。他们从这一次开始就约定以后要早退、要隐居,“同归林下,对床夜雨”,并且时常在往后的诗文中说起这件事。两个人之间有某种约定,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它可以在岁月里打捞起不少月光般的东西。
一别三年,他们才重新相聚。后来一起经历了父亲去世的悲痛。随后,因为两人公事都繁忙,无法经常相处。五年后又分开了。东坡去杭州外派的时候,苏辙去颍州相送,随后的七年间(1071-1077年)始终分隔两地。在这个第二个20年中,他们的官场生涯没有太多波折,只是兄弟俩聚少离多。算一算,加起来有8年左右时间是团聚的。中年人生的初局通常还没有太多波澜,越往后走挑战更大。
乌台诗案发生后,他们之间剩下的另外的22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080年,苏东坡被贬黄州(今黄冈),路过陈州(今淮阳县)的时候,苏辙特意从南京赶来与哥哥相聚三日。后来他还送东坡家小来到黄州。东坡特地跑了20里地来迎接,接着又是四年没见。
人到深度中年总是漂泊,身不由己,苏氏兄弟经历了各种生死攸关、步步为营、变幻莫测的官场环境,但始终相互携手,沉稳前行,共进退、同患难。这14年1个月中,他们相处时间是4年6个月。
到了晚年,两兄弟更是被一贬再贬,聚少离多,在近8年时间里,最多只在一起1个多月。
据统计,东坡涉及兄弟之情的242首诗歌创作中,只有49首诗创作于相聚时,193首都是分离状态。可见,分离和思念总是诗歌最好的温床。他们两个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思念和内心的孤寂。
苏辙的《怀渑池寄子瞻兄》,抒发了思念和孤寂。东坡则回应了《和子由渑池怀旧》,成为千古经典——“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抓,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中年人可能要面对各种离别。人生也就是这几件难事——生老病死断舍离。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别离自己的朋友、亲人,离开熟悉的地方、告别自己熟悉的、习惯的生活方式,而且还不知道别离会再发生多少次,要漂泊多久。对于这对“难兄难弟”而言,更是这样。
由于他们感情太好,别离次数又过多,就为后世提供了很多面对失落和别离的方法。东坡曾写“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理解并接受了“人生如寄”。苏辙写了学术著作《古史》,他认为,百年人生不过俯仰之间,在历史中,风雨和困难都是一瞬间,过好自己的生活只能求诸于己。在他二次被贬时,写过“孤舟适远身如寄,二顷躬耕道自肥。”因为人生如寄,本质上都是无依无靠的,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把自己活好。懂得了这个道理,修炼好了自己,也就光明得道了。
东坡帮苏辙的女儿一个个都安排嫁到合适的好人家,也总是为他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更多时候,他也不是全能的。在精神上,谁都是孤独的。虽然在人生中,可能会有很好的父母、兄弟、朋友、贵人相助,但人最终是自己孤独地走完这一生的,只能闭着眼睛勇敢闯荡。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替代的精神对话者,是稀有的、最珍贵的。
东坡把弟弟当成知己——“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我少知子由,天资和而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苏辙是他的弟弟,更是朋友,是知己,是命运共同体。
人生在漫长的历史与岁月中,真是不足道啊。哪里才是你的家?命运才是你的家。
另外,苏氏兄弟告诉我们,只有思想与生活紧密联系,才能走出困境。精神越是强大,它的外延就越小。自己拥有的乐观是解救的药丸,人生之幸可能在于,总有人可以相互监督鞭笞,做同一类型的事情,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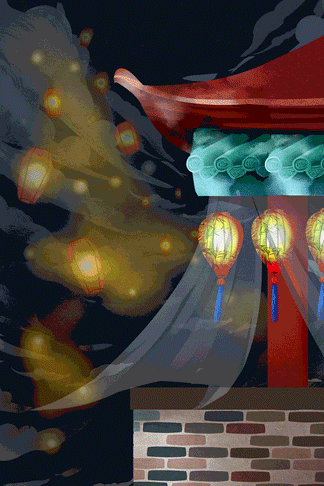
苏辙的才华其实并不比东坡差。少时,他就比东坡沉稳圆滑些,但也容易因为刚直,坚持自己而得罪人,他第一次入仕就遇到挫折,官职化为乌有。但他很快想明白了,专心在京城隐居做学术研究,著书立说。这让东坡很是钦佩。
我们现在最熟悉的是古人的诗词,其实古人看中的是自己的学术研究、解决政事的能力,诗词歌赋并不是文人的主业,只是调剂品。东坡是到24岁才写诗,37岁才填词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真正读得懂词的都是有故事的中年人。
苏辙更不愿意为了写诗而写诗,而他留下的词也只有4首。东坡离世之后,苏辙隐居在颍水边,用心与自己的妻子孩子相处。他在东坡的光芒之下,心态从来是稳定的,一个人有了研究精神和真正的审美情趣之后,是可以自足的。
苏辙从小体弱多病,所以比东坡更关注修身养性,在他的生命排序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能是倒过来的。
东坡很佩服弟弟的研究精神,他在黄州时,曾说“闲废无心,专治经书”。他读了《论语》《书》《易》,弟弟则同时读了《春秋》《诗》。
东坡总是从弟弟的诗文和信为基础,再做些延伸和拔高。这么看来,问题的发现者更具有原创性,是弟弟给了东坡新的启发。他们从小志趣相同,苏辙特别了解东坡的抱负,要实现“当世志”,想成为全才。比如东坡在1064年,27岁的时候夏军攻边境时,他还想去参军带兵。
他们有共同的工作和生活追求,所以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思念、惯性(文学交往和学术探讨)、情绪琐事等等,都可以聊成经典。他们在被贬的时候,都有共同的救赎之道,就是相信道术和禅学。这样,他们可以在做事的抱负和归隐的乐趣之间自由切换。苏氏兄弟于是成为了文化范型。
他们的“乐观”矿藏丰富,可以随时挖掘出来用。比如,对于东坡而言,买不起羊肉可以好好研发猪肉,于是给后世留了“东坡肉”。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他让人明白,用你最好的能力去对付你最差的际遇,用你最好的一面挡现实的子弹,这就是自救。
怎么活得好呢?怎么养自己的气质呢?靠社会实践、游历、向名师请教,跟贤人交往。苏辙说的,心安就气安。
东坡则提出了一个更美丽的概念,叫“身与竹化”。
这个词源自于他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什么意思呢?欲画墨竹,需先胸有成竹,身与竹化,才能画出竹子的神韵,将自己所见化为优美的艺术形象。
所谓审美是不带任何欲求的,带了就有烦恼和悲苦。苏辙晚年经常入定,他获得了那种进入虚静接近无限的生命感受。
身与竹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世界万物皆在我胸中。这样才能不被困境、坏事、痛苦萦绕吧。还是祝大家好。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