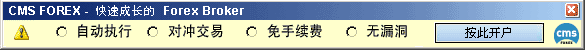从邻居的不幸中学习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14日 16:47 《环球企业家》杂志 | ||||||||
|
改革者们的基本挑战是必须在历史遗产所给定的舞台上跳舞,既要大力推进改革,又不能翻车出轨。要做到这一点,改革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必须极其密切地配合 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改革的目标和结果明显不同,这已是一种广泛的共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西方式的经济制度,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记得曾经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就喜欢引用中俄两国20世纪90年代的GDP增长曲线。那是一对X形的曲线:中国的GDP一路高速增长,俄罗斯则一路下滑。中国的读者和听众很容易读出其中的信息:中国蒸蒸日上,俄罗斯一塌糊涂,“目标和结果明显不同”。几年前,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斯蒂格利茨教授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他那一番中俄比较把在场的年轻的中国听众说得心花怒放,不断博得如雷般的掌声。 中俄的“不同”是惊人的,也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确史无前例,确实值得骄傲。然而,一边校订《世纪大拍卖》的译稿,一边体味着电视里和媒体上的中国故事,我还是感到困惑。 今年二月的《焦点访谈》报道说:“左手倒右手,国有变私有。”山东一家国有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在他们管理的这家企业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私人企业。他们同时经营着国家的企业和自己的企业,做着相同的业务,国家的企业一片破败,私人的企业热火朝天。“一手管两家,左手的钱是国家的,右手的钱是自个儿的,左手跟右手做生意,左手稍微露点缝,钱就全到了右手”,中央电视台的声音显得颇有些无可奈何。 这很容易地让我想起《世纪大拍卖》第四章中的那位“红色经理”杜杰尔尼:他的工厂成为诺沃斯别斯克地区第一家被出售的企业。问题只有一个——杜杰尔尼决意成为企业的新的所有者,以至于他不想让任何法律挡他的路。他系统地将企业的资产价值低估以便利其购买,并操纵了一起“投资投标”,通过这个过程,他把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出售给了一家与他关系密切的公司。 连杜杰尔尼也只是把他的企业出售给了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公司”,而且还得费力气操纵一个“投资招标”,山东那家国企的经理们好像没有费他那么多周折,他们干脆把国企股份卖给了他们自己的私人公司。而且,这显然得到了当地有关政府部门的首肯。电视台采访前不久,上级还不辞辛劳地发了红头文件,不让那个私人企业的一把手继续当国企一把手,而是任命其二把手来当国企的一把手。 事实上,这本书中的很多故事,都让人联想起上大学时学会的那句伟人名言:只要换一个名字,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人们当然可以找到一百条理由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故事与俄罗斯的故事终究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不是纠缠于外在表象而是深入到一些实质性的特征,就很容易发现相似之处。而且,正是这些相似之处,才最令人忧心。 “路径依赖” 《世纪大拍卖》一书所描述的是一个西方主流媒体记者眼中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作者讲述的多是自己耳闻目睹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比学者们的模型更为生动地展示了1990年代俄罗斯经济、社会和政治转轨的悲壮激烈的场景。 1990年代的俄罗斯发生了什么?用作者的话概括说来就是:“俄罗斯创造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却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经济。”作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是私有的(private)经济,却不是一种生产性(productive)的经济;其中有市场存在,但却是被操纵和控制的市场。 这其实也就是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吴敬琏近年来一再提起的“坏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结果是坚信“世界的其他地区现在不可避免地要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趋同”的西方学者和俄罗斯的改革设计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就不难看到,这种“始料不及”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加深的过程。对中国的改革者情况尤其如此。2001年,以“吴市场”的雅号闻名于世的吴敬琏教授承认,“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现在,他认识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 《世纪大拍卖》讲述的,正是俄罗斯如何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滑向“坏的市场经济”的泥坑的故事。这种坏的市场经济中,“大公司掠夺小公司,官员和骗子们掠夺所有的人”。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问题是,俄罗斯究竟在什么地方走错了?这也是作者试图探究的问题。在她看来,最大的错误是叶利钦和青年改革家们为了在1996年大选中胜出而与寡头们进行的出卖灵魂的“浮士德交易”。在这个交易中,叶利钦和青年改革家们以巨额国有资产相赠,换来了寡头们的政治支持,并引狼入室,使寡头们操纵了国家政治,变成了作者所说的“资本家政治局”。 虽然这个“浮士德交易”对寡头集团的兴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全面地观察,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俄罗斯的许多无奈似乎都可以首先归之于经济学家所说的“路径依赖”。表面上看起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俄罗斯顷刻之间走上了一条与我们完全不同的道路。实际上,如作者所说的,“新的制度就是旧的那一个”。叶利钦本人也承认,他的总统府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苏联时代的旧官僚。至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则更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书中一位叫本杜克兹的私人企业家说出了问题的要害。俄罗斯需要的是一个“摩西解决方案”——让这一代俄罗斯人到大沙漠上去呆40年,以便与历史一刀两断。既然这根本不可能,俄罗斯就必须考虑面对现实,它的问题部分地在于它的出发点。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只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改革者们的基本挑战是必须在历史遗产所给定的舞台上跳舞,既要大力推进改革,又不能翻车出轨。要做到这一点,改革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必须极其密切地配合。在俄罗斯,承担这一份历史任务的是青年改革家们和他们的政治领袖叶利钦。然而,他们之间的配合似乎很不理想。作者把青年改革家们称做“麦肯锡革命者”,一再强调他们缺乏自己的政治基础,只能仰赖某一个如叶利钦这样的政治强人来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否则便一事无成。 其实在我看来,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生产改革思想的经济学家和把改革思想付诸实践的政治家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要求改革的思想家都同时是政治家,就像要求政治家都精通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一样,恐怕有些勉为其难。作者没有说出来的、但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是,在俄罗斯社会中,没有形成那种愿意接受并有能力推行他们的改革主张的政治力量。1996年他们和寡头们结盟扶持叶利钦。但是,当他们因坚持自己的改革思路而触动了寡头的利益时,联盟便告瓦解。 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有二:其一,青年改革家们的思想过于西化、过于脱离现实,以至于不能符合俄罗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要求,于是在俄罗斯找不到自己的接受者;其二,他们的思想其实符合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但这个利益集团在给定的政治体制下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或许,这两种因素都起了作用。 青年改革家的局限 历史遗产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意味着改革不可能没有妥协。在俄罗斯也和在中国一样,妥协都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即作者所说的“目的证明手段”。在中国,人们有许多种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如“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理论出发”,“不要照抄西方书本理论”,要有“可操作性”,“水至清则无鱼”等等。 以盖达尔和丘拜斯为首的青年改革派作为激进的休克疗法的罪魁,似乎是那种食洋不化、理论脱离实际的空想家和不顾群众死活的冷血动物。然而,他们的失败又恰恰在于他们过分慷慨地“从实际出发”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1992——1994年的认股证私有化最后实际上是一次内部人私有化。政府提出了三个私有化的可选方案,把选择权交给了“企业”,实际上就是交给了作者所说的“红色经理”们。参加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有2/3都选择了其中的方案2,按该方案,企业管理层和职工加在一起持有企业5l%以上的股份。虽然表面上是管理层和职工共同所有,但实际的结果是西方经济学家后来说的管理层所有制(managerial ownership)。“红色经理”们有无数的办法控制工人手里的股份。 在作者看来,这是对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大的讽刺:由于丘拜斯为推进私有化过程中所达成的政治妥协,旧体制的贵族们,那些红色经理们成了旧体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利益分配,而是如此私有化的企业很难有成功的重组。人还是那些人,机制几乎也还是过去的机制,新的所有者很难有新的资金投入支持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其重组能力如何也大成问题,因为这种私有化完全排斥了竞争。唯一的好处是,这样的方案可以为杜马所接受,从而加快私有化的过程。这一点是实现了。不到三年时间,在私人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从不到1/10提高到2/3。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俄罗斯的经济是变成了一个“私有的”经济,但却没有变成一个“生产性”的经济。 1996年与寡头的结盟是青年改革家又一次“从实际出发”而慷慨地出卖了自己的原则。通过和寡头结盟、操纵媒体等卑劣手段而取得的“胜利”,最后被证明是一场灾难。自由派记者伯格认为,青年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为了民主的腐败”。实际的结果是,腐败是的确腐败了,民主却不仅没有获得,而且被粗暴地践踏了。作者认为可悲的是,“那并不是一种意外付出的代价,而是完全自觉的选择”。不过这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真是完全自觉的选择,就说明这样的错误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改革毫无疑问是一场历史性的利益再分配。如果说俄罗斯转轨的最初几年还是围绕思想而展开的斗争,转轨发动起来之后,“俄罗斯的转型已经不再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再是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与维护苏联传统制度的强硬派之间的较量,而是变成了一场争斗,这场争斗的核心也是一切革命的核心:战利品归谁?” 既然是市场经济,自然要承认私人利益的原则:人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革。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挑战在于,利益主体多元化之后的经济和政治博弈依据什么样的规则。 俄罗斯的寡头现在已经是臭名昭著,但正如叶利钦所说:“他们不是江洋大盗。不是黑手党头目;他们是与国家有着紧密、复杂关系的大资本代表……事实上,大资本对政权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问题的症结只在于这种影响采用了什么方式。” 叶利钦的话应该说是很中肯的。俄罗斯的寡头们本来只是一些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成功首先是得益于他们比较早地觉悟,勇敢地跳进了市场经济的海洋。对很多人来说,这里面也有几分无奈。因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在旧体制中曾属于另类。他们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比别人更善于利用旧体制的漏洞和空隙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当他们的生意大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要试图影响政治。 实际上,民主政治的要义就在于允许人民影响政治,而且人民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有权利为自己的利益而对国家政治施加自己的影响。寡头们当然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事实上,由于大量持有国家财政短期债券,寡头们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而其直接原因就是政府宣布无力支付。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寡头们影响了政治,而在于他们垄断了影响政治的途径或“市场”,变成了“资本家政治局”,造成了西方学者所说的“政府俘获”(statecapture)的局面。 如何能防止出现这样的结局?简单地把民营企业家或其他什么利益集团排斥在民主政治之外,显然是无理的和愚蠢的。真正的出路在于建立一种制度和机制,使所有的公民不论贫富贵贱,都能在影响国家政治方面有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在俄罗斯1996年的大选中,这种制度建设的缺失非常明显。 我们同样面临着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挑战,各种利益集团同样要求对国家政治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其中同样既包括腰缠万贯的富豪,也包括下岗工人、民工和农民。我们同样需要应对一个挑战:如何在制度和机制的层面上保证各种利益集团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对国家政治生活平等地施加其影响? 在这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世界里,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可以在法律划定的框架内公开地为自己的利益而奔走,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可以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要求政府采取或拒绝某种改革措施。但改革者自己似乎是一个例外,他们必须在全民共同利益之中寻找自己的利益,表现出足够的“奉献精神”,才能取得公信力。在这方面,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在俄罗斯,“青年改革派的部分问题是,在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家,他们感觉自己属于他们创造的新俄罗斯人那部分,而不是属于社会其他阶层,而这些阶层的支持对成功地完成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生活在一个10万美元只是‘小钱’的社会圈子里,挣着每月不足500美元的政府工资,青年改革派面临着一种可怕的、个人的两难境地。他们自己的薄薄工资袋和他们暴富的商界朋友之间的对比,使他们的某些人产生了一种痛苦的感觉,或者至少是一种有权利让自己致富的感觉。” 实际上,在改革的过程中,总是可以看到一种情况:大家都认识到某一个体制漏洞,但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有的人致力于推进改革来堵上这些漏洞;有的人抓紧时间趁漏洞还没有堵上给自己捞一把;更有人为了自己多捞几把而昧着良心阻碍别人堵这些漏洞。做合法的但道德不高尚的事情,是某些人自己的选择和权利。 在这样一个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每个人都在新的市场经济中焦急地给自己寻找有利地形的转轨过程中,我们如何激励我们的公职人员?如何保持一支廉洁高效的公职人员队伍?这依然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作者为世界银行高级企业重组专家。本文为描述1990年代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的《世纪大拍卖》一书的翻译札记,有删节 ,全文首发《比较》。《世纪大拍卖》一书将于10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文/《环球企业家》□ 张春霖|文 出自:2004年10月 总第103期)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知识案例 > 《环球企业家》2004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