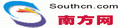严义明:遍缠绷带的中国股市维权第一人
他既为周正毅辩护,也帮助小股民维权;
他从“中国股市维权第一人”,到要求政府信息公开;
在“商务”与“公益”之间,该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如何取舍?
南方周末记者 陈涛 发自上海
遍缠绷带的“中国股市维权第一人”
“我不能肯定他们仅仅是要警告我一下,还是要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个有着典型江南男人长相的律师淡淡地说。
他缠着厚厚的绷带,连挪动一下背后的沙发靠垫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在向记者描述自己五天前所经历的遇袭事件时,他如同在讲述别人的事情,并不时地用一些书面用语,以使得自己的描述更严密、更具有逻辑性。
这就是被媒体冠以“中国股市维权第一人”的严义明。舆论广泛认为,他这次遇袭与长期从事的股市维权有关,并把矛头直接对准某家著名的上市公司。不过,严义明本人则以律师特有的严密和谨慎不愿意对“到底是谁干的”发表看法。
对于被贴上“中国股市维权第一人”这个标签,严义明本人似乎也并不非常认同,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位代理公众投资人、向弄虚作假的上市公司索赔的律师,并因此于2002年被美国《商业周刊》杂志评为当年度的“亚洲之星”(这一年,他代理的中国第一个股市索赔案终于得以了结)。他在这个领域做的案件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红光、银广夏、大庆联谊、科龙、石油龙昌、东方集团、长征电器、银河科技等等。
按照严义明自己的表述,股市维权只是他称为“公益性法务”的一部分,而且,他现在已经把自己的“公益性法务”的重点投放到环保、政府信息公开上去了。“股市维权现在法院已经开始受理了,而且也有很多的律师跟进,我可以把更的精力投放到其他公益性案件中去。”他解释道。
在国外,通过“集体诉讼”(“Class action”,即只要有一个人发起诉讼,诉讼结果将适用于所有相同利益受损者。这会导致最终的赔偿金额高得惊人,比如2002年10月,洛杉矶法院曾裁决菲利普·莫里斯公司280亿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向上市公司索取巨额赔偿,这几乎是律师最为赚钱的一个途径,但是,严义明却把它当一个“公益性法务”来做,不收费或者少量收费。这当然跟我们的司法环境有关。以严义明代理的红光案为例,该案历时整整四年,中间经过了非常多的波折,最后的结果是,11名原告总共只获得了22.5万元,对于动辄按照每小时数百美元标准收费的律师来说,如果不是出于公益目的,很难坚持做这样的案子。
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到政府部门信息披露
如果说股市维权还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收取一定的费用的话,那么严义明现在从事的环保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就很难获得一分钱的收益。
今年1月,他专程赴北京,向财政部和发改委递交申请,要求财政部在“两会”前公布2008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及2009年的财政收入、支出预算。
要求发改委公布四万亿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内容:哪些省市递交了申请,具体都申请了哪些项目;资金来源以及具体项目选取的原因,投资预算;实时公布资金使用的过程。
这两项信息公开申请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严义明表示,他还会持续跟进这个事情。
此前,他曾就环保问题与安徽省有关部门进行了十多次交锋,历时两年。
去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中,他又向国家质检总局和卫生部发出申请,要求它们公开相关信息:国家质检总局是如何认定三鹿奶粉“免检产品”的?卫生部是否在第一知晓时间采取合适的对策?
这样的工作有点类似新闻记者,它的产品是公共性的,申请人个人无法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如果没有当律师,我一定会去做一名记者。”严义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然了,律师的执业经验也给了他这项“公益性法务”很大的帮助。为他提供主要法律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2007年4月5日发布,2008年5月1日开始正式执行。
记者遍查严义明所申请公开的所有信息,几乎每一个主张和要求,无论听起来多么大胆、多么超出普通人的“常识”以及官场的“潜规则”,都能获得该条例明确的法律支撑。
按照严义明的介绍,他介入“政府信息公开”这个领域多多少少有一点偶然。
在决定暂别股市维权之后,严义明最初选定的另外一个“公益性法务”领域是环保。当时,中国华北的一座城市被一家国际环保组织评为“世界最脏的城市”,此事对他震动很大,于是把环保问题列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并亲自到了那个城市。
“去了那里才知道,尽管研究透了环保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但是,事情根本没办法做。”严义明说,“在法律上,关键是要有证据,可是我取的污水样去有关部门,人家根本不做检验。”
就在这个时候,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了,这让他找到了从事环保问题的一个重大法律依据:环境问题是该条例规定的重点信息披露内容。
在研究信息公开条例过程中,严义明又发现,除了环境问题,很多以往认为“敏感”的信息,都是该条例明文规定政府应该披露的,于是,促进政府信息披露本身成了他“公益性法务”的重要内容。
在“公益”和“商务”之间
尽管从事了非常多的“公益性法务”,严义明的“主业”还是他称之为“商务性法务”的工作。
“总要谋生吧?”尽管身体有伤,他仍带着笑说,“现在的时间和精力安排大约是一半一半吧。怎么兼顾呢?”他自问自答,“我的办法就是延长工作时间,以前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12个小时,最近几年身体有点儿吃不消,但是还是坚持12个小时。”严义明今年46岁,拥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
他从“商务性法务”能获取多少个人利益?“公益性法务”是否是他个人打品牌的一种方式,以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
“我个人的法律服务收入连续多年在中国律师界都应该是前100名吧。”他如此作答。在记者进一步要求下,他给出一个数字范围量化了“中国律师界前100名”,那是一个高得足以令普通人吃惊的数字。
早年留学日本的经验使得他成为上海第一批精通日文的律师(即使现在,这种律师在上海也比较稀缺),而随着日本企业大批到中国投资,对相关法律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使得他的“工作多得做不过来,根本不需要通过公益行为来宣传”。
相反,由于所做的“公益性法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监督政府部门,而外资企业并不愿意自己的律师是这个形象,他因此丢掉了一些多年的客户。
不过,严义明并不担心生意。无论是当年作为上海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还是后来自己出来开业,严义明的“商务性法务”的收费都不低。一个例子是,他曾是周正毅的辩护律师。他说,“那个案子可不是公益性的,我收取了费用,而且收费标准还不低。”
那么,支撑严义明长期从事公益性服务的动力是什么呢?遇袭之后,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文解释:
“我知道,从事维权,对绝大多数律师来说,是公益或者半公益性质,期间耗费了很多精力、成本,甚至还要遭受人身威胁,暴力行凶。而能够支撑他们继续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内心中难以磨灭的信念。”
在接受采访2个多小时里,每当谈到从事公益性法务的原动力问题,这个46岁的“老男人”都会追忆自己年轻时候的理想:在读法律时,把社会公正(Justice)看得高于一切;在个人价值观上则是“人格独立,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他甚至提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在谈这些事情时,他眼里总是闪烁着光芒。
而尊重法律,在现有的法律和规则框架下做事情,推进到能够推进的地方,这是他做事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说,“我们缺的不是好的法律条文和制度安排,缺乏的是对法律和制度的尊重。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就很好,关键是怎么把这种制度落到实处。”
(杨海鹏对此文亦有贡献)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