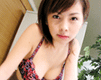中国科技财富:11号文打击资本外逃误伤红筹股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5月09日 15:59 中国科技财富 | ||||||||
|
文 张亮 2005年1月24日,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了《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称为“11号文”)。这一规定的出台主要源于商务部上报国务院一份题为《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四千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大约五百多亿美元的资金
11号文相当有针对性的对资本外逃通道加强了监管力度,在注册境外企业、资本注入、并购境内资产这几个主要环节都有一些新的规定。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规定甫一出台便引起金融界和部分媒体的争论,其焦点在于:这一刀落下,在堵住资本外逃通道的同时也封杀了中小企业海外融资的快捷通道——红筹股上市。 红筹股现在一般指在海外注册、海外上市而主营业务在中国大陆的股票。实际就是间接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 2003年证监会取消“无异议函”制度后,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迎来一个新的高峰,IPO的数量为48家,筹资金额约70亿美元;2004年的数量为84家,筹资111.51亿美元。截止2004年末,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的情况如表1。 统计表明,2003、2004两年中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占到目前海外上市总量的79%,而其中绝大多数都采用的红筹模式。 从筹资额看,2004年深沪两市发行的98只新股共筹资353.46亿人民币,约42.7亿美圆,不足同期海外上市筹资额的40%。 再打开各交易所红筹股的名单,石油巨头中国海洋石油;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游戏新贵盛大网络,电信巨子中国网通全都赫然在目;囊括其中的还有华润、中信、中远、光大、粤海、招商局、越秀等国内超大集团的分拆企业;加上中国粮油国际、中航油、联想……如果需要,这个名单可以很长,而且每一个名字份量都很重。 这些数字和名字已经表明了红筹模式存在的意义,但11号文的出台却为这一段辉煌打上了一连串的问号:打击资本外逃为什么会“误伤”红筹?红筹之路真的被完全堵住了吗?以后的红筹该怎么办? 11号文打中了什么? 资本外逃的手法千奇百怪,这里不作详细介绍,但有一些基础的共性还是可以把握的。比如:资本会最后流向策划人完全可控的境外企业;过程中必然包含将资金从境内流向境外和反向收购境内资产两大环节。 沿着这一思路看11号文,就会发现这一通知的针对性极强。第一条实际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的补充。因为《管理办法》第二条中明确说明针对的是法人机构,对个人是空白。而离岸公司的特点是公司的股东可以是一个人,资料保密,使个人行为可以取代公司行为。因此11号文强调了“境内居民”而非“境内公民”这一概念,将监管范围扩大。 第二条至少有两点可以注意。一是重申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加强了审批程序。在过去一直有“商务部审批,外管局开户”的说法——对外项目经过商务部审批后,在外管局开设外汇帐户,外管局的监控就是通过对帐户资金的进出进行,明显是一种事后监控。某投行人士表示,在11号文出台前,商务部审批过的项目很少被外管局再审。而现在外管局的监控职能被大大强化。特别是境内居民通过外资企业收购境内资产时,不仅要说明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还要上报到总局批准。二是监管了并购过程中的转让价格,根据《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八条,并购价格必须是经过评估的。但据介绍,原先的评估对于国资比较严格,而非国有资产的评估往往只是流于形式。使得不法分子在侵吞国有资产后可以轻松的改头换面,流出境外。 第三条明确指出了并购过程中,“同一管理层”的企业将被严格审批,审批流程中更强调要“审查并购合同以了解实施并购的境外企业是否为境内居民所设立或控制”。结合第二条,显然是希望通过控制关联交易来扼杀资本外逃的途径。一系列采访表明,也正是这一条,在红筹上市的路上设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四条是针对已完成并购过程的企业。它的意义除了补充完善外更近于宣告了一种态度,表明了管理层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决心。 可见11号文目的就是监控境外注册、资本注入、并购境内资产这几个资本外逃的主要环节,不再是出了问题事后回来翻证据,而是希望早发现,早制止。但是它不是从“黑钱”产生的根源入手,而是先解决资本外逃的途径。 尽管11号文并非为了“堵住红筹之路”。但实际操作中,红筹运转模式确实受到波及。“外管局的通知下发后,公司的几个项目都先停了。”一家咨询公司向我们说。他所指的项目就是几家企业准备用红筹的方式在海外上市。 借壳到造壳 红筹模式的演变 海外上市融资之路无非两条:直接上市或间接上市。 直接上市要迈过“456”的门槛,即净资产不少于4亿元人民币,上一年度的税后利润不低于6000万人民币,并显示出有增长潜力;按合理预期市盈率计算,筹资额不少于5000万美元。这些数字的来由无从探考,但普遍的反应是“太高了”。尽管有对于特殊情况证监会可以豁免,就是适当放宽的说法,但“豁免”本身就是破坏规则的行为,而且豁免的标准不明确,希望不能寄托在这上面。 间接上市通常有造壳、借壳两种形式。 借壳上市实际上就是指买一个已上市的公司,用再融资的方法募集资金,或注入资产,实现资本运作的目的。80年代末越秀集团、粤海集团的在港上市都用的这种方式。90年代初中信收购泰富更是把这一模式推上了一个高潮。它的过程非常简单:泰富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1986年上市。同年2月,向中信香港定向发行2.7亿股新股,从而使中信香港持有泰富64.7%的股权。自此,泰富成为中信的子公司,初步完成了借壳的过程。从1990年起,中信香港将属下的工业大厦、货仓、港龙航空股权、国泰航空股权及澳门电讯股权等资产不断地注入中信泰富,令中信泰富跳跃性地实现资产扩张和实力壮大。1991年该股票正式更名“中信泰富”,完成“上市”步骤。 之所以选中信泰富作为这一模式的代表,一是因为它在买壳过程中用定向发行的方式成功解决了买壳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成本过高。二是中信大规模资产的成功注入确立了借壳上市完美流程:中信香港将属下的资产及业务出售给中信泰富,从中信泰富手中套取现金用于购置或发展集团公司的新资产及新业务,中信泰富则利用其上市地位不断地从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来收购这些资产,以此来实现集团公司的资产套现——“资产从中信香港流向中信泰富;资金从证券市场流向中信泰富再流向中信香港”。从而一度激发了香港市场对红筹的追捧。 这一成功范例使得早期的香港红筹股中大量是以借壳的方式运作的。其优点在于可以规避初始上市的一系列法律程序,避免了复杂甚至是艰难的企业“包装”过程,节约时间。 到上海实业、北京控股在港上市,忽然发现可以借用在港的窗口企业。虽然增加了一些时间和成本,但和融资额比就不算什么了。对这一方式的探索逐步演化出现在最常用的红筹模式——造壳上市。 对此,嘉富诚资本研究有限公司郑锦桥董事长为我们简单讲解了流程。 国内企业要到海外上市又不能满足“456”的条件的,往往在海外注册一家公司作为上市主体,通过控股国内企业达到上市目的。过程经过几个环节: 一、注册地的选择。理论上来说要注意注册所在地的财务准则是不是通用,有没有产业政策限制等方面的问题。但普遍情况下受到的限制很少,在海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都可以的情况下为自己谋求一些顺带的方便也是可以理解的,注册手续的便捷,费用的多少,经营的方便,还有税收上的优惠。综合之下,离岸金融中心成为多数企业的选择。 二、海外企业的资金来源。初注册的海外公司只是一个空壳,让他运转起来第一笔资金就很重要。直接将资金打过去要受到外汇监管,也很难解释哪里来的那么多外汇(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基本无法逾越,而大国企不在讨论之列),于是就有了资金离境的种种通道。 一种方法是走桥公司,这种公司一般境内外都有业务,在境内付给桥公司人民币,从桥公司在境外的企业收回外汇注入壳公司,中间桥公司会收取“手续费”。至于他的钱怎么走的,据说是“自然有办法”。想来资本项目下或贸易项目下均可,但走贸易的方式有沉重的税。反正最终成本加利润都在“手续费”里。这一方法优点是不管代价多高钱能出去,缺点是中间总有点“灰色”的味道。 另一种方法是找投资,比如蒙牛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蒙牛的上市过程说起来比较复杂,但最能说明这种模式。 它的整体架构分3级:最上端是由国内管理层、投资人、关系人等组成的金牛公司和银牛公司。第二层是蒙牛开曼群岛公司和毛里求斯公司。第三层才是蒙牛的国内主体。开曼公司和毛里求斯公司在初设立的时候是没有资金的,于是蒙牛管理层找来了摩根、鼎辉、和英联三家海外战略投资者(MS Dairy、CDH和CIC)投向开曼公司。蒙牛与三家投资者的股权划分很有特点:金牛和银牛分别出资1134美元、2968美元的价格认购了开曼群岛公司1134股和2968股的A类股票,而三家投资商分别出资1733.2705万美元、550万美元、314.1007万美元,买下了开曼公司90.6%的B类股票。双方规定1股A类股票有10票投票权,而B类股票只有1票。意思是说实际控制权还在蒙牛。之后开曼公司拿募来的这2597.37万美元认购了毛里求斯公司全部股份,毛里求斯公司再拿这笔钱从蒙牛股东那里收购了国内蒙牛66.7%的股权,初步完成了股权架构的调整。之后在香港上市的主体就是就是开曼公司。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每一步都很正规化,但缺陷也不少。一是投资方不好找,不是所有想上市的小企业都象蒙牛一样有前途,吸引外资的基础不足。二是即使找到投资方,条件也一定很苛刻。别人千百万美金不会只想买你的空壳,你又不得不需要他的钱,结果可想而知。比如蒙牛在香港上市,境外投资商的作用不言而喻,但他要的也不少。如果有选择,牛根生肯定不会选择以7830万股权为代价的“豪赌”。换一家企业,谁敢赌自己连续三年50%以上的增长。蒙牛赌赢了,但投资方还是赚的盘满钵满。三家外资机构于2002年6月对蒙牛作出2597万美元首轮投资,再于2003年10月作出3523万美元的次轮投资,共出资6120万美元,折合港币约4.77亿元,蒙牛上市已先为他们套回3.525亿港元,余下的1.245亿港元投资,换来当时市值3.88亿港元的蒙牛股票。 三、并购国内资产。没有资产和业务的公司是上不了市的,国外企业拿到钱还要买进资产,充实业务,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原先这方面的监控比较松,正常商业行为,你愿买,我愿卖,基本商务部批了就算成功。但现在不行了。上报到外管局意味着对资金来源和用途要有合理解释,靠灰色通道出去的钱难以使用;对收购价格要合理评估,很多手段无法操作;最为难的是强调了“同一管理层”、“实际控制人”的概念,这是真正的“绝命一枪”。 德恒律师事务所郭克军律师曾参与过新浪等多家企业的海外上市过程。他为我们指出了11号文关键所在: 11号文附件《外资并购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登记操作规程》中,写明报到外管局“书面申请中应包含以下申明文字“本公司的外资新股东与出让股权(或资产)的原中方股东之间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和资产关联,也不存在其他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内部交易行为,本次交易的相关支付结算安排均遵守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的规定。如存在虚假陈述,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或如实表述公司外资新股东与出让股权(或资产)的原中方股东之间存在的直接或间接的股权与资产关联关系。” 就是说想完成收购的企业要么声明国内和国外企业间是同一管理层或有关联关系,那就要受到严格的审查;要么就睁着眼说瞎话,境内外的企业没关系。但你的目的是上市,上市时各交易所都有类似规定,要求律师事务所出据材料证明“该企业没有违反所在地国家的法律的行为”。这就把中介推到了前台。原先国内没有要求就“同一管理层”问题在材料中明确说明,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做。现在逼着你“宣”了,不如实说明就有了“违法”的味道,律师事务所不愿为此负责,上市就缺了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 即使能解决这一难题,根据去年10月发改委颁布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境内投资主体及其通过在境外控股的企业或机构,在境外进行的投资(含新建、购并、参股、增资、再投资)项目的核准,与外商购并境内企业等各类外商投资项目的核准均需要按不同资金规模上报国家及地方发改委。” 根据这些新规定,首先,以个人名义在境外设立公司要到外管局审批;其次,以境外公司并购境内资产,要经过商务部、发改委与外管总局的三道审批。三堂会审之下,企业只能感叹过关不易。 红筹的漏洞在于造出监管空白地带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虽然11号文本意并不针对红筹市场,其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可能表现在一、审批程序的复杂化,拖延时间,增加成本;二、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项目会暂停,打断原订计划;三、今后的审批标准不确定,是全部停、还是针对性的停、还是有更细化的标准,都需要看新的发展。四、即使不堵死红筹上市的路子,但有些区别对待将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注册在离岸金融中心和注册在法规比较严密国家的企业;股东的国籍、身份;股东结构比较单一和结构比较复杂的企业;资金来源、用途比较清晰和比较模糊的企业等等。 我们知道,红筹模式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本质还是一种绕过我国金融管制政策的手段。境内企业用红筹模式上市,决定了它必然会完成一个大跨度的身份转变,拥有了两个新的身份。一个身份是海外上市公司,对它的监管由上市所在地交易所和监管部门进行,而且只针对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另一个身份是外资企业,对它的监控权转到注册地所在国,因此数以万计的企业选择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就是让这个身份受到的约束更少些。而国内对这两种身份都无法监管。明明是中国企业,却处于国内的监管空白点,这就有了极大的漏洞。 红筹股中出现过欧亚农业这类的不良范例,也有超大农业、中国稀土等遭受财务造假质疑,虽然是一些个别现象,实际原因是什么也可以探讨,但至少说明这个空白点是存在的。近期的中航油事件、创维事件也印证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强力政府,管理力度是一个问题,但不应存在管不到地方。 是什么催生了红筹模式? 中国证监会曾表示“鼓励直接上市,不提倡间接上市”,但红筹上市依然迅猛发展说明了企业对海外融资的渴望,也说明直接海外上市的通道并不通畅。“456”的高标准为的是保证海外上市企业的质量,但现在大量的重型企业踏上红筹之路已经说明这一功能趋于弱化甚至消失,它的意义何在? 一方面,“456”用高高的门槛挡住了大量有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控制了海外直接上市的通道。但这是不是他应尽的功能,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什么样的企业能上市,各交易所根据自身情况都有详尽的规定。我们有什么理由越俎代庖帮别人把关?即使真有这个必要,上市条件是简单的“456”能够囊括的吗?“456” 的条件偏重于盈利指标,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在香港主板市场为想上市的公司提供了盈利测试、市值/收益测试、市值/收益/现金流量测试三个标准,满足其中一个即可;新加坡主板也有三种标准可选择,3年累计赢利750万新元的准入条件成为吸引大量中资企业的重要因素。交易所都不要求那么高的赢利水平,境外投资者也不为此苛求,我们却自己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另一方面,那些能够满足“456”的大企业也未必选择直接上市的途径,比如我们文章开头列出的长长的名单。对于很多企业来讲,融资,已经不是上市的唯一目的。对某些企业而言,寻找国际战略合作伙伴远比寻找投资方更为重要,有一个境外企业的身份有时更为方便。再比如三大门户网站,作为内容提供商,受产业政策限制,不能直接海外上市,不作红筹,他们的融资需求怎么满足? 靠国内资本市场吗?抛开承受力不谈,在海外上市还有国内市场暂时难以比拟的优势,例如周期短,成功率高,一般1年内可以完成全过程,而国内市场的周期通常在2-3年;再如再融资灵活性强,难度低;金融衍生品种丰富;易于寻找战略投资者;发起人禁售期短等种种因素。综合考虑,国内证券市场竞争力已远远不如海外市场。 因此,海外上市的需求是挡不住的。而正是海外直接上市不通畅,才会有种种间接上市模式的诞生。借壳也好,造壳也好,都是市场用自己的标准对正常渠道作出的一种修正,这就是红筹模式诞生的根源。既然是修正,总有不被正规渠道所承认的地方。但不调整自身,靠“堵”能堵住吗? 红筹上市面临手段创新 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也意味着无数对策的诞生。一位投行人士表示,“现在虽然多了很多阻碍,但还是有办法绕过去的”。这个结果很让人悲哀。企业之所以选择红筹上市,就是因为时间短、成本低。他们如果能绕过去,那些不计成本急于外逃的资金大概也未必控制的住。11号文颁布后,外汇监管体系加强了、完善了,但是不是真的能堵住资本外逃的通道,还存疑。 关于“绕过去”的具体手法目前还没有谁愿意透露,或者新环境下奇货可居;或者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谈不上“有效手法”。但对这个问题关心的大有人在,往往片言只语就能引发不少联想。 有人提出“民企老板中国公民身份换成外国国籍”的方法。在我们参与的一些讨论中被称为“理论上可行”。因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个人移居境外后,其境内的资产产生的收益,可以持规定的证明材料和有效凭证向外管局指定银行购汇汇出或者携带出境”;“驻华机构及来华人员的合法人民币收入,需要汇出境外的,可以持有关证明材料和凭证到外汇指定银行兑付。”这样资金、资产出境就有了合法渠道。至于境外注册,对于外籍身份更是不成问题。但也有几个难点:1、上市要考虑时间成本,如果已经是外籍身份当然好,否则现在开始办移民一方面有不确定因素,一方面时间不好把握。如果拖个两年,再加上包装上市的时间,不如在国内市场排队算了;2、11号文强调“境内居民”,这一概念不仅包括中国公民,也包括定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以及在中国境内居留满一年(按申请人护照上登记的本次入境日期计算)以上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同胞。这就是说对于长期居留国内的外籍人是不是也受政策制约,监管会到一个什么尺度搞不清楚。但如果为了上市要跑到国外定居就是一个玩笑了。所以说,这个方法只要足够的时间作代价是可行的,但对于以上市为目的的企业而言,只是“理论上可行”。 也有业内人提出“资产桥公司”的概念。通过前面对目前红筹流程的分析可以看到,境外注册和资金出境都是有办法解决的,难点在于如何用境外企业收购境内资产的同时回避严格监管关联关系的问题。既然资金有“桥”,资产是不是也可以走“桥”呢?简单说,就是用无关联境外公司收购境内资产,这样在申报外管局时就不存在“同一管理层”的问题。第一次收购完成后,再用自己的境外公司收购无关联境外企业,或收购股权,或买回境内资产都可以。境外企业间的交易,不受国内法律监控。如果需要,可以搞成多次收购。但这也有问题:一是过程中风险太大,由于不可控,资产随时有易手的可能,即使成功成本也不会低;二是最终依然取决于中介机构的评判尺度。即使收购过程搞的再复杂,最终还是会回到关联企业的关系,这样算不算违法行为,律师等中介会有自己的标准。如果中介不愿向交易所出具证明文件,一切都是无用功。而中介的评判标准无疑是根据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以及态度在不断调整的。这也是现在红筹模式暂时陷入停滞的原因之一。 这些只能算是一些猜想,但不可回避的是红筹手段创新势在必行。 一切都是过渡 从一家不愿透露身份的中介机构了解到,11号文出台后,还是有企业按程序申报材料,但基本没有回复。红筹上市显然处于僵局。 其实我们无须为此担心,市场会为供需双方找到适当的出路。从借壳到造壳,成本和资源的制约已经促使红筹发生了一次演变。只要海外融资的需求存在,海外直接上市的通道不改进,红筹还会为自身找到一条合适的演化途径。只不过这次演化是自上而下的。 嘉富诚董事长郑锦桥先生在我们采访的最后表示了一个很乐观的态度:“现在的种种审批都是建立在人民币不能自由流通的基础上的,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是可预期的目标,如果实现就不存在现在的这些问题。甚至只要实现正在被讨论的“香港自由行”,人民币能够自由进出香港,现在的一些管制措施都没有意义了。从这个角度讲,11号文只会是一个过渡性措施。” |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证券要闻 > 《中国科技财富》2005 > 正文 |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怎样迅速挖掘网络财富 |
| 短线最大黑马股票预报 |
| 海顺咨询 安全获利 |
| 开风情布艺店生意火爆 |
| 首家名牌时装折扣店 |
| 如何加盟创业赚大钱? |
| 05年具有潜力好项目 |
| 开麦当劳式美式快餐店 |
| 开冰淇淋店赚得疯狂 |
| 美味--抵挡不住的诱惑 |
| 新行业 新技术 狂赚! |
| 投资3万年利高的惊人 |
| 1000个赚钱好项目联展 |
| 05年投资赚钱好项目!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