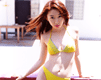高西庆诊问证券法修订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13日 17:07 《商务周刊》杂志 | ||||||||
|
“我们都希望每次修改都有所进步,达到帕雷托优化,至少有点进步,而不是恶化。我觉得这次《证券法》修订草案达到了这个目的” 记者 宁南 商思林 在股市一派“六月飞雪”的萧索奇观下,《证券法》的修订攒足了市场的注意力。
比较美国《证券法》从出台到首次大的修改长达42年的时间跨度而言,中国《证券法》时隔7年就来一次大面积“修车补胎”,不禁令人困惑,是这世界变化快,还是我们的《证券法》“保鲜技术”太失败? 事实上,法治环境差一直是中国证券市场难以茁壮的隐疾,而其中法制建设不足也被认为是这个市场发育不良的病因所在。在上证综指直坠1000点的严峻景况下,赶在《公司法》修订之前修订《证券法》,或多或少被市场和监管部门寄托了一种迫切的“振市”期望。 5月19日,就此次《证券法》修订的诸多疑问和难点,《商务周刊》专访了深谙这场修订历史背景的权威人士——曾任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美国杜克大学、清华、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高西庆。 曾经担任过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的高西庆首先看到的是,这次修订终于在几个关键部位进行了较为准确的“补位”,其中,诚信义务(他称作为“受托人义务”)和赔偿责任的明确,最被这位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先驱”所赞赏。 没有诚信就没有证券市场,高西庆认为,这次《证券法》修订在建立诚信制度性建设方面增加了一些条款,使我国的证券市场无论在发行、交易、结算、信息披露等方面都有了进步,为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曾经是华尔街执业律师的高西庆希望,此次修订能让他在证监会的前同事们在监管时少一份自己当年的尴尬。 另外,明确民事赔偿责任也是此次修改草案里很重要的一条,在市场交易中规定了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三大类禁止行为,并明确提出,如果这些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高西庆认为,以前很多这类的案件不能判决,就是缺乏法律的支撑。 不过,高西庆进一步认为:“既然明确了民事赔偿责任,那么就应该允许集团诉讼。”因为监管机构毕竟精力和财力有限,必须依靠和激励真正受伤害的人,也就是中小股民自己去诉讼。他认为这是当前法律、司法制度未尽的一大遗憾。 “只有真正受伤害的中小投资者,才是可以依靠的无所不在的强大监管力量。”高西庆说。 作为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高西庆谙熟美国《证券法》。“美国《证券法》只有薄薄一本,”他向记者指了指身后书柜中足有十几厚的解释条例说,“但它的规则非常厚,美国证监会几乎每周都在修改和补充。”在这位美国律师协会会员看来,无论是《证券法》的制定和修订,都不应该忘记这是一本大法,注重的是原则而非细节。 高西庆指出,尽管此次修订总的来说是一种进步,“有总比没有好”,但更多属于法律技术性进步,失于其繁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证券法》的稳定性。他坚持,市场有市场的智慧,会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 高西庆是急性子,讲起话来不喘气。无论是多年的留洋生涯,还是丰富的从政经历,似乎都没能改变他当年在川陕大山里修铁路、打锤放炮熏陶出的耿直脾气。 “《证券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虽然面对的是一个窄众,但牵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它的起草和修改,应该在它所能影响的更广范围内进行。”在高西庆看来,原来是部门立法,现在增加了人大法工委,是一个进步,但还不够。他说:“应该把所有不同脾气、不同路子、不同利益的人放在一块讨论修订,这个法的基础才能真正坚实。” 迟来的“补丁”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此次修订有哪些突出的亮点或者说成绩? 高西庆:首先,在上市公司质量问题方面,最重要的修改是明确了诚信责任(我想更准确地应表述为“受托人义务”)。我们为此鼓吹了很多年,在制定《公司法》时曾坚持一定要写明诚信责任,但一直没能明确。所以,当年上海嘉丰实业的大股东偷偷摸摸把国有股卖掉的那个案子,尽管被认为属于严重的大股东、董事违反诚信责任,证监会却难以据此追究大股东、董事长的责任。 其次,一个突出的修改就是民事赔偿责任的明确。现代社会里,法律机制要特别具体,尤其是赔偿责任,罚多少钱,判多少年,判罚依据一定要清楚,这次明确非常好。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既然明确了民事赔偿责任,那么就应该允许集团诉讼。 当初在证监会时,我们和最高法院谈了很久,指出虽然给了股民这个权利,但还只是画了一张饼,希望能够把允许股民真正行使其权利的机制写清楚。司法部门说不行,担心到时候所有人呼隆呼隆地过来告,影响稳定。我说这是影响所有人根本利益的矛盾,你必须想办法解决。 但最后,银广夏、郑百文等几百个案子还是一直没能进行下去。虽然看起来股民不上街、不游行,可这也说明股民对政府的信任产生了疑问,这是一个长远的损失。我们必须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投资者进行民事诉讼,因为监管部门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有真正受伤害的中小投资者,才是可以依靠的无所不在的强大监管力量。 《商务周刊》:此次修订特别强调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甚至规定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这是不是也是一个突出成绩? 高西庆:我觉得提出建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是很应该的,但并不一定要写在《证券法》里。证券保护基金很多国家都有,我们国家也需要这样一个机制,不过,应该清楚这个机制的建立有一个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为了公平,让投资者高兴,那就让他们无论投资哪家证券公司,钱最后都能百分之百地拿回去,那么大家都无所谓了,这就会出现道德风险,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就没有了。 在美国市场,如果一个金融机构破产,投资者要想从保护基金拿回自己的存款或保证金,各种复杂程序最少需要一年才能实现。这就要求投资者要为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你当初为什么放着好证券公司不选,选一些业绩不好的证券公司?还不是它们给你了很多“免费的午餐”嘛。妈妈从小就告诉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仍然去选择这个,就应该自己负责。这一点,立法者应该心中有数。 《商务周刊》:草案新增29条,修订95条,删除14条,修补面达到138条,工程可谓浩大,这些修订的效果您如何评判? 高西庆:这次具体的修改很多,也是一个突出特点,有积极的一方面。例如,高管任职资格原来也有,这次细化了;明确了大股东的资格认定;对大股东贷款、担保责任进行了重新修改等等。这些改动都是积极的,其他国家对此都有相关的规定。 但也应该清楚,法律很死板、很生硬,条例写得越多,问题可能出得越多,因为现实生活中创造出的问题远比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得多。所以证券市场法律环境健全的国家,很少把一些细致的规定写进《证券法》这种大法里,这会大大损害大法的灵活性。 比如上市公司给母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问题。其实在经济学上,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并非绝对不可以做。因为市场上就这些人,把他们都排除出去,利益的相关者没有了,谁来做这个市场?又怎样产生效率? 再比如,草案中为了防止证券公司挪用资金,规定资金必须由银行托管。但从国际市场经验来看,资金放在证券公司还是商业银行并没有惟一正确的答案,即使坚持放在商业银行,它和证券公司之间关系仍然可能孳生许多问题。 其实,《证券法》只要做出不许挪用的规定就可以了,至于怎样具体操作,市场有市场的智慧,完全有能力自己做出选择。所以我认为,此次一些修订不需要搞得绵密详细,许多问题让具体的监管部门、交易所,甚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来做,可能更有利。否则将来与现实发生矛盾,《证券法》改来改去,不但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大法的权威也会受损。 《商务周刊》:修订者好像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涉及“分业经营、现货交易、融资融券、国企炒股、银行资金入市”5个有争议方面时,进行了“但书”处理。 高西庆:这次修订使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这种“但书”,应该是一个进步。至少市场需要,证监会鼓吹鼓吹,领导同意就可以弄,起码不用改大法,不至于发生为了搞创业板,情急之下全国人大把《公司法》最后一条做出修改这样的尴尬事件。 但也要认识到,中国证券市场是从上至下,政府主导的市场。《证券法》也难以脱离开这样一个机制或者环境。我前几年研究发现,世界上104个有正规证券市场的国家中,除了中国和越南,绝大部分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都是从下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很多权责不需要写在《证券法》里,因为他们认为权力与生俱来,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许可的,国家没有权力随便禁止。 但是我们国家的政府部门在传统上不太接受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法律没有规定就是不被允许。证监会没有说让你做衍生品,你就不可以做衍生品。比如《证券法》规定,只能进行现货交易,一句话就全顶死了。我们当年搞《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其中也有一个类似“国务院特别批准”的但书,但出台《证券法》的时候被删掉了。 其实,中国《证券法》的不少规定,都属于市场范围内,不是政府应该天天琢磨的问题。政府管好自己能管的、应该管的事就行了,干吗要去管本来自己管不好的事情?那只能增加寻租的可能性,结果无非是给官员提供一个贪污受贿的机会而已,市场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多少缺失仍然遗憾? 《商务周刊》:修订草案增加了监管机构的执法手段和权限,但不少意见认为证监会的权力已经够大了。 高西庆:我在证监会这么多年,一直认为证监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当“警察”,而不是审批这个审批那个,搞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关注股市的涨落,操心哪个利益集团赚了钱,哪批投资者陪了本——那都是“市场”的功能,或者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责。可是证监会最重要的“警察”权力却很少,不重要的资源分配权力却很大。现在,证监会把80%的精力放在调配公共资源方面,价值取向放在这方面,就难有时间去发挥“警察”的功能。 所以,我一直鼓吹一定要先把那边放弃,然后这边(警察功能)再增加。但现在看来,那边没有放弃,这边却增加了。不过,增加证监会的“警察”权力总体来说应该是好事,这一点是有深刻教训的。当年我们发现中科创股市操纵案时,中科创操纵的4家公司账上还有价值7亿多元人民币的股票,我们马上要求冻结。我是做律师的,我知道在中国通常情况下私人之间的案子,冻结用不了半天,只要你交上保证金,保证你不是在捣乱,很快就办理下来。但这个案子就是做不下去。拿到一家法院,说不行,需要什么什么文件,今天弄、明天弄,拖了整整两个礼拜。结果,最后账上只剩下了价值1000多万的股票,7亿全跑了。事后,证监会碍于面子罚这个、罚那个,但已于事无补,因为当事人已成了“滚刀肉”,无财产可罚了。当然,机制的腐败什么环境都会有,但这个法律机制的缺失让腐败很容易形成。我想起这些事情就非常愤怒。 的确,现在证监会的权力够大了,但这一块权力必须增加,让它有“警察”应该有的权力。但是,监管机构也必须小心,别干别的事情,别分担利益分配,你分担这个,肯定会卷入利益里边。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此次修订还有哪些应该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 高西庆:首先,关于证券交易所的问题,特别是证交所的性质问题。证交所看起来是商业组织,实际上是社会公器,因为它是完全垄断,市场大、利益复杂。其性质是会员制还是公司制?是事业单位还是国家机关?是公益事业还是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是自律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 如果这些问题弄不清楚,产权就不能明晰。 证交所的资产按说是国家的,但这么多资产由谁支配?交易所前几年自己办的公司很多,而且会费说收多少就收多少,这些问题必须解决。纽约证券交易所很典型,它是会员制,它的收入和支出必须保持平衡。收进来的钱,由于不能分红,只能用于交易所的运转和投资者教育,如果用足了这些还有富余,就必须降年费。 证交所治理结构在修订草案里说了一些,但要说清楚或者明确指出证交所是由什么机制决定的。有些修改的地方说了很多很细致的条款,但说了几条后就不说了,最后还是不清楚,这是立法技术的问题。 其次是披露事项。草案规定,司法机关对于上市公司的强制措施,比如说拘捕高管等等必须披露,但有些不是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比如“双规”,却没有明确说明。“双规”不是司法措施,但影响比司法手段更厉害。这些问题得有一个说法。 另外,收购方面,场内收购、要约收购等等都没有写进去,概念上也不是很明确。这个问题不是太大,可以把权力下放给证监会,让其下一步去具体确定。在法律责任方面,挪用客户保证金的赔偿责任其实可以说,但却没有提到。这些缺失,也可以通过“由证监会具体做出规定”等类似指引补充完整。 《证券法》要有大思路 《商务周刊》:那么,解决《证券法》修订中的缺失,或者更广地说,解决证券市场的缺失,应该建立怎样一种共识和基础? 高西庆:解决这样的复杂问题,必须有大思路。首先是我们《证券法》的机制。世界上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实质性审查机制,一种是信息披露制。我们说我们不是实质性审查,是核准,但这不过是把猫叫成咪。因为人人都知道,不经过证监会这么复杂、这么细微、这么艰苦的这一套机制,这么多人审来审去,根本无法进入这个市场。这中间不知道要打通多少关节,花多少银子、交多少“租”,这不是审查是什么?! 而信息披露制,很简单,就是注册制。就是说行不行由自己负责,敢说假话的,事后惩罚。两者差别极大,要想好。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人力财力有限,信息披露制更省事,也更有利于监管部门集中精力抓坏人。但如果真的要强调中国特色,实行审查制,也未尝不可,只是要说清楚。不可以什么都要,无所不为。 再就是证监会的功能定位问题。目前大家对于证券市场的期待太高了,对于证监会的要求也太高了。这种状况,谁在中国证监会都不一定能搞好。为什么?要求太多,权力不够,而有些权力不应该给却给了。证监会作为一个政府部门,权力是什么,义务又是什么?是作为一个裁判者、规则的制定者,还是要同时做一个公共资源的分配者? 在我看来,至少证监会这样的部门,就应该做一个裁判者,作为一个规则的制定者,一个警察,一个专门抓坏人的机构,不应该赋予它任何公共资源的分配权。 有人说,发行上市,审查这个审查那个,这是警察的功能。这个说法不对。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这种审查已经变成分配公共资源的功能了,因为一个公司如果能够上市,就如同“乌鸡变凤凰”。这种强大的利益驱动把一个政府部门的价值取向完全扭曲了,不管它自己愿意与否,都会被全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权力部门推着走。而大部分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总是很难靠一个没有显性激励机制的政府部门一家做好的。这一点已如此地显而易见,以至很少有人再来质疑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决定的正确性了。 所以,从这个方面应该引申出几条,比如发行审核、产品准入、市场准入等等,所有这些跟公共资源分配有关的权力都应该统统下放给自律性组织即“社会”,证监会只负责规则的制定和监督执行。这跟工商局、公安局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年的进步一样,企业注册、办理护照,规定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现在办个护照多简单啊,当年办一个护照是天大的事情,得祖宗八辈都审完了还常常拿不到。现在公安局态度多好,没有这么多龌龊事,这就说明做对了,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抓坏人上面了。回过头来说,如果给证监会资源分配这方面的好处大,它的压力也大,它当然把精力放在这方面了,就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激励去抓坏人了。 《商务周刊》:但多年来证监会“警察”权力的加强一直难如人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难办的问题吗? 高西庆:不是不能也,而是不为也。一些部门总是把老百姓当作子民,认为子民的智慧不如政府。毛主席说,“老百姓最聪明,我们是愚蠢的。”他说的“我们”不就是指政府嘛。 加强证监会的警察功能并非多么复杂,现在缺的警察功能就是证监会的法规制定权和司法解释权。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10条。这一条的B款看起来很简单,就是说什么是证券欺诈,并说可由证监会作进一步解释。一般人也不太明白。但在如今美国证券违规事件中,用得最多的是由此条款引申出的10B5。10B5条款不在《证券交易法》里,而是美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条例里解释出来的一个条款,即由证监会来解释认定证券市场的操纵、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美国每年因此很多人被判入狱,其中有90%的司法解释都来自这个条款。 《证券法》大法里语焉不详、模糊粗糙的条款,都可以由证监会来解释。理由是它处于监管一线,专职干这个工作,自然可以比国会的立法人员或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更有效地做好这个工作。美国证监会一诞生就拥有的这个权力,使其越干越精,市场中稍微有违规、变小花样,美国证监会都能整出来。不像我们,监管机构的稽查人员苦得要命,费了半天劲,查一年两年,很多事情却因为法院对法律条款的解释与证监部门的理解不同而不了了之。 现在看来,无论是《证券法》的完善,还是未来中国证券市场法律体系的健全,我们仍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焦点透视 > 《证券法》修改正式启动 > 正文 |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怎样迅速挖掘网络财富 |
| 短线最大黑马股票预报 |
| 海顺咨询 安全获利 |
| 风情小布艺店生意火爆 |
| 首家名牌时装折扣店 |
| 如何加盟创业赚大钱? |
| 品牌服装 一折供货 |
| 火爆粥铺 四季稳赚 |
| 开冰淇淋店赚得疯狂 |
| 美味--抵挡不住的诱惑 |
| 新行业 新技术 狂赚! |
| 投资3万年利高的惊人 |
| 05年开什么店好赚钱? |
| 05年投资赚钱好项目!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