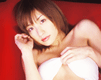|
文/傅勇
曾几何时,中国的富豪们给人留下了挥霍无度的暴发户形象。前不久,美国《时代》杂志“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富豪的典型生活方式。男人们身着“国产或者意大利品牌的西服(袖子上还留着商标)”,“在每年会费1万美元的俱乐部中打高尔夫球,去拉斯维加斯豪赌。”“每餐要在600美元以上,菜单中包括鲨鱼翅、鲍鱼等各种高档海鲜,”;而女人们则是
怀抱长毛宠物,穿的是“路易·威登或者香奈尔的时装”,手提“芬迪的手袋”,涂上鲜红的指甲油,“只乘坐奔驰轿车或者黑色劳斯莱斯轿车,同时配有吉利号码的车牌……”
幸好,近日发布的2005年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鲜活的反例,使得上述描述显得以偏概全,让人难以认同。在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位列榜首的云南世纪金源集团公司董事长黄如论无疑是近年来的“慈善先生”:过去两年内他共捐出了2.86亿元,相当于他全部财富的二成。
我们得承认,正确地看待自己财富并将他们处置得当并非易事,为物所累的人并不在少数。对此,美国钢铁大王、私人大规模慈善活动的倡导者卡耐基深有体会。在专门探索如何正当处理财富的书(《财富的福音》)中,他这样写道:“应该好好记住,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社会。”最后,卡耐基捐出了他一生所有的财产,共计3.5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亿美元。由此倡导了美国大规模的慈善事业。
对于我们这个正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市场经济是我们已经找到的最能激发人们创富欲望的制度,然而,一个和谐社会绝不仅仅意味着商品的堆积。市场经济的逻辑本质上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财富的集中不仅是获取规模效益的需要,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这一机制正是保证经济效率的前提。因此,贫富不均是不可避免的,起点上的不公平又会导致更严重的分化。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最为憎恶之处也正在于此: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财富在资本家一端累积,而贫穷在工人阶级一端累积”。
《圣经》中“马太福音”第25章有这么几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们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73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莫顿用这句话来概括社会分化的现象,并命名为“马太效应”。市场竞争的这种“马太效应”无疑是和谐社会的最大威胁之一。
对此,政府的有形之手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福利国家在财富再分配上做的不可谓不多。然而,在维护公平的同时也损害了效率。瑞典作为福利国家的“橱窗”,还获得了一项额外殊荣——以自己国家命名的“瑞典病”:经济增长缓慢,工作积极性下降,政府机构庞大等等。原因很简单,高额税收强行拿走了过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家甚至工人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把蛋糕做得更大。
实际上,对于一个和谐社会来说,最好的稳定器来自人们发自内心的慈善活动。自愿的慈善活动给了慈善家们充分的自由度来决定何时贡献自己的财富。在个人事业处于发展时期,财富的积累对企业家自己也非常重要,应该允许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人会倾向于看淡财富,而更加关心社会的疾苦。因此,慈善这种财富的转移方式无疑要灵巧和柔和的多。
具体来说,慈善活动首先帮助社会实现了一种分工:在某个时刻,有些人在努力做大蛋糕,而慈善家则关心如何公平地分配它。这样,前者并不一定要随时准备把自己的财富贡献给社会,相反,可以把财富投入到再生产中;而慈善家是在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在社会范围内再分配。也就是说,这种分工可以保证生产性更强的资源从事生产。正如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所发现的,分工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最重要的源泉,财富上的分工也是如此。这样,慈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府征税“一刀切”式的拙笨,能较好地协调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增强社会自我调节的韧性。
其次,慈善的作用在于在总财富一定的情况下,能够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福利经济学指出,同一般商品一样,人们从一单位财富中所获得的满足感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同样适用于财富。具体地看,同样是100元,对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下岗职工来说,意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慈善家把一部分财富转移给穷人,对整个社会来说,所增加的效用要大于减少的效用,从而会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而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卡尔多式的社会改进。
当然,慈善活动绝不是富翁们的专利。其实,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5%的捐款来自美国民众,这些捐款占了老百姓平均收入的2%。所以,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涓涓细流汇成了金钱巨浪。而要在一般民众中树立起合理的财富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慈善这一社会稳定器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为其提供良好的环境。人们愿意慷慨解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能够信任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把他们的钱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事业上。另外,为了鼓励社会参与慈善公益事业还可以制定一些税务优惠政策。比如你捐款100美元,就可以得到30美元的税务优惠,实际上你只捐了7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