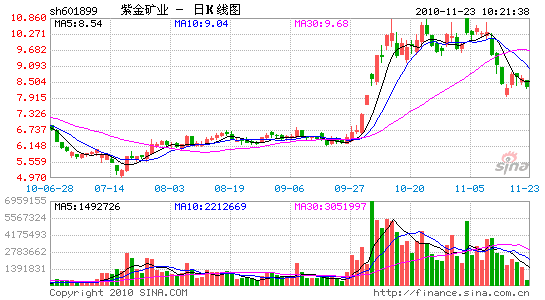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的色彩演变
红顶商人、国企老总、诗人……陈景河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其本人游刃有余地操控着颠簸的紫金矿业,但重回轨道已是无比艰难。
本刊记者 周夫荣
夏日傍晚的一场细雨驱走了白天的闷热,福建上杭县的青山经雨水冲刷后越显清丽。汀江边,渔民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畅想又一年的大丰收。7月是渔民的收获季节,每年此时,他们便“开始铆着劲数钞票”。沿河的饭馆和往常一样,在店前大张旗鼓地打出“汀江活鱼”的招牌,招揽来此贩鱼的生意人和游客。
雨后的汀江水面平静,鱼群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出来透气。有的渔民发现自家的鱼箱上层漂着几条死鱼。偶尔死几条鱼是正常的,为了防止传染别的鱼,他们赶紧把死鱼捞出来扔掉。可是几天后,鱼箱里的鱼全死了,有此遭遇的渔民不止一户。
很快,整条汀江水面完全被死鱼覆盖。臭鱼的气息蔓延到沿河饭馆,饭馆老板慌忙把招牌从“汀江活鱼”换成“店内的鱼运自梅江”。
“杭川大地,汀水缠绵;五龙欲飞,麒麟梦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曾经作词《永遇乐·金山》这样描写这方水土。然而自今年7月3日紫金矿业旗下的福建上杭紫金矿业铜湿法厂向汀江排放了9100立方米废水后,渔民赖以生存的汀江不再碧波荡漾,江岸边隆起大大小小的土包,这里埋着承载渔民致富梦想的鱼尸。因水质污染严重,渔民们3年内不能养鱼,只能卖掉渔船,另谋生路。
红色成长
陈景河1957年出生于福建著名的革命老区永定县,唱着《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度过“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的童年时代,新生国家特有的朝气渗透进他幼年懵懂的心灵。
少年时代的陈景河以“从小努力学习,长大报效祖国”为志向,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路斗志昂扬。他赶上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经历过手拿红宝书、臂戴红袖章,只要背对毛主席语录,坐车就不用买票的红色岁月,感受过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革命热情。
同样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但陈景河不像红军的儿子、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一样“拧”,不像商人的儿子、开元旅业集团董事长陈妙林一样快人快语,也不像新闻记者的儿子、贝恩资本董事长黄晶生一样健谈,受老实巴交的父亲影响,他自小就不爱说话、性格沉稳。
陈景河的父亲是一名教师,因此,陈景河从小很爱学习,对自己要求也特别严格,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当年老师就觉得他是个“不简单的孩子”。陈景河的家庭条件一般,买不起书,他就到邻居家借旧书看。文革时期,即便教室里经常会飞进砖头,许多同龄人毅然丢下书本去改天换地,陈景河还是抓住一切机会坚持读书。文革中断了陈景河的高中生活,但由于出身贫农家庭,根正苗红的他凭借扎实的学习基础,在18岁那年当上了村里生产大队的会计。
青年时代的陈景河有着那个时代人特有的英雄情结,他梦想着到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有一番作为。激荡的历史,狂热的年月里,他学会在碰撞中成长,在纷乱中判断和抉择。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和村里的同伴考前两个月才知道这个消息,可那时城里的孩子已复习半年了。”随后的两个月,陈景河天天挑灯苦读,最终考入福州大学地质专业,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陈景河之所以选择地质专业,是因为“勘探队员寻找地下宝藏的锤声,吸引了我充满理想的心灵。广阔天地,改天换地赤诚的红心;体能和意志的磨砺,让我初尝收获的喜悦、生活的艰辛。”(陈景河《我和紫金,此生不了情》)
文革带来的是精神饥饿。进入大学的陈景河面对知识爆炸和改革开放开始恶补,陈景河的大学老师回忆说,他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每天他都是最早一个来到实验室,最晚一个离开。
毕业时陈景河怀着一腔红色激情到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报到,并作为福建省上杭县的紫金山金矿普查项目负责人前往紫金山。日后陈景河在散文中写道:“千百万年地质历史留下的痕迹,使我痴迷,使我一见钟情。骑着五龙驾雾,伴着麒麟入眠,多少汗水、多少艰辛。”
他的人生信条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日后的创业、扩张过程中,他逐步用行动诠释了这一点。
金色创业
毕业两年后,陈景河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依据紫金山的地质构造提出紫金山“上金下铜”的观点,并在以后的工程实践中证实了这个论断。29岁时,陈景河辞掉了福建闽西地质大队长的工作,到贫困的上杭县走马上任“职工只有76人,总资产仅351万元,靠买卖零星矿产品度日”的上杭县矿产公司经理,这家公司便是日后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企业紫金矿业。
有知情者称,外表憨厚的陈景河其实很有城府,之所以选择上杭县矿产公司,是因为他私下判断紫金山富含铜矿,在这工作比他在城里当地质大队队长更容易崭露头角、建功立业。至于他后来在紫金山勘测出大量黄金,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敢赌的陈景河充分表现出客家人的特点。客家人“情愿在外讨饭吃,不愿在家掌灶炉”,一千多年来从中原向外迁徙,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饱受奔波之苦,没有归属感,却也由此激发出一种进取精神。陈景河生性喜欢冒险,不管前途坎坷还是平坦。
当时陈景河的妻子赖金莲在福建龙岩医院上班,陈景河很长时间才能去看妻子一次。每次跟妻子说好去逛街、旅游,陈景河都会因“临时有事”或需“去矿上看看”而爽约,陈景河说:“看到矿山,我就眼睛发亮,对于逛商店、看风景,我没有兴趣。”他因此得了个“空头支票”的外号。
那是一段异常艰苦的日子,陈景河和同事们住在山上的破庙里。“夜间,十几个人就挤在破庙的泥地板上睡觉,炎炎夏日,一天也只有一桶水。”那是陈景河生命中的金色年华,破庙的泥地板并不影响他做找金子的梦。
紫金山一度是荒芜的悬崖峭壁,谁也没指望它下面能有什么宝贝。陈景河就要“干别人不敢干或干不成的事”。36岁那年,陈景河用自己开发的软件,计算出紫金山的黄金储量达254吨,通过这次“点石成金”,紫金山金铜矿成为我国“七五”期间探明的重要金属矿床之一。陈景河在这一年接过这家县级公司的方向盘,带领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企业开始寻金之旅。
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紫金矿业成立初期,第一期工程建设预计需投资2900多万元,这对濒临倒闭的公司来说是个天文数字。陈景河突破常规,提出“第一期工程建设采用堆浸提金化工艺建设年处理万吨矿石的生产规模”的思路,仅用700多万元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建设,成为中国南方堆浸提金第一人。
其后十几年,陈景河身上的红色革命英雄主义种子扎根紫金山,结出黄澄澄的金子。他说:“在这里,我们要把沉睡千万年的宝藏唤醒,要开创宏伟的辉煌和功勋!”他立志创立“百年紫金”。
陈景河起初投入紫金矿业仅700多万元,而紫金矿业市值最高时曾达1500亿元。陈景河能从一个地质勘探员,一直做到中国最大黄金矿业集团的董事长,离不开他在地质勘探方面的深厚学术造诣、实践经验和早年练就的独到眼光。
在企业运营上,经历过文革的陈景河有着超乎常人的政治敏感性,以致紫金矿业中充斥着众多“红顶商人”。上杭县环保局知情人士称,当地官员与紫金矿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杭县政界大部分退休官员都是紫金矿业的抢夺对象,他们被委以闲职,年薪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记者从紫金矿业的网站了解到,紫金矿业的公司管理团队有浓厚的官员背景,多位管理人员曾供职政府部门,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中有一部分人具政府部门工作背景。据当地某位政府官员称,有时候省里有官员到了上杭都是直接与陈景河会面,县里的领导只能得到陈景河的邀请才有机会陪同。
紫色扩张
在色彩文化中,红色是最热烈的颜色,象征热情、暴力、侵略,蓝色是最寒冷的颜色,象征内敛、沉稳、广阔,紫色正是由这两种矛盾的基本色调和而成。陈景河融热情激越、内敛沉稳两种极端性格于一身,当外界条件具备时,人到中年的陈景河便把二者调和起来,野心勃勃地展开了紫金矿业的紫色扩张。他的办公桌对面是中国地质图,后面是亚欧地质图,彰显着他由内而外、逐步拿下全球的雄心。
陈景河一惯以黑西装白衬衣面对镜头,接受采访时他喜欢把两只胳膊搭在椅子扶手上,即使说话胳膊也很少拿下来,与身体形成稳定的三角结构。陈景河长着特有的厚嘴唇,说话比较慢,表情少有变化,给人印象平和稳重,甚至有些憨厚。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憨厚的人,说自己不满现状、不甘寂寞,计划从2007年到2020年再造十个紫金,2020年把紫金矿业建成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紫金矿业在他“走出去”的战略引领下,开始衔枚急行,踏上迅速扩张之路。
因为亲身经历过物资贫乏的三年自然灾害,陈景河笃信拥有资源才能拥有未来。他在常委会上这样表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想舒服,我只做紫金山最舒服,一年有几千万元的利润,每年花两三百万元,每天花天酒地,过得也会很不错。而我出去投资既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可能。如果失败了,就要背负很大的责任。可是如果把企业困在紫金山,那我们就只能坐吃山空,紫金山开采完,这个企业也就消亡了。现在有条件、有机会,我们就应该走出去。紫金矿业要更长远、更长久地发展。于是在矿山市场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他开始四处收购。
紫金矿业承载着陈景河的红色使命和金色梦想。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小企业,能够做出这种决定,是起源于陈景河基因里的不安全感及由此生发的占有欲,以及他成就一番事业的情结和把握时机、顺势壮大的斗志。
扩张过程中,紫金矿业盘活了不少企业。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珲春金铜矿因资源品位低下、技术老化、资金匮乏、体制僵化等原因濒临破产。2003年,陈景河与珲春联合成立了珲春紫金矿业有限公司。通过运用自行研制的铜金精矿热压浸出——氰化工艺和常压化学催化预氧化工艺,以及重大技术改造的成功、新工艺流程的确定、资源的重新认识和评价,珲春紫金矿业不到一年就扭亏为盈,不但招回原矿的所有下岗工人,而且吸引了一大批人才。如今,印有“ZJ”标志的紫金旗帜已遍布新疆、吉林、贵州、四川、安徽、西藏等省和自治区,拥有数十家下属企业。
2006年以前,陈景河提及最多的是“资本”二字,之后,他常把“国际化”三字挂在嘴上,扩张路上他开始思考如何推动紫金矿业走出国门,在国际黄金领域傲视同侪。“尽管我们拥有中国唯一一座世界级金矿,但我们与国际行业巨头还有很大的差距,走出去是公司发展的必然要求”。他带领紫金矿业将矿山开到了菲律宾、印尼、蒙古等国家。
收购过程中,陈景河也有拔不下的寨。甘肃阳山金矿被称为亚洲第一金矿,曾被中金黄金、山东黄金、紫金矿业等三家上市公司公开争夺,业界称“得阳山者得天下”,阳山金矿最后落入了中金黄金的手里。对此,陈景河说:“反正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谁拿到都是一样。”不过他马上补充说,紫金在矿山生产的黄金肯定是行业第一的,这还不算冶炼的黄金。他还在另一个场合呼吁记者,“你要给我们中国第一大金矿正名”。陈景河近乎偏执地迷恋紫金矿业“第一”的身份,这是他快速扩张的动力之一。
陈景河还补充,阳山金矿是近些年来新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矿床,这种评价是对的,说它是亚洲第一大矿,那肯定是不准确的。阳山金矿150吨的储量只是一个预测,而按照评估,实际储量比这个可能要低。陈景河说:“只不过是一个矿山而已,比紫金矿业差多了!紫金矿业的储量是300多吨,这是已经确认的。”在陈景河心里,阳山金矿究竟是酸葡萄还是鸡肋,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灰色收尾
紫金矿业总部所在地——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大酒店,这栋十余层高、集办公和酒店于一体的总部大楼伫立在出入县城的咽喉要道上。酒店内工作人员及入住的客人进进出出,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一家正处于环保风暴中的企业。总部一楼大厅里,高悬着一幅诗词:“开山劈地,艰辛探索,奉金抱铜献。古往今来,多少心愿,紫金重任在肩。”诗的署名是陈景河。
紫金山金铜矿湿法厂办公楼前,“中国第一大金矿”的招牌仍然熠熠发光,但工厂里已无昔日的机器轰鸣声。厂里的污水池已被抽干,不远处的小山包上,树立着陈景河的环保口号“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红色的宣传标牌分外惹眼。陈景河曾把2007年作为紫金山金铜矿植被恢复年,计划把矿山建设成为园林式矿山,他还计划在以后恢复好的植被上建立世界第一的矿山高尔夫球场。“我们把环保当做一个品牌在经营,而不是满足达标排放。关键的时候,这个品牌可以为公司加分。”陈景河曾在多种场合信誓旦旦地宣传自己的环保理念,他还创造过一个新名词——紫金概念的环保:零污染、零排放,环境再造更美丽。
陈景河还曾请外来的和尚帮紫金念环保经。国际著名的SRK国际矿业咨询顾问公司矿业环境专家沃尔夫在考察紫金矿业后说:“公司在环保上取得的成绩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将来可以参加大型的国际性会议,向国外同行推广优秀的环境治理。”
而如今,陈景河留给老区的是一江污水。
其实,福建汀江早在今年6月5日就漂浮起成片的死鱼,事态如此严重,以致上杭县教育局不得不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参加高考的学生一律不要吃鱼。
有当地百姓说:“在很多外地人眼里,紫金矿业是金色的,但是在我们上杭人眼里,它是灰色的。”“自来水不能做饭、不能喝,这都是紫金矿业污染造成的。污染太严重了,没人敢喝这种水,只能洗澡和冲马桶。”
今年紫金矿业还获得“2009年度中国最诚信企业”称号,陈景河也一直推崇诚信,但今年5月,环保部曾经发文通报批评11家存在严重环保问题的上市企业,紫金矿业位列其中,被环保部称为言而无信。
当一江污水滚滚流出福建流向广东之后,紫金矿业仍在道歉信中坚持,事故起源于“福建境内持续强降雨”导致的污水处理池泄漏,且称渗漏事件对上杭县及下游生活用水并未产生影响,“出于避免社会动荡以及干扰抢险工作的考虑,公司没有及时披露这一信息”。
事故过去半个多月,陈景河才出现在公司所在地的上杭县电视节目中,就公司对事故发生及信息披露处置不当,造成矿山下游库区网箱鱼养殖户重大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向当地各界人士道歉。在瞒报的9天里,陈景河在哪里?他是否知道这件事?直至记者发稿日,紫金矿业也没人回答这个本来不难求证的问题。
陈景河最关心的还是公司的利益。“最大的损失是公司的声誉。”陈景河称,过去紫金矿业在环保上的优势是迅速扩张的重要支撑,“现在一夜之间,这个金字招牌被砸个稀巴烂。而且3到5年时间里无法恢复”。
陈景河从红色的少年时代开始上路,金色的青年创业时期步入起跑线,紫色的中年扩张时期展翅飞翔,从污染开始的那天起,灰色便永远烙在陈景河身上,足以使他折翅坠落。17年间,他带领一家濒临破产的县级矿产公司一路披荆斩棘,逐步把紫金的旗帜插到中国各地乃至世界上的多个国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也变身为“中国第一矿”,而他被人提起,更多的却是因为污染。他履行社会责任的左腿远远跟不上追求经济利益的右腿,因而摔得头破血流,他只顾忙着赶路而无法超越自己,绚烂之后却以灰色收场。
四年前,陈景河曾说:“《神话》的歌声响遍大地。我未来的神话是什么?”言语间洋溢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情。四年后,他留给福建上杭县满目死寂。当陈景河拿走一山黄金,留下一河死鱼,当他从第一金王变身污染大王,当上杭县政府以6块钱一斤的价格回收死鱼时,陈景河的社会责任感和紫金矿业的声誉是否也值6块钱一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