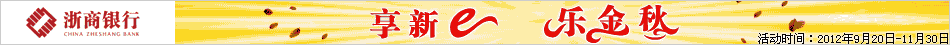三十年间两件事
朱正琳
入学
1980年,我赶了一个末班车,在“恢复高考”的第四个年头,以“同等学力”直接报考了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的硕士研究生。在我的录取问题上,曾出现过一点波折,当时还成了一个见了报的新闻。我先收到的是“不拟录取”的一纸通知,理由虽未说明,但我知道是由于政审出了问题:“文革”期间我曾因反革命案坐过几年牢。我斗胆上京去讨个说法,没想到竟赢得多方支持,而校领导也居然就同意“重新考虑”,并终于推翻了不录取的决定。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我真切地感觉到,史称“八十年代”的那个时代正破土而出。
我不是不想考本科,而是报考无门。当时我属于无业人员,没有“单位”,而按规定须由各单位统一为本单位考生报名。后来我打听到,考研究生倒可以由考生自己持单位证明到招生办报名,而且无单位者持街道办事处的证明亦可。于是才有了那场改写人生的考试。我报考的专业是现代外国哲学,专业方向是黑格尔哲学与新黑格尔主义,导师是张世英。选择这样一个专业方向,只是因为目录中所开参考书有一本《小逻辑》。我曾用力啃过这本书,并且自信像我这样啃过的人不会太多。
当年我是有些偏爱哲学,这大概和我有些好玄思的个人气质有关。但是,我之所以啃《小逻辑》,却主要是因为列宁的一句话。那句话的大概意思是:不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没法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是其第一章。与我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当时是下决心要读懂《资本论》的。原因在今天听来也许有点不靠谱,我们都想要从理论上弄清楚“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我们当年抱定的成见,如果不读《资本论》,则根本不可能取得那个“理论高度”(当年常用语)。“中国向何处去”是杨小凯先生当年所写的一篇著名文章的标题,我常借它来概括我们当年的一种关怀。那显然是一种政治关怀。我有时会自嘲,称那种政治关怀为“大关怀”。在自己的权利被剥夺殆尽之际,却相信自己的使命乃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此种关怀是显得大了点。
不过我以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虽大却不空,是一个我们从切身感受出发提出的真问题,与响应“关心国家大事”的“伟大号召”已无太大关系。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像是卷入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明显地失去了正当性。最切身的感受莫过于人的尊严备受践踏,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人权备受践踏,只不过那时候人权二字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词典。因此,当我们追问“中国向何处去”时,无疑是在表明对现实政治的怀疑与批判态度。同时也是在从根本上追问: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这当然关涉到我们现今常说到的“价值”二字。问题之所以会这样被提出来,说明我们原先被灌输的价值已在我们心目中被颠覆。北岛曾喊出一句引起强烈共鸣的“我不相信”,表达了在一代人心目中发生的这种颠覆。颠覆之后的价值重估,则变成了一场“理论突围”(我姑妄称之)。我们从小就都生活在某种理论的笼罩之下,是非善恶不能由自己直接做出判断,而须根据既定理论进行推论。可以认为,理论已经接管了我们的良知。为了让我们的良知挣脱理论,重新独立地做出善恶判断,我们委实费了不少心力与理论纠缠。按我自己在纠缠中的体会,笼罩着我们的理论之中心概念是“历史”,接管良知就是以历史的名义进行的。我们的“理论突围”或许也可简单概括为,力图摆脱“历史的偶像崇拜”(借用雷蒙·阿隆的说法)。
“理论突围”当然主要靠读书。我的视野有限,所看到的突围路径大致有三。一是读马列经典,并上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所谓“正本清源”。读黑格尔可算在其中。二是从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发掘其人道主义出发点,最常被说起的书是《经济学-哲学手稿》。三是借助“文化形态”说或“世界历史的文化形态学观”(斯宾格勒语),突破历史阶段论的模式(其简化版是苏联式《社会发展简史》),从中西文明的冲突与比较去重新认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节写本)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影响较大。再有就是一套“资料汇编”——《外国资产阶级论中国近代史》。这三种书当时都是“内部读物”,但流传也甚广。或许还该说到的一点是,在1970年代后期,存在主义的概念开始引起注意。依我看它最能打动我们的地方,是高调倡言人的自由。还有它“摈弃了对历史的总体性的信仰”(再次借用雷蒙·阿隆),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历史必然性”的消解。
入学之后,发觉来自天南地北的同气相求者还不在少数。一代人经历太相似,诉求也就很容易一致。同样的“大关怀”,同样的理论困扰与同样的“理论突围”,我当时的感叹是:连叹口气都是相通的!有比我视野宽的,更早地接触了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理论等等,在“理论突围”上兴许比我走得更远。这些学说在1980年代的中国一度成为“显学”,并带动了一种西学译介的热潮。当然,那其实大多只是一种“恶补”。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的“恶补”多少具有一种囫囵吞枣的性质,关注的焦点还是多在一个人字。至少在1980年代初,人字一度成为关键词。我后来回顾时也曾写道:“人字在1980年代被几代文化人高举起来,成为全社会最引人注目、最敏感、最能激发理性思考又最能寄托浪漫情怀的字眼。”“人的理论”、“人学”,一时间差不多成了时尚话题。人的价值(至少在文字上)被高扬,显然是对其曾经(在现实生活中)被严重贬抑的一种反动,应该不难理解。
还有一种“突围”的路径却是我入学之前不曾注意到的,用一个学科术语来说就是“分析哲学”。这是一种从认识论入手,在思想方法上寻求突破口的路径,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来使理论对我们的笼罩瓦解崩塌,其实很值得重视。我注意到,循此路径突围的人在关怀上与我们也并无二致,但他们的思想往往却更为透彻和清晰。1981年在北大的人民代表竞选活动中,那种透彻和清晰就有所表现。自由的概念一度被清晰提出,值得一说的是,那是阔别已久的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而非(我们很多人囫囵抱持着的)浪漫主义的自由概念。我在这里借用了伯林所做的一种区分(或可参看伯林《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
这里当然不是讨论自由概念的地方。但我还是想借着这种区分来说一点我的个人感想。我们在“文革”时期最痛切的感受,是一个个具体存在着的人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而不是被浪漫主义地高扬了的人的概念(例如“人,诗意的栖居”)没有成为现实。因此,当我们主张人的价值时,应该是在主张现实生活中(按理论标准)有着这样那样毛病的普通人就有价值,而不是主张人就其被假定应有的完美本质或“本真存在”而言才有价值。或者说直白一点,我们的主张是:人有权有一己之私,人有权有低级趣味,人有权过不那么高尚的寻常日子……如此等等,都应受到尊重。干嘛要逼着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干吗要逼着“六亿神州尽舜尧”?听上去这好像是愤激之词,其实却是“文革”经历中广泛形成的一种共识。想想1980年代早期春晚的相声《如此照相》是用什么赢得观众会心大笑的?李文华:你说一句好话……。姜昆(附耳):我给您送工资来了!这曾让我想起“文革”时期的另一个笑话。买卖双方言语间起了争执。卖鱼人:你说一句好话我就把这条鱼送给你。买鱼人:这是你说的?毛主席万岁!没有人敢阻拦他把鱼拿走。
我是有些感慨。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了的事理,为什么后来在知识界却又变得云遮雾罩歧义多多?一些当年的“知识青年”在完成了“华丽大转身”变成“知识分子”之后,似乎真又“好了伤疤忘了疼”?浪漫化的人的概念逐渐变成一种审美意象,“最壮观和最受到深刻赞赏的景观是一个孤独的未得到支持的人。”(借伯林语)这个景观或许得自存在主义(想想西西弗斯的形象),但好像也很能满足中国文人的孤高自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一次被视为一种沉沦。于是,对强有力人格本身的崇拜终于又死灰复燃,自由的概念又被诠释成如下模样:“作为自由人的唯一证明是激情地奉献给国家或种族或历史或为了权力而‘力本论’地去追求权力。”(伯林语)我在这里说的是我观察到的一种心智现象,当然有些过于简化。
收起感慨,回头说说我的北大生涯。入学前我学哲学,是“带着问题学的”,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它会成为我的职业(搞哲学)。我甚至还有一个更为偏激的想法,认为哲学就不应该成为一种行业。但入学即入行,我意识到从今往后哲学大概就变成了我的饭碗,书就变成了“资料”。对此我一度心存抵触,因为这显然有违我的初衷。不过,三年间虽然有过一些纠结,但我毕竟还是接受了学术ABC的训练,学会了尊重学术。渐渐也觉得,我最初的想法可能有失偏颇,以学术为业未必就会放弃始于初衷的关怀。而必要的系统学习和研究,其实有助于充实思想,使那种关怀不至于枯竭,变成一种僵滞的情感。我后来反省我们早年那种关怀时,曾有过如下结论:“我对我们当年那种思想贫乏的关怀评价并不高。但我也意识到,需要做的是改变那种贫乏,而非放弃那份关怀。”至于哲学是否应该成为一种专业和职业,这个问题在我1984年读到波普尔的一段话后终获解决。波普尔说:“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哲学家。如果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有哲学问题,他们至少具有哲学上的偏见。这些偏见大部分都是一些未经考察就接受下来的理论,他们所吸取的这些理论来自周围的思想环境和传统。……需要有人对这些流传很广和有影响的理论做出批判性的考察,这就是专业哲学存在的理由。”可以说,以上所引的每一句话我都同意。由此我还得出一个自己的推论:专业“搞哲学”的应该多做减法,简单说就是多澄清少堆砌。
办刊
1990年秋,我在德国汉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期满。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之际,我的那位87岁的德国房东老太太问我:“你回去后会做些什么?”我回答说:“我想办一个杂志。”她又问:“能挣很多钱?”我又答:“不是为了钱。”老太太沉吟片刻,却说了一句让我沉吟至今的话:“哦,什么也不为。”这句话的德语是 Fuer Nichts, 完全可以译作“为了虚无”或“为了无”。
我之所以在德国起意要回国办刊,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的那种“大关怀”又在发酵。回国后却发现同道者不乏其人,说明当时同步“发酵”者也不在少数。时值东欧剧变,此前不久“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又一次被明确提出,“发酵”现象自不难理解。不过,我两手空空地回来了,要办刊并无任何“资源”(那时候对这个词我也并无任何概念)。但回国后运气似乎不错,没多久就发现了办刊的机会。其实是当时有很多有“资源”的人都在谋划办刊之事,所以才让我这个没头苍蝇也撞了个正着。后来回想起来,我曾引用一句名言(谁说的却记不准了)来形容当时的情景:“是时候了,许多不同的人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想起了同一件事。”
先是撞上了三联书店想要“恢复”当年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周刊》,时间大约是在1992年。不过,如我后来所言,我只是参与了“《三联生活周刊》史前史”中的一小段。三联当初从香港带来了香港资本和市场运作的模式,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尝试。记得当时有从事报业工作的朋友就曾议论说:“盯住老朱参与的那摊事。”但我不久就被辞退了。在那种运作模式中,我的遭遇就不过是“还没开工就被炒了鱿鱼”(我自己如是说)。虽然这与我的自我期许落差不小,我却觉“无怨无悔”(借用一个时下常用语)。与香港投资方的接触,让我获益匪浅,好比上了一大课。单是“卖点”这么一个词,对我造成的冲击就非同小可。先是语塞,后是思深,这才明白自己原不过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举着双手呼唤市场经济,进入市场却两眼一抹黑,还端着个非卖品的架子。那种身段当然十分可笑。好在我当时还有点反省能力,没有急急忙忙地就想缩回“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心理老巢。
在三联的挫败让我心有不甘,索性在当时我供职的湖北大学告了长假,举家到京守株待兔。大有此生不办一回刊死不还乡的架势。运气也可谓好得出奇,没过几个月就还真让我等着那只兔子了!那就是《东方》杂志。《东方》杂志是一份双月刊,于1993年10月出创刊号,兼有试刊的意思。1994年元月正式出第一期,到1996年11月出当年的最后一期后被叫停,历时共三年。我从筹办1994年第一期开始介入,到1996年4月因个人原因退出,在该杂志社供职约两年半时间。虽也有过不少不快经历,但终究是在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说白了,总算是过了一把办刊瘾。
《东方》杂志的办刊理念比较传统,大概就是一个“言论阵地”的意思,不像《三联生活周刊》决意以市场为主导的理念那样先进。但是,《东方》杂志也自有其领风气之先的地方,那就在于它基本上是民办的性质。主办方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不太可能对杂志提供很实际的支持。于是,“资金自筹”就基本靠的是“化缘”,“编辑部自组”后也就基本自主。当然,后来也发觉,钱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我们把《东方》定位为“文化评论杂志”,在提法上无疑是受到兴起于80年代的“文化热”的影响。不过,我们当时都倾向于把文化作最广义的理解,并且在办刊理念上更偏重于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分析与判断。这里说的“我们”,是指《东方》编辑部的同人。人员不多,不难达成共识。我说过,文化这个概念曾经是我当年做“理论突围”时窥见的一点亮光、一个可能的突破口。想当初我就曾背着一本《西方的没落》流落故乡(“倒流”回城),一心想着要解透中国“文化的宿命”(斯宾格勒的概念)。然而,在北大重读斯宾格勒,对他那种“文化”概念已觉很难苟同。1980年代“文化讨论”中出现的“文化”概念当然也让我满心狐疑。我对1980年代文化讨论比较具体的批评意见有两点:一是缺少对“文化形态”说或“世界历史的文化形态学观”(斯宾格勒语)的基础理论部分进行批判性考察;二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谈论现代中国。用我的话说就是,上下五千年都谈了,可就是不谈我们身在其中的这四十年。我不是不理解这种回避,但我担心回避成习会产生一种错觉,有人直接对现实生活下判断时,我们反而会觉得人家太不“深刻”。后来我在回顾80年代的一篇文字中也曾写道:“没有直接对现实进行的判断作为基础,理论争论就往往会变成从概念到概念的推论。‘文化讨论’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中国当代这几十年的历史,反而被有意无意地遗漏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这两个庞大概念的夹缝之间了。”可以说,我参与办《东方》时曾有一种自觉,想尽可能不要步“文化讨论”的后尘。
从《东方》退出后我还是心有不甘,想再找机会续上前缘,重办一个杂志。为了赖在北京,我开始给央视打工,参与了《读书时间》栏目的工作。我的说法是:且找个栖身之地。没想到这一栖,就是整整十年时间,直至2005年《读书时间》停办。十年间也曾有过一些貌似机会的人事接触,与各种投资者商量办刊事宜,却无一例外地都只有极为短暂的“史前史”。看来我已是好运不再。我也曾想,“不是为了钱”很可能真的已等同于“为了虚无”?但转念间又不禁莞尔:不要如此自恋,现如今网上“不是为了钱”的办刊人还少吗?
(作者系知名学者及书评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