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地产泡沫是谁吹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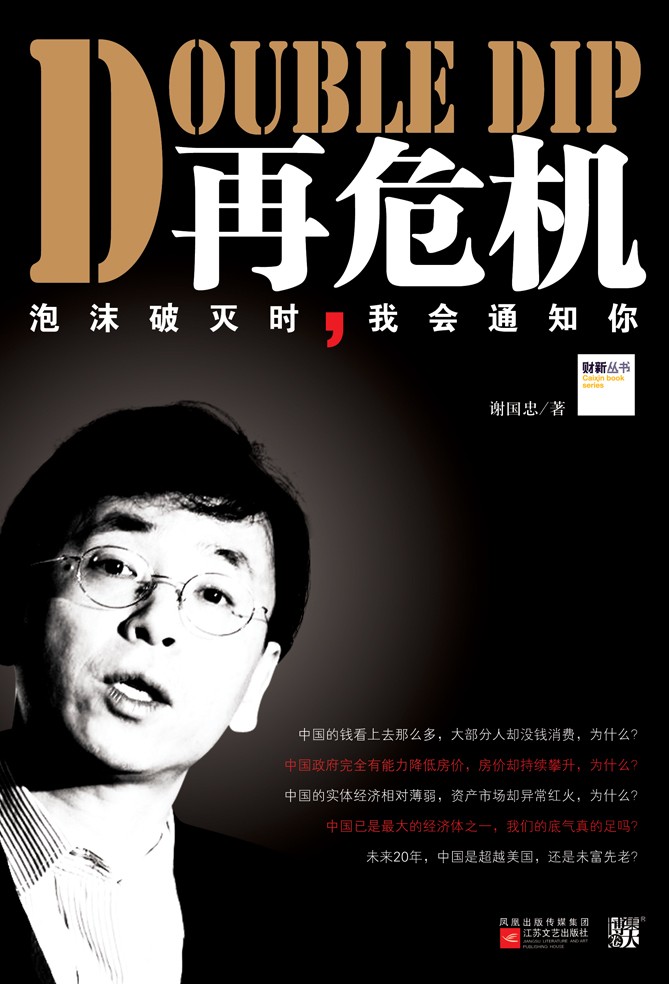 |
专访谢国忠:地产泡沫是谁吹大的
作者:程明霞
在埃及尼罗河的三角洲地带,有一座小镇叫作Rosetta。两百多年前,拿破仑的部下攻城略地到达这里,在打地基建造防御工程的时候,挖出了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密密麻麻无人能懂的碑文。大石头先是被运往开罗研究所,后来几经辗转,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穿越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一直留存到今天。
原来大石头已有千年之久,上面用三种语言记载着一位古老的埃及国王的功绩。曾有埃及、英国、法国的多位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努力读解石碑上的内容而不得。几十年过去,据说最后是一位德国学者破译了全部碑文,让死亡的文字重新复活,让遗失的意义再次浮现。
这块大石头,以它出土的村庄命名,被叫作Rosetta Stone,中文里通常将它音译为“罗塞塔石碑”。但谢国忠将它意译为一个更动听的名字——玫瑰石。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我觉得它代表着一种跨时代、跨文化、跨语言的对知识的追求,”谢国忠说,所以他以这块石碑为自己的公司命名——玫瑰石顾问公司。
就像很多人并不知道“玫瑰石”这个名字的来历与意义一样,很多人也并不了解,谢国忠那些耸人听闻的结论背后,有着多么强大的逻辑和证据。
据说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谢国忠就以三大预言的逐一应验而扬名立万: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回归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中国在20世纪末的通货紧缩。
20世纪的故事已经显得遥远。就我个人而言,真正意识到这个人的声音值得倾听、他的惊人之语并非都是妄言,是2007年到2008年之间:
2007年8月,华尔街两只对冲基金破产,引起美国金融市场一阵恐慌,当时本报为此做了一个小专题《华尔街的盛夏寒流》。在做这个专题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北京、纽约、伦敦的多位经济学家与分析师,询问他们对市场的判断。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太拿当时的状况当回事,尤其是北京与伦敦的经济学家,都表示对美国金融业、对华尔街非常有信心。
只有谢国忠一人,在当时发出了无比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全球信贷泡沫正在破裂……目前的全球流动性泡沫很可能在2008年终结,并以华尔街衍生品市场的崩溃为开始。”当时谢国忠让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骇人的预言,还有他激烈的表达方式,他写到:“是时候了,让华尔街的骗子们破产去吧!”
2008年9月,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全球经济随之跌入泥潭——当我想起谢国忠一年前的预言时,我觉得他简直是个巫师!他是怎么做到的?那时甚至还没有几个人能说明白,“次级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当我终于弄明白,美国房地产市场所谓的次级抵押贷款是怎么回事,我也意识到,谢国忠不是巫师,他就是一个眼光敏锐、大脑清晰,又无所顾忌、敢于直言的经济学家。他之所以敢于预言,他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言准确,背后自有一套严密而强大的事实和逻辑。只是人们往往被他的结论所吸引并激怒,而没有耐心去听他结论到来之前的路径。
在联络采访谢国忠先生的过程中,我像他的朋友们一样称呼他为Andy(他的英文名)。其实,私下里我叫他“Mr. Bubble”——泡沫先生。翻看他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文章结集《再危机——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叫他“泡沫先生”并不算偏颇。近十年来贯穿他言说的主题,就是对经济泡沫的剖析和警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泡沫总是要破的,没有例外。……最终的杀手就是通货膨胀。……泡沫的发展和破灭,有自己的时间表。当它即将破灭时,我会让你知道。……很有可能,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将在2012年破裂。”
著名地产商潘石屹说,他不喜欢谢先生那种“上帝般的说话方式”。
谁会喜欢呢?——当上帝说的是“离开伊甸园吧”,而不是“上去诺亚方舟吧”。激怒人们的,并不是谢国忠说话时那种“上帝般的口吻”,而是他总在叫嚣丧钟已经敲响,悲剧即将上演。在一片狂欢景象中,这样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预言,而像是诅咒。
但是,当你耐心倾听完他的话,你会发现,这位“泡沫先生”——Mr. Bubble谢国忠,其实比任何人都憎恨泡沫。既是出于“说出心中真相”的本能驱使,也是出于对泡沫破灭后巨大的经济与精神损失的担心,才让谢国忠如此执着地言说泡沫。
我以为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的谢国忠博士,一定有着身为经济学家的更伟大的志向,比如让中国人民更富裕、让中国社会更美好什么的。没想到他说,作为经济学家,他只希望中国人辛辛苦苦赚的钱,不要被平白无故地骗走。
在经济学之外,他的兴趣在历史,他的志向在写小说,因为这个多彩的时代是在很适合写小说,“我一定会写,但可能会先用英文写。”
谢国忠一向以英文写作,《再危机》这本书呈现出的简洁明快、清晰有力的语言风格,要感谢翻译们的杰出工作。接受《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专访时,谢国忠关于西方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比,也多少解释了他本人何以形成今天的思维方式和表达风格。
我想,如果将来有人写一部“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史”的书,没准儿“谢泡沫”的称呼会和“吴市场”一样被留下来。人们会记得,当年有位吴敬琏先生,是多么热爱“市场”;还有一位谢国忠先生,是多么痛恨“泡沫”。
“不能靠泡沫发展经济”
问=程明霞 侯思铭 答=谢国忠
谁吹大了泡沫
问:我们还是从房地产说起吧,你最近的文章说,“香港所有的不幸都可以归因于对房地产的痴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香港一样,经济重心如此依赖于房地产。”这和我们大陆目前的样子不是很像么?你书中写,上海的小保姆都辞职去炒房了。
谢:是的。但是大陆和香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大陆房地产业的钱都跑到政府口袋里去了,香港可不是这样的,钱主要是给开发商拿走了。
一个泡沫最终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就像股市从100点涨到200点再回到100点,这中间什么都没变,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但是从起点走到终点这个过程中,有人买入、有人卖出,所以有的人钱变多了,有的人钱变少了,财富总量没有变,但是重新分配过了。第二,它也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中间有人投资进去想要获利,结果造成了损失。
而大陆房地产泡沫的情形就是,这个过程中,财富和资源最后都流向政府了。所以你看政府这几年突然变得非常有钱,财政富余很多。那么问题就是,政府要怎么花这么多钱?效率能有多高?会不会浪费?这是最大的问题。
问:在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上,你一直都把板子打在政府屁股上,你觉得房地产商其实在里面并没赚多少钱,不应该为高房价负责?
谢:如果把他们交的税都算进去,开发商真的不赚钱。
土地增值税是60%。地方政府财政一有压力,他就去找开发商,说你必须给我交土地增值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楼盘卖到最后,开发商都会留一套不卖,留一套房子他就保留着项目公司,跟政府说,我的公司还在,房子没卖完,不交税。于是地方政府就说,那我先预征,我算过了你应该交六个亿的税,现在先交两亿吧。开发商原来都是靠不交税赚到钱的。等到六亿都交给政府,开发商根本没赚多少钱。
你可以去分析房地产公司的净资产。比如绿地集团这么大的公司,你看它整个公司的价值全部是靠土地升值来的,造房子本身是不赚钱的。它最初买了一块地造房子,卖了房子赚了钱,然后把赚的钱全部投进去,还不够买同样地段的另一块地。就只能再去银行借钱,买地段更差的一块地,再造房子,卖掉以后,再拿出全部的钱,同时还要向银行借钱,再去更差的地段继续造房子。所以你看它越做越小,它一直滚动下去但是其实根本没赚什么钱。
再来看万科。这么大的房地产公司,分析员发现它公司的资产构成,其中70%都是靠高价发股票赚来的,也就是说,万科的钱大部分是从股市赚来的,靠造房子卖房子并没有赚多少。所以中国的开发商是不赚钱的,即使他们靠造房子赚了钱,做大了,政府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把钱拿走。
去年全国卖房子一共卖了4.6万亿,把建筑成本、毛利、土地税都算下来,这4.6万亿里面政府大概赚了75%,也就是3.5万亿多。去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总共才7万亿。
问:所以房地产泡沫主要是政府卖地造成的?你判断泡沫的标准是什么?高房价?空置率?
谢: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量,一个是价。
量,就是空置率,中国现在有大量的空房子。现在城市里的商品房大约有六千万套,空置率是25%到30%。这还不包括企业造的房子,企业自己造的房子大约有三千万到四千万套。我到长沙去,看到湖南广电集团造了很多很多房子,都是给员工的福利房,质量是非常好的,不是宿舍,是完全可以跟商品房竞争的那种房子。
但是我不知道员工有没有产权,是不是可以到市场上卖房子。我看到有些是员工自己住,也有些是进入市场的。自己造房子的民企国企都有,中粮、三一重工,都造了很多房子给自己员工住。全国各地这些企业造的房子,还有一些小产权房加在一起,空置率差不多也是25%到30%左右。
问:这个空置率的数字是怎么得出的?
谢:空置率本来应该是政府统计的,但是政府没有做这个事情,或者它根本不想把这个数据搞清楚。
我说的这个空置率是观察样本来的。如果你知道一个总数,然后在全国各个城市去随机抽样的话,100个样本下来得出的数据就是比较准的,可以代表整体。我在全国各地,到任何城市去观察,差不多都是这样,25%到30%这个空置率我认为差不多。
那么,已建的六千万套和企业造的三、四千万套加起来差不多一亿套,算100亿平方米吧。再加上城市原来100亿平方米的老房子拆迁等等,这些都加下来,就是已建的和在建的城市商用住房大约有200亿平米。
按照每人平均20平米来算的话,就意味着中国现在已建和在建的房子够10亿人住了。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全部完成,城市人口达到最高点,也就是10亿人吧。因为一般城市化到70%就到头了,一些岁数大了的农村人是不愿意进城定居的。
对比一下其他国家,日本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6平米,欧洲也不过20多平米。所以,从量上来看,中国造的房子已经足够住了,不用再造房子了。但是你看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土地都准备好了,他还要继续把地都卖出去造房子,我估计还得有30亿平米。到时候那么多房子怎么办?
再从价格上来看。看房价是不是合理,一个是看房价跟工资的对比,再一个是看房租回报率。
一般国际上来看,比较合理的是,每平米的房价跟一个月工资差不多。如果房价一直涨,那么你的工资也应该差不多同幅度增长。但是你看,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四千块,但是房价平均是每平米二万六,超过五倍了。而且还没有把税算进去,中国人买房子的税是很高的,再把要交的税折算进去,房价就更高了,当然是不合理的。香港现在也是这样,房价差不多是香港人四个月以上的工资。而东京和纽约的房价差不多是当地人一个月出头的工资。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看房租回报率。世界上正常的房租回报率一般是7%,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房价一直跌的话,房租回报率就会高,比如日本、德国的房租回报率都在10%以上。而香港在97年泡沫最严重的时候,房租回报率是2%左右。大陆现在的房租回报率是3%左右,按7%的合理水平算下来,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房价高了至少一倍,所以泡沫是很严重的。这是“价”的泡沫,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量”的泡沫。
房地产“量”的泡沫比“价”的泡沫更糟糕。糟糕的就是很多人看不到那些空房子,意识不到空房子都是存货的概念。最后泡沫爆掉,一部分空房子可以折价卖掉,就没有损失,那些卖不出去的空房子,就成为烂尾楼,这是真正的损失。还有,政府在房地产业赚了那么多钱,用来搞形象工程腐化掉了,把钱浪费了,这也是真正的损失。
问:但是房地产业的增长,也有真实需求在里面吧?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才刚起步嘛。
谢:不是的,中国房地产的增长和一般老百姓的需求关系不是很大。两亿多人进城工作生活,他们哪里买得起当地的房子?
在上海的调查,不住上海的外地人来买房的、还有买二套房、三套房的,这些占到全部买房者的六七成。刚才我们算过了,中国的房子从供应来说是足够的,不能说已经绝对过剩,但是人均有20平米,相当不错了,但问题就在这里——真正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而买得起房子的人,他自己不缺房子住,却在不断地买房子。
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国社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灰色收入。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少?几年前我听央行说有三到四万亿,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定义灰色收入的。因为在中国,灰色收入是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做小买卖的不报税、医生老师拿红包、大卖场里的采购员拿回扣,民间的商业腐败是很大的。
但是我说的灰色收入不包括这些,我是按照国际上对灰色收入的定义,就是指与腐败有关的收入,中国官方的腐败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刚抓起来的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他在一个小区里面拿了20多套房子。
其实当官的都特别明白这些道理,他知道货币供应量那么大,通货膨胀会很厉害,钱会贬值,而且中国人第一次可以有机会买卖房子,他就拼命买。所以中国有这么多空房子,跟这个有关。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房地产业在回笼灰色收入。以前官员的灰色收入都往国外跑,现在都跑到房地产去了,那么最后还是都回到政府的口袋里去了。
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个,它成为官员灰色收入躲藏的地方,它带动了房地产业的投机,造成泡沫。昨天我跟一个老板聊天,他问一屋子的人:你买房子亏过么?没有吧。一个一个问下来,他说:看,没有人买房子亏过吧?继续买!另一个,它会带来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方面空房子那么多,一方面老百姓买不起房子。这是很大的隐患。中国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政府在坐庄。
未富先老?
问:刚才我们说到,农民工进城多年也买不起城里的房子,所以城市化这么多年了,“农民工”这个词没有消失,而是出现了“农二代”和“富二代”这些阶层。但是“中产”,这个保证社会稳定的核心阶层好像始终没有形成?
谢:中国的中产阶级其实已经开始有了,但是中国现在的“中产”看上去不是“中产”,只是因为房价过高。中国的房子现在比美国还贵!这怎么可能?中国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三四千万,按照国际的定义,他们从技校、本科毕业的收入可以算是中产了,但是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中产。
问:我看美国电影里说,美国人只要有套房子,房子前面还带块草坪,就觉得自己是中产了。
谢:在美国你有吃有穿,有房有车,每年还能出去度假一次,就是中产了。中国的中产主要就是因为房价太高,所以觉得生活压力很大。
问:“富二代”生活没有压力,成天飙车,泡妞。这个阶层到底占有多少财富,有数据吗?
谢:中国所谓的富豪榜都不可信,很多有钱人的财富都是虚的,背后都是一屁股债。在中国靠做正当生意赚很多钱是很难的,所以说那些富豪、富二代有多少钱都是不可信的。真正的财富都是我们刚才说的灰色收入那一块。
政府在房地产业的这个游戏能玩下去,也跟中国人的观念有关,他就是要买房子,一定要把几代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富,都拿给小孩在城里买房子结婚,这完全是非理性的,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父母这样做,所以让政府一直有的赚。
问:这是文化上的因素吧,中国人追求“成家立业”。
谢:就是不安全感,普通老百姓的不安全感让政府的游戏一直维持下去。政府说,你活该嘛,租金不算高,但是你非要买。你看中国历史也从来都是这样,可以做下去,就凑合着做下去,实在做不成了,再推倒重来。
问: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还有“老龄化”,你文章中写到日本被老龄化拖累的景象是很悲惨的。那中国该怎么应对老龄化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么?
谢:现在放开也来不及了呀。而且按照国际经验,农民一旦进了城,生育率是不可能很高的,城市生活压力这么大,生养孩子的成本也很高。所以,中国以后就会出现日本现在的景象。你去日本看,只有东京和大阪还有活力,其他地方都是老人。
那么日本的解决方式,就是一些老人继续工作。我去年在日本京都、奈良,遇到70多岁的老人开出租车,餐馆里做饭的也是老人。所以,面对老龄化社会,是不是就要让老人都去佛罗里达养老?也未必。我看那些老人精神都不错。所以我觉得日本这条路也挺好,我们可以借鉴。
当然,日本的经济是没救了,一个老龄化社会,它的经济不会增长了,房价还在往下掉,股市也起不来,老人家才不会去炒股。
问:日本在老龄化之前毕竟还富裕过,中国会不会“未富先老”呢?你在书中也提出这个问题,中国未来十年究竟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社会?
谢: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中国有一天是要搞革命的,整个社会都会出现大的波动。中国核心的问题是官僚资本主义,是政府本身的问题,它体现和暴露在房地产泡沫和灰色收入上。所以最根本上,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体制,你不能靠泡沫来发展经济。太多的钱集中在政府手里是不好的。
问:香港政府财政增收,就退税给每个香港人。我们的财政连续增收很多年,但是财政部说,大陆的税制结构比较复杂,没有办法发给每个人。
谢:政府要抓人的时候,怎么谁都抓得住,要发钱的时候就找不到人?每个人都有身份证号码,拿着身份证去中国银行领嘛,这有什么难!
玫瑰石的传说
问:你在观察中国经济的时候,主要是看数据,还是去地方考察?你怎么确信你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判断是准确的?
谢:数据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数据都不准,不可信,你看最近发布的通货膨胀的数据,明显不可能嘛!
所以观察中国经济,就要自己辛苦一点去了解真实情况,去地方看,看地方政府和企业。一家企业,它哪怕只做一种产品,只要它是面向全国销售的,那么你就能通过它看到整个中国经济。而地方政府是横向跟整个面互动的,所以看地方政府在做什么,你就能掌握整个面的状况。因此这两个渠道是非常重要的,都要切入去了解和观察。
所以首先是我自己去搜集数据,第二就是怎么来分析。经济学特别复杂,它的体系里充满了无数的变量,所有变量交织在一起。在分析这些变量的时候,要怎么去抽象化、具体化、简单化,就是个分析方法的问题。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这个需要你的判断力。但是中国的问题更复杂,因为中国是政治经济体系,它不是市场经济体系。
问:你在国内读本科时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后来去美国读书为什么转成了经济学?
谢:对经济学感兴趣。我觉得经济学最能反映西方的思维方式。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把问题系统化、抽象化、简单化。不像中国的思维方式,就是阴阳什么的,它不去把事情背后那个道理想明白,不要搞得太清楚,不要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科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也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是实用主义,把牛顿定理拿来用,但不去想定理背后的东西。所以,中国要创新,就要从思维方式上改变。
不过这也需要时间段。你看日本,它是在泡沫爆了以后,整个社会的心态才平和下来,才开始反思,然后二十年里出现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中国从历史上到现在,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它始终是一个官僚社会,以前是官僚农业社会,现在是官僚工业社会,核心一点也没有变。
问:你在国内读完本科,之后的求学和工作一直都在西方的大学与机构里,因为你更认同西方的文化么?
谢:我觉得中国很多企业也不错,但是在中国的企业里面会比较累。因为中国什么都是要讲政治的,要搞好关系,它的思维方式过度复杂化,总是考虑这个人怎么想、那个人怎么想,所以中国人活得很累的。
西方社会就非常简单,所有人都围绕两个参照系来生活,一个是法律体系,一个是宗教体系。个人是自由的,个人也有限制,但限制是你看得到的,就像你知道自己在一个游泳池里水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愿意蛙泳、自由泳都随便。中国不一样,非常复杂,没有个人,个人不自由。
问:你的祖籍是上海,海派文化在你身上有痕迹吗?
谢:上海本身就是一种大城市的文化,它属于江南文化,跟中原文化是很不一样的。江南文化一直就是比较理性的、商业的。所以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它一直是生产力最高、最富裕的地方,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历来都主要来自江南地区。所以,江南文化跟西方文化是比较接近的,相对简单,所以中国最早的现代化也是从江南开始的。它不像北方文化的传统,就是搞好关系,巴结领导,一个人生活的全部起点和中心就是这些。
问:你是经济学家,我想知道,经济学的本质在你看来是解释世界的,还是解决问题的?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很瞧不起那些一心要给政府当智囊的经济学家,他说经济学家应该面向大众去传播知识,解释世界。
谢:经济学本来应该是解释世界的,但是现在中国哪里是这个样子?经济学全部是用来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要不要印钞票、要不要加利息、要不要对碳排放征税。经济学家全部在做这些事情。
问:那你自己呢?你书里说,中国的经济政策要很好地执行,最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谢: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从来都是为了当官,这个和西方也很不一样。在西方,如果你说你是知识分子,那你的起点就是批评政府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这样。
我自己就是喜欢说,没别的,我只是提供一些想法供大家思维。
问:那你是说给官员听,还是大众听?
谢:都有啊,不一样的听众。我十几年前就在凤凰卫视做节目,一些地方官员跟我说,“我的经济学知识都是从你那儿来的,听你在凤凰卫视讲的还挺有道理的,而且我还听得懂。”我觉得也挺好。我给彭博社写文章,我知道它的读者都是基金经理,我给财新那里写,我知道有好多小股民会看,那么我就要写的很具体、逻辑清楚、解释明白。
但是中国跟美国不一样。在美国,奥巴马会叫人坐成一个圆桌讨论问题,在中国不是,中国人都是形象思维,中国的官员总是讲:你给我举个例子,谁干过,后来怎么样?而且中国官员讲任何事情都是和吃有关,这个好吃,那个难吃,这个我吃不下。中国人历史上穷怕了,所以整个中国文化都是从饿肚子来的。地主家吃肉都不容易,所以革命就是吃地主的饭,住地主的房,睡地主的老婆,就是这么简单的思维。
问:“玫瑰石顾问公司”是你起的名字?“玫瑰石”这个名字很好听,有出处么?
谢:对,我起的名字。这是古埃及留下的一块石碑,后人在玫瑰石那个村庄找到的。它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为了记录功绩刻下的一块石碑,上面的碑文有三种语言,但是失传了,没人看得懂,这块石碑就叫做玫瑰石。后来,一个德国人花了20多年破译了碑文,让死亡的语言又复活了。这段历史很有名。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它反应了一种对知识的追求,而且是跨时代、跨语言、跨文化的,我非常喜欢。
问:听说你经济学之外的兴趣是历史,很喜欢《罗马帝国衰亡史》这类书?
谢:是,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我出国以前把中国历史都通读完了。
《罗马帝国衰亡史》,我为什么喜欢它?你看写这本书的吉本是英国人,在他的时代英国已经开始崛起了,他在罗马旅游时,看到那么多古迹废墟,他就想,为什么这么辉煌的帝国就变成废墟了呢?他就去探求背后的原因,然后花了很多年时间写了这本书。
如果中国人解释这个事情,就会说这是天意,是周期使然。西方人是不相信什么周期的,他就去军事政治这些方面找原因,最后,让罗马垮掉的其实是腐败问题。我比较喜欢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去探索背后真正原因的态度。
问:我们看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是大思想家,亚当·斯密、熊彼得、哈耶克等等,他们的工作最后都是为了捍卫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那么你作为经济学家,是为了探索事情背后的因果,追求纯粹的知识上的乐趣么?
谢:我就希望中国人的钱不要被骗走就好了。中国人都有贪小便宜的心理,在房地产、股市不是都这样嘛?看别人赚一点,我也想赚,结果辛辛苦苦攒的钱转眼都没了。中国人好不容易才富了点,我就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的钱看好,不要被骗走。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