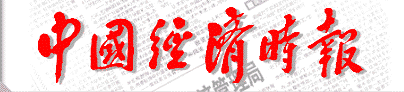自由与平等(四)
■陈季冰专栏从古希腊到现代欧美,自由与平等——实际上也可以称为“权利与福利”或“效率与公平”——一直是西方社会中一对难以克服的矛盾。正如秦晖教授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在西方,左派执政,社会将增加福利,减少自由;右派上台,则正好相反。自由要求限制政府权力,而平等则必然要求扩张政府权力。
但在我们这里,近年来许多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其实就是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实际上是一对虚幻的矛盾。就像秦晖一再强调的,在发达国家,与“效率”相对的“公平”是指结果平等而言。竞争出效率,但竞争的结果有输赢之别,输赢无别的“平等”等于取消竞争,因而会影响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效率和公平”确实是个两难选择。然而从来没有人会认为竞争过程的公正与效率不相容,因为过程的公正恰恰是竞争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而也是效率的前提。因此“效率与公平之争”从来就不是针对过程的公正而言的,在过程中如果没有公平也就不可能有效率,如果没有效率,那必然意味着现行制度是不公平的。
我们这里最常见的现状是:一方面,在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存在着大量人们熟视无睹的“过程不公正”。也就是说公民(或团体)因为出身、户籍、所有制等许多原因被分为三六九等,享受不到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有些个体和团体受到国家行政权力的特殊眷顾,而另一些则被重重限制。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民意却又念兹在兹所谓的“结果平等”。用秦晖的话来说,在盛行“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今天,有人忙于论证“抢来本钱”是如何不可避免,是飞向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有人则忙于抨击“做买卖”是如何败坏人文精神,是造成社会不公的罪恶渊薮。却很少有人在为公民争取“做买卖”的权利的同时,向“抢来本钱”者做正义的抗争。事实上,如果真做到了“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且后来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我们现在的贫富悬殊又何至于如此严重!
于是,我们的必然情形是:当社会呼唤公平时,国家权力肆意扩张,从而导致自由减少,本来应该预期的“平等”却未见实质性的增加;反过来,当社会呼唤效率时,则在过程中的暗箱操作、钱权交易甚至贪污腐败被视为“思想解放”的改革探索,从而导致福利大幅度减少,而本来应当由此换得的“自由”却未见任何落实。那些理想化地希望获得平等的人也许永远都不会明白,他们的全部努力换来的很可能是包裹着一层薄薄的“公平”糖衣的强权而已,这是我所能预见的最暗淡的一幅图景。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