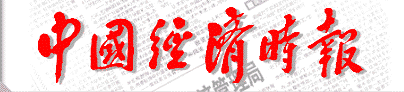怀念钢鳅
■杨绍碧钢鳅,是昔日家乡小河里的一种鱼,似泥鳅而非泥鳅,通体浑圆细长,状如钢条。说是“鳅”,不钻泥、钻沙。说是“钢”,咬得动、咽得下,竟是一美味佳肴,肉多骨少。肉质鲜美细嫩,骨少且细短,且容易剔除,无论怎样吃都没有鱼刺在喉之虞。
它全身淡黑带黄,黄里透红,尤以头尾部为最。胸鳍、尾鳍色泽鲜亮,状如胭脂瓣儿。只五七厘米长,最大不过十厘米,有成人小指头般宽,扁平,尾鳍不分叉。从头到尾排满整齐而且清晰的黑色斑点,一般十个左右,背部两侧也布满斑点,但不规则,看上去仿佛花豹、仿佛斑马。
钢鳅子繁殖快、生长快、性贪食、喜洞居,也很容易钓到。在家乡大人小孩都喜欢它,喜欢看它、钓它、吃它,而它的数量似乎永远在小河里占绝对的优势,钓之不尽,吃之不竭。
记得童年的时候,那时家乡的小河很宽阔,河里深潭浅滩相连,水清见底。小河两岸的野麻柳、野核桃、野李树等杂七杂八的树木茂盛,枝叶交相掩盖,把小河遮得阴阴的、凉飕飕的。春天,那小河宛若一条充满绿意的带子;夏天,小河却掩隐在绿色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秋天,在半山腰望小河,觉得它好细长、好悠远;冬天,在高高的山上看小河,山脚下蜿蜒的小河在枯枝间隐隐约约。
那时,小河里的鱼很多,鱼里面钢鳅子又最多,随处可以见到它们在清水里快速游动,细长的身躯柔弱无骨又刚劲有力。春天、夏天、秋天,天气好的时候,就跑到小河里钓鱼。钓木叶鱼、麻鱼子,而最好钓的就是钢鳅子。一根长长的箭竹节杆,两三米化学线,小小的鱼钩用牙膏皮做坠子,钓钢鳅子的工具就成了。小河里像开碰头会一样聚在一起的大石头是钢鳅子最好的窝。挖上几根蚯蚓,或伸手在水里捞一把小石头,从中捉一条眠虫穿在钩上,把钩放到洞口轻微地抖动,不一会儿,钢鳅子便围着鱼钩上下翻动、绕来绕去,煞是好看。鱼竿一有闪动就往上扯,一扯一条,一扯一条……
儿时的钢鳅鱼汤,好鲜、好美、好香,我一直喜欢喝,也喜欢钓。每到夏天的星期天,我都会邀约几个小伙伴到离家不远的小河去钓鱼。天刚亮就出发,下午回家,总是大半竹篓,可装大半脸盆。到屋前的小溪沟破腹洗净后,采些小茴香、鱼香草,就让外婆给我们熬鱼汤,那味道鲜美自不用说了。
三十多年过去,每次回到老家,再也没有喝到那样的味道了。
不知何时起,小河渐渐变窄了,小河的对岸半山腰已经有了一条公路,河的对岸山上有了一座铁矿,河滩上有了几个石材加工厂,河中的石头变多了,有些地方几乎断流;河水混浊地从石缝中流出,河两岸的杂木也渐渐少了,能看见的都低低矮矮,伤痕累累。
不知何时起,河里的钢鳅子渐渐没了,在我的印象里好像突然就没了。当我意识到没见到它了,刻意去寻找的时候,再也难觅它的踪迹了。我问家乡的同龄人,说那小河里曾经有个。我也问过家乡的小孩,他们竟不知道钢鳅子是什么样的鱼!
小河是我小时最爱钓鱼的地方,也是现在我回老家的必经之地,河里、小溪里已经少见“鱼翔浅底”的迷人镜头了。河里没有了鱼的原因也很简单,生态环境的破坏,河流的污染,让鱼遭受了灭顶之灾。
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在河的下游西清河段散步,希望可以看见钢鳅子的身影。可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不但没有钢鳅子,连著名的桃花斑、斑鱼子、木叶子也不多见了。
我更加想见到钢鳅子了,想找几条放回家乡的小河里。我问附近小河、溪里有什么鱼,小孩子们稚气地告诉我“只有木叶子”,而不知道钢鳅子。当我努力向他们描述钢鳅子,面面相觑的他们过了半晌才对我说:“没见过……”我的心突地悲哀起来。
不过,我相信钢鳅会回到那小河的,今年回老家,那小河的水变清了。河滩的石材厂搬了家,山上的铁矿建了尾矿坝沉沙池,山腰的公路进行了硬化,河水不再污浊,久违的钢鳅一定会鱼跃于河底的。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