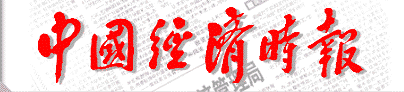诗一定要读得懂吗
■王万然笔者自小爱好诗歌,读了顾城的朦胧诗后,怦然心动,虽猜不出写什么。顾城、舒婷、北岛等朦胧诗派的作品读多了,恍然和诗有种灵动。后来自己创作,不少朋友和年纪大的诗人都说读不懂。甚至有人问写的是什么意思,笔者只能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著名青年诗人杨克说,过去的诗可以背诵,现在的诗无法记住。他说,现代人阅读不是为了记住,只要有了感觉就好。此话我似懂非懂。
近读余光中的《读者·学者·作者》(《新华文摘》2009年第20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诗是不用读懂的。小说、散文都有读不懂的地方,何况诗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指出:“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诗无达诂,留给了读者广大的想像空间。
余光中把读者分为纯读者(诗迷)、学者和诗人。他认为:“学者读诗,因为是做学问,所以必须耐下心来,读得深入而又普遍,遇到不配胃口的作者或作品,也不许避重就轻,绕道而过。诗人读诗,只要拣自己喜欢的作品,不喜欢的可以不理──这一点,诗人和纯读者相同。不同的是,纯读者享受到读诗的乐趣,就达到目的了,诗人却必须更进一步,不但读得陶然,还要读得警醒,才能时时触类旁通,活师前人。”他举食物为例,诗迷只要求可口,诗人则在可口之外寻求营养,而学者就必须加以清点和评价了。所以,“如果你的目的只在追求‘诗意’满足‘美感’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情调’那就不必太伤脑筋只要兴之所至随意讽诵吟哦击节称赏在幻想中‘自慰’或‘自虐’一番做一个诗迷就行了”。
历史上确实有不少让读者一读就懂的优秀诗篇,如李白《静夜思》、骆宾王《咏鹅》等。但读得懂的也照样争论纷纭,如“床前明月光”的“床”是床铺还是井栏,“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是否互文,“春江水暖鸭先知”为何鹅就不先知等等,论争了千百年。而论争是那些专家、学者的工作,纯读者是不用浪费时间去等他们争论出结果来的。
读诗和听歌是同一个道理,除了专门为了宣传而一下子能让人听明白的外,其他诗、歌基本是强调旋律和意蕴的。小时候我听了一首革命歌曲,但不知道唱的是什么词,只是跟着哼,哼来哼去,就把歌的开头哼成了“一只汤匙舀鱼汁波,鱼汁好食勿啰嗦……”诗来自于歌,诗歌相通。诗经、乐府都是歌谣。以前叫填词,就是按照歌谱写诗;现在叫谱曲,按照歌词作曲。人们在唱歌的时候,虽然同时也被歌词所倾倒,但主要还是沉湎于歌曲的旋律。如《青藏高原》,不管是唱还是吼或者叫,演唱者和听众沉醉的是歌的旋律,若这时候偏偏要去弄明白歌词大意,那真是索然无味。为什么?因为歌词有问题。“一座座山川相连”,高昂悠扬,但它是病句。如果一边唱一边想着歌词是否对错,那一定是唱不下去的。
从余光中先生对纯读者、作者和学者三者对诗歌三种不同要求的阅读态度和方式中我们得到启发,只要你不是学者,就没必要去深究每句诗究竟写的是什么东西,更没必要去挖掘什么主题思想、深刻涵义。只要读了以后有一种与作者沟通的冲动,就已经被诗打动了。事实上,古诗又有多少让人读懂,还不是因为有注释而一知半解?李商隐的诗人称难懂惹得元好问叹气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也惹得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说“这些诗他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像梁启超这样的大学者对李商隐的朦胧诗,也只求愉快,不求达诂。诗为心声,把这种心声表达出来,就已经功德圆满,也没必要老想着人家读得懂读不懂。我们欢迎朗朗上口又很隽永的“白日依山尽”,也无法拒绝朦胧而又令人回味的“锦瑟无端五十弦”。杨克说:“诗是写给灵魂相通的人看的。”只要诗的意境或是一瞬间感觉,让人读到音律美或语言美,或是智慧、或是幽默或是灵动,从而产生共鸣,给人愉悦,这首诗就算好了。既不要刻意写得平白如水,更不要故弄玄虚写得像天书一样。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