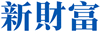朱为众:脱离国情的劳动密集产业转型
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需求,为拉动农村内需提供动力;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欣欣向荣,因此,急于产业转型未必符合中国国情。目前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告别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政府在资金、技术等方面都可以给予企业帮助,唯独不该一刀切地排斥它们。
中国进出口连续8个月大幅度下滑令人忧虑,成千上万出口企业的倒闭和由此造成的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大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现。与此同时,国内理论界就中国究竟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亚当·斯密斯在18世纪提出的理论被拍了拍积尘翻出来引经据典,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被旁征博引,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的大帽子被晃来晃去吓唬人,亚洲“四条小龙”的经验被牵强附会地用来证明产业转型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可是,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出路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依笔者之见,眼下被炒得很热的中国产业转型理论虽有前瞻性,却不符合目前的中国国情,据此制定的政策将会贻害无穷。
就业才能稳定,稳定方能发展
稳定、发展、就业,作为20国集团首脑伦敦峰会的三大主题,简短明确,令人激赏,不过依笔者之见,它的顺序应该颠倒一下,即:就业、稳定、发展。因为就业率高才能稳定,稳定方能发展。美国的经济复苏为什么进两步退一步,步履蹒跚?就是因为就业的问题没解决,虽然金融界迫在眉睫的信用危机似乎得到缓解,但失业率却随着大大小小企业的裁员屡创新高,真正可靠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失业率降低这个滞后的指标才可以准确无误地显示出来。
就业与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在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尤其如此。现在国内关于失业率的统计其实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工厂倒闭后被殃及的都是农民工(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说法,失业农民工有2000万之众),但农民从来都不在失业统计的范畴之内,农民工当然也不在,所以一方面是诸多工厂倒闭,一方面是失业率基本稳定。这一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失业率统计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次中国出口企业受创导致的失业浪潮摧毁了多少农民工的梦?当年他们抛妻别雏,挤上火车南下打工时,一路不停念叨着跟村里打工先驱们学来的民谣: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
如今,还是那拥挤不堪的列车,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浩浩荡荡地北上返乡,民谣也变成了:马路空荡荡,工厂不再忙。两手空空回,如何见爹娘?
让我斗胆说一个可能会遭国人一顿板砖的立论—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文化水平比较低,还在为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辛苦劳作,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他们是郎才女貌的“天仙配”。
今年2月,我在浙江访问一家羽毛制品厂时,惊讶于工人正用小刀一点点去刮遗留在羽毛根部的残肉。工厂老总告诉我,因为美国海关要求严格,不得不让工人一根根检验羽毛,凡是发现有残留肉迹的,一律手工刮去。我当时特别感慨,要是转型了,这些工人干什么?他们有的甚至连初中都没上过,不会英语,更不懂电脑,可是却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毋庸置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就业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
产业是唯一出路吗?
4月在台湾地区出差时,我看到《天下》杂志一篇关于就业市场最新调查的封面文章,标题赫然醒目:《高科技免谈》。为什么“免谈”?因为高科技产业昔日的光环不再,景气不再,当然待遇就不如以前,加上经济大环境也不好,企业纷纷裁员,弄得丢了工作的怨声载道,没丢工作的忧心忡忡。这样的行业既无力招收新的员工,就是招也没有人愿意去,所以就“免谈”。
其实这种情况在内地也同样存在。这次金融风暴中遭到打击的也包括很多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而率先恢复的却恰恰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最近有报道说,一些女大学生因为就业无路,计划用嫁人的方式解决失业的困境。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因为我们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处在“免谈”的尴尬阶段。它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它们的发展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欣欣向荣。
发展第三产业切勿“杀鸡取卵”
目前国内另一个很时髦的话题是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确,美国的GDP有70%以上来自包括物流、金融、零售和旅游等行业在内的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而中国的服务业产值仅仅占GDP的30%不到。表面上看,中国发展服务业的空间很大,其实不然,至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暂时不可能大幅度地改变,更是不能把这种结构性的长期战略转型用来解金融危机这样的燃眉之急。发展第三产业是远水,金融危机是近渴,远水不解近渴。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服务业的对象是消费者,中国人口虽有13亿之众,但绝大多数是农民。这些年,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已经有超过两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成为农民工,他们正成为一群不可忽略的享用服务的消费者。当成千上万的工厂倒闭时,物流企业就没有东西运输和仓储了;当数以千万的农民工失业时,他们原本购买的各种保险可能就停掉了,原来的存款可能就要提现了;逛商店购物变成了昔日的回忆;旅游更成为奢想;至于家乡父老兄弟的治病钱和学费,当然更是无能为力了。显而易见,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重创后,殃及的恰恰是我们想要发展的第三产业,两者的关系也是唇齿相依,为发展第三产业打压第二产业无异于“杀鸡取卵”。
拉动内需的动力在农村
被舆论炒作得很热的拉动内需虽然有必要,但在中国,内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取代外需。更重要的是,内需的最大市场在哪里?最终是在广大的农村。为什么要实施“家电下乡”政策?因为那里有8亿民众。可是不要忘了,8亿农民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于两亿农民工。当农民工失业时,他们哪里有钱寄给爹娘买电器呢?所以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培育内需的温床,它和内需也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满足就业需要,不就业就无法产生内需。任何运动似的“家电下乡”和“消费券”之类的活动,注定只能以轰轰烈烈开场,以不了了之告终,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为什么?因为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只要就业的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持久稳定的内需。
劳动密集型产业≠环境污染
一些专家提出的中国产业应当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转移的另一个理由就是要抑制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消耗,其实,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据我观察,随着人民币的持续坚挺,越来越多出口企业青睐进口原材料,除了消除汇率的影响外,进口原材料还有着质量好、交货期准以及符合最终消费市场的安全和环保要求等优势。这一趋势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增长的势头。
至于环境污染,更是无需因噎废食。现在各种先进的环保设备和技术不但非常成熟,而且价格日趋合理。随着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要求的不断提高和购买国对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国内企业的环保意识已经从最初的“要我做”改变为“我要做”,迈出了缓慢但可喜的一步。这方面,政府可以给予企业帮助的地方很多,如资金的资助、技术的扶持等,唯独不该做的就是运动式的“一刀切”,排斥劳动密集型企业。说到底,这是涉及到产权保护的制度问题,任何政策和法规的出台都要考虑长远的效果,考虑企业经营环境这个大前提,切忌朝令夕改,急功近利。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过去30年中实在是太深刻了。
把劳动密集型产业
送出去只是一厢情愿
还有人提出,非洲的劳动力如何如何便宜,仅为中国的几分之一,中国应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送到那里去,读来令人喷饭。我在美国念完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帮助一家进口商进行生产基地大转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将生产线从中国香港、台湾和韩国转到了内地的大连、沈阳、赤峰、呼和浩特、无锡和南京等市。我的老板在这之前曾经亲手策划把公司的生产从美国本土迁移到中国台湾和韩国。记得他当时对我如释重负地说:“这下好了,不用再搬来搬去了!”意思是中国有13亿人口,世界工厂非中国莫属。从那以后,我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共五家连锁店负责国际货源的采购工作,深谙其中奥秘,更加深了对当年老板一番感慨的理解。
我不但非常清楚当时为什么要把生产基地转到中国,也很明白为什么理论家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送出去的说法根本就行不通。劳动力的价格其实只是决定美国各大连锁店全球货源战略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中国除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外,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上游供应商的有效供应链、产品品质的不断提高和保证、协调产品开发的能力和30年改革开放中基础建设所形成的物流能力,是大量出口型企业赖以生存和竞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且已经形成了世界领先的总体优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实非一日之功,其他国家即使想模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送出去只是一厢情愿的事。英国谚语说“倒洗澡水别把婴儿一起倒掉”,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送出去,就无异于把一个可爱的婴儿随着洗澡水一起倒掉。
我们找对象都知道,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姚明好啊,有钱有名人也帅,可是合适你吗?郭晶晶也不错,有名有钱也漂亮,可是合适你吗?就算是你觉得合适,人家同意吗?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就业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依赖关系;就业和稳定是唇齿相依的依附关系;稳定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互助关系。中国经济和产业的转型绝不应该脱离国情去简单地套用国际上所谓的先进经验,也不应该生搬硬套某个“密集型”作为自己的出路。恰恰相反,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扬长避短走出一条有特色的经济转型之路。
中国内地既不是台湾也不是韩国,既不是香港也不是新加坡,所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业应该而且将会长期留在内地。学习他人的长处最忌东施效颦,最后落得个邯郸学步,“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那才既可悲又可笑。学习他国的先进经验,最重要的不是模仿和照搬,真正成功借鉴他人经验者,无论是个人、组织或民族,是那些能够根据国情将其本土化的佼佼者。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