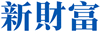经济恢复均衡之后关注结构调整
在我们所研究的的经济史中,经历大幅通胀冲击和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经济复苏往往呈现出漫长而曲折的特征,这可能是由一个经济体结构调整的要求所决定。而2009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在“大悲”之后的“大喜”似乎有些超乎预期。回想日本在经历过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V字反弹似乎与中国2009上半年的经历有些类似,当年去库存、刚性需求的释放和政策推动三个因素共同推动了日本经济在1974年末探出异常低点两个季度之后,也就是1975年的中期出现了经济恢复正常水平的特征。
不是真正的经济复苏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复苏,经济复苏的本质在于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就是收入的增长机制。对于中国和当年的日本而言,由于同处于制造核心国的地位,其收入增长机制显然来源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以,外需的缺失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缺陷。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经济调整过程必然是长期结构性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二季度经济数据所代表的含义可能在于:一方面,它具有我们前期反复提出的价格扰动后刚性需求释放的因素,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它可能也意味着两个超预期的存在。首先是中国强力的财政政策对投资的拉动;其次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泡沫化预期。这两点能够出现的根本原因都在于中国目前所处的是一个本质上通缩的经济环境。与当前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背景限制了日本的货币政策宽松程度,所以,当年日本的地产和汽车成交量的释放在6个月之后逐步走向衰竭,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泡沫化预期的影响下似乎带来了超预期的乐观。因此,严格意义上看两个超预期的因素并非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所在,而是一个将存量财富变成泡沫后迅速消融的过程,所以,此番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十分值得关注。
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
结构性机会
这种集中使用投资拉动和内需的方法能够使中国经济恢复到什么水平,对于如何评判经济增速8%的意义也十分重要。中国的工业化起飞(2000-2007年)依靠的是外需和内部城市化引擎。如果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依赖外需的再次启动,那么单引擎能够引领中国经济达到多高的增长速度呢?若抛开复杂的国民经济核算,以我们的工业化史研究经验来看,在单靠内需的工业化起飞中,如美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工业化,以及同期随后的法、德工业化,高速期的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就是6.5%左右,如果加上当前的产业结构差异和货币泡沫因素差异,8%应该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均衡增长中枢所在。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中,我们可能很难看到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
当经济增速达到8%后,未来经济继续上行的空间和难度都在加大,比较理性的选择是在此后更多地关注经济萧条期尾声附近的结构调整问题,特别是对产能的压缩和对新兴产业的培育,这都是一个经济体为了迎接可能的经济复苏所需要作出的必要准备。因此,在经济“救急”之后,我们也许应该把视线转移到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组织的调整,市场的系统性机会将转变为结构机会。
二次探底中
地产和汽车的差异
我们一再提出,经济周期中,收入预期下降将是下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2009上半年可选消费品的火爆来源于价格的下降和前期压抑需求的释放,而这种需求的释放可能受到存量财富和未来收入预期两方面的影响,所以,对未来可选消费的分歧也在于“存量财富和增量财富哪个更关键”,因此,对经济是否二次探底和二次探底的程度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与其说存量财富不如说是货币因素更为贴切,泡沫化的领域显然是受到了信贷扩张和低利率的支持,这是激发存量需求的关键。但是这种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信贷因素还没有一个顺畅的转换为收入的渠道,除非首付继续降低,否则以泡沫化激发房地产的方法终究是边际效用递减的。
经济二次探底本质上看是一个可选消费品的探底,所以,当我们观察二次探底程度从而修正我们的经济预期时,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可选消费品的持续性。只不过在2009下半年的观测中,房地产的意义在大大降低,因为其本身具有的泡沫性质决定了它不一定真实反映人们的消费意愿,从而反映收入预期下降对消费的影响。因此,我们更愿意选择汽车、家电、酒类等消费品作为观察对象,因为这些领域会更贴切地反映居民的消费意愿,从而投射出收入预期的变化特征。
三季度是过渡期
中国经济已经回归了均衡的中枢水平,在超预期的喜悦面前,大家应更多地关注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因为三季度会是一个难以超预期的季度,它将更多的成为一种过渡,这种过渡除了我们原来提出的对于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寻觅之外,还更多地带有经济能否为迎接复苏做好准备的意义。实际上,经济周期也许会被烫平,但永远不能消失,这是在超预期喜悦的同时不能忘记的。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