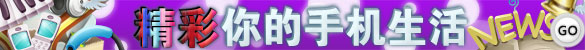迷失的中投何去何从
马光远 经济学博士
在沉寂了一年之后,关于中投重启海外投资计划的消息又在坊间热议起来。最新的传闻是,中投公司正计划数项海外收购交易,包括收购德意志银行在新加坡的不良资产等,投资规模接近86亿美元。巧合的是,这个数额恰好等于此前中投投资于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总额。
中投此次出海,显属无奈之举。想当年中投成立之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以2000亿美金的注册资本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司。然而,成立以来,仅有的三笔交易堪称“惨败”:一是用30亿美金“打新股”投资黑石10%的无投票权的IPO股票;二是斥资56亿美金投资摩根士丹利9.9%的股权;三是被媒体曝光用50亿美金投资美国老牌私募基金Primary fund。前两笔投资亏损高达60亿美金,而后一笔投资因该基金持有破产的雷曼的巨额债券而被暂停赎回,能否全身而退很没把握。
对中投的失败,业界人士将之主要归结于“天时”之不幸,颇含惋惜之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一个专业的投资公司而言,对“天时”的判断也是基本的职业素养。如果说投资黑石之时,金融风暴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话,而后来的两笔投资,基本属于冒险和赌博了,这和中国很多机构抱有的不自量力的海外“抄底”的心态不无关系。
笔者研究发现,在2008年次贷危机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全球跨国并购的规模大降60%,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规模却“暴涨”了40%,而这些急吼吼的所谓海外抄底行为,无一不败北:据笔者统计,中铝收购力拓,亏损750多亿人民币,创下了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亏损的纪录;国开行收购巴克莱,亏损200多亿人民币;平安收购富通,238亿人民币的投资仅剩10亿人民币,投资基本被清零。这些惨败的案例说明,中国企业对于投资时机的把握上,需要做的功课还很多。正如楼继伟在博鳌论坛上所庆幸的:要不是欧洲市场给中投公司的投资行为制造了很多障碍,亏损何止区区60亿美元。
一方面是海外投资的完败,另一方面却是舆论的压力和每天近3亿元的资金成本。而公司目前资产配置高达90%以上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更让人对成立中投公司的必要性打上问号。正是在这种“生存”的压力下,中投已经不堪重负,急需找到投资机会给自己正名,加上国内机构新一轮的海外抄底的冲动,中投就在这种悲壮而危险的情绪下决定再次出手了。很显然,中投已经逐渐丧失了成立之初的骄傲和自信,这是一个专业投资机构最危险的时候。更致命的是,在投资惨败的阴影下,开始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首先,中投和外管局的边界开始模糊。中投公司成立之初,制度设计似乎非常理想,将其定位为主权财富基金,并以淡马锡为模板,通过商业化的运作,为“多余”的外汇储备搭建一个高收益的平台,以此与讲求安全第一的外管局形成合理的投资边界。但随着中投的屡投屡败,中投与外管局的界限越来越含混不清。外管局不仅投资海外的政府债券,也开始涉足股权投资,二者甚至形成了竞争关系。
其次,中投的职能开始杂乱。中投名为依照《公司法》成立的纯商业化运作机构,但无论是公司的高层,还是基本治理模式,都和一个政府机关没有任何两样,高层不是来自央行,就是来自财政部。而这样的一个架构,一开始就给欧美市场对其投资行为设置种种障碍提供了十足的借口。而且,公司在成立的时候,将主要承担政策性功能的汇金公司揽入麾下,这样,名为商业机构,实际却要承担很多政策性的使命。比如,中投通过汇金公司注资农业银行和国开行200亿美金,究竟是政策性投资还是商业性投资?如果是政策性投资,显然违背了其成立的初衷;如果是商业性投资,谁又为这些投资的风险承担责任?因此,就中投的基本运作架构和职能而言,成了一个非牛非马的东西。
第三,中投开始不敢出海,想到国内觅食。中投成立之初,用意极为明显,就是把当初泛滥的流动性“引出”国门,投资海外市场,按照其章程,主要投资于商业化的金融产品,比如债券、股票、基金、衍生金融工具等。尽管章程没有说不能投资国内,但如果投资国内,事实上在技术上就必须进行二次结汇,外汇储备又回到了央行。但海外投资的挫败,很明显已经让中投对海外市场没有了信心,竟然开始投资于中铁这样的项目。但如果其投资国内,无论是股市还是实业,和一般的投资机构又有何异?
笔者认为,鉴于中投目前的心态已经完全“走坏”,为“正名”而盲目出手,再次受挫的可能极大,况且金融危机是否到底,的确不敢轻易下此赌注。与其冒险“出海”,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自己的定位和投资策略。
首先,中投应该坚持商业化的定位,笔者建议将汇金公司从中投独立出来,让中投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业化运作的机构。不要轻易涉足所谓战略性资产,也不要轻易给中投赋予到海外为中国收购资产或者技术的重任,欧美市场对此防范很重,而是让中投老老实实去赚钱;其次,中投应该好好设计其资产配置,不要眼睛就盯着股权投资,也不要就盯着不良资产,更不要没出息到想回国内炒股;第三,中投的眼睛不要只盯着欧美市场。事实证明,对于海外投资而言,新兴市场的收益远远大于成熟市场,中投应该将一部分资产配置到新兴市场;第四,中投自己的水平肯定不行,所以在投资上还应该以选择投资管理人委托投资为主,而且,在高管都是官员的情况下,在中层配置一流的人才就成了中投生死的关键;最后,当然是中投的运作模式,官僚化的运作决策机制,可能永远成为中投最大的竞争短板,在现有的体制下,如何弥补,恐怕还需要中投好好去探索。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