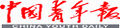IMF中国执行董事: 超主权国际货币是改革方向
本报记者 潘圆
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论”如一石激水,不仅各路专家为此群起争鸣,而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回应。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随后也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呼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至此,这轮由政府官员掀起的“货币战争”,不仅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引向了更富有建设意义的层面。而且在G20峰会前夜,货币问题的升温,尤显得意味深长。
“周小川的文章,实际上给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身在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执行董事葛华勇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专访时指出,“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改革的呼声也日益迫切。在这一时机提出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如果能引起国际社会重视,推动相关研究,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中国的提议正得到更多国际知名人士的支持。3月26日,联合国大会收到一份报告,由联合国设立的顾问委员会“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提出,全球领袖应尽快关注就创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达成共识,该体系将取代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G20会议讨论的一项内容。但能否取得进展尚有待观察。”葛华勇坦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一项长期任务,近期美元的主导地位不会发生改变。”
SDR有可能成为一种超主权国际货币
3月23日,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表文章,倡导“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周小川指出,“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葛华勇强调,创造一种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应受到世界各国监督。但实际上,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发行货币时,首要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需求和货币政策,这必然会与世界利益相冲突。”
3月18日,美联储表示,将收购至多3000亿美元长期美国国债,并将另购入至多75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是美联储40年来首度购入长期国债。消息传来,美元指数遭受24年来最大单日跌幅。专家认为,这种“印钞行为”不仅加剧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而且进一步引发人们对美元贬值,全球通膨趋势加剧的普遍忧虑。但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对储备发行国的这种“发钞行为”缺乏有力的制约机制。
“这也使得创造一种超主权货币显得更加迫切。而目前要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最大的障碍来自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因为这意味着它们既得利益会受到影响。”葛华勇说。
在文章中,周小川除了提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外,还提出推动特别提款权(SDR)分配,扩大其使用范围。“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IMF)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SDR是国际储备的一种,是IMF的计账符号,但不是支付手段,不能用于国际贸易的结算,不能进行商品标价,还不能算作一种储备货币。”葛华勇解释说,目前SDR只有IMF在计算国际储备时使用,可在各国中央银行间使用,它与美元、欧元、英磅、日元四种储备货币挂钩,也可兑换黄金。目前IMF只有200多亿SDR,数量太小。如果扩大SDR的分配和使用范围,允许其标价使用,SDR将有可能成为一种超主权国际货币。
外汇储备不是出资多少的依据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各国政府纷纷推出了资金庞大的刺激经济发展计划。日前,德国媒体批露了一份由英国起草、涉及2万亿美元全球性财政刺激方案的G20会议公报草案。虽然英国方面随即作出回应,称德国媒体所刊登草案实为一份“数据已过时的旧文件”。但专家预计,涉及巨额资金的刺激经济计划显然是G20会议的题中应有之意。IMF总裁卡恩3月27日也在提出的几个希望峰会能取得成果的关键问题中,提到希望增加贷款资源至少达到5000亿美元。
3月27日王岐山副总理,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表示中国愿意买入IMF发行的债券,为扩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库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但同时强调,在增资规模上,要考虑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人均GDP水平、外汇储备资金性质和形成、积累过程以及本国经济安全对其依赖程度的巨大差别。简单以外汇储备多寡确定出资规模既不现实也是不公正的。
葛华勇认为,危机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应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依靠发展中国家来救发达国家,不能让人均GDP远低于危机国家的穷国去拯救富国。现在向IMF借款的冰岛、匈牙利等国,其收入、人均GDP等都比中国高。像冰岛的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几倍。“让穷国出资借给富国,是本末倒置。而且从经济总量等多方面因素来考虑,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能力来救发达国家。”
“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多,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说到底,这仍然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各国为了保证金融安全,都相应增加了外汇储备。因为一旦出现金融危机,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可通过发钞票来应对危机,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并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不能采取这种手段,所以只能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做大,以防范金融风险。”葛华勇指出。
葛华勇强调,“现在支持IMF增资,应该坚持‘责任权利挂钩’的原则。现在很多人把目光盯在了日本和中国身上。去年,日本向IMF提供借款1000亿美元。但中国不能和日本相比,日本本身就是发达国家。它不但外汇储备高,而且国民的海外资产、人均GDP等也比中国高得多。我国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人均外汇储备相当低。因此,在对危机的救助中应坚持力所能及的自愿原则。比如按在IMF所占份额出资,即在IMF份额占多大比例,出资时就出多大比例。”
他认为,中国对国际社会尽义务应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对IMF临时出资是一种国际合作,但中国应对危机并不仅限于此。“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这是最主要的贡献。现在很少有发达国家能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的稳定增长,将对世界经济起到积极作用,这是最大的贡献。”
“目前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一旦这些国家出现危机,就可能通过人民币支付体系来购买产品,这也是一种贡献。”
作为政府间国际金融合作组织,IMF赋有促进国际货币金融合作、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然而此轮危机中,IMF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问题。葛华勇认为,要解决IMF的资金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扩大份额。众所周知,基金组织是根据份额确定投票权的,目前中国在基金组织所占份额为3.72%,投票权3.66%。
基金组织份额,类似于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各成员国在加入IMF时,都要入缴一定的份额。目前IMF份额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贡献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其经济地位也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但这些并没有在份额中得到体现。葛华勇认为,“要解决IMF的资金缺口,就必须改革IMF份额分配比例。IMF不应成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应有广泛性、代表性,应是185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
本报北京4月1日电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