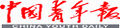货币战争硝烟缘何笼罩G20(2)
目前,总额度3000多亿美元的IMF遵循“谁出资多谁权力大”的原则。美国拥有17%投票权,欧洲国家整体占40%,发展中国家总共约占30%。最关键的是,美国在IMF中拥有“一票否决权”,基本上左右着该机构政策走向。
至于特别提款权(SDR),相比目前全球7.7万亿储备货币的总量(美元占63%、欧元27%)来说,数量很小,想要“一统江湖”成为世界货币,仍属天方夜谭。
“理想化,但操作性不强”,这是多数分析人士对SDR的评价。向松祚讲了个故事以说明“货币的本质”。
1944年,在决定战后经济格局的布林顿森林会议上,有两套世界货币方案摆在各国代表面前。其一是由美国财政部长助理怀特提出,就是IFM和SDR的前身;其二是经济学家凯恩斯设计的国际清算单位班柯(Bancor)。有人把两个方案拿给罗斯福。
当时,这位历经铁血考验的战时总统看了看,然后说:“为什么要这个?不是有美元吗?”
要形成“大中华货币圈”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对G20会议看得很淡。
“这一次,我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也顺应了各国民意”,但是,宋鸿兵说,国际金融制度与国际政治现实一样,“实力才是最重的砝码”。
宋鸿兵对即将到来的全球货币角逐提出了自己的理念:货币的背后其实是战争!19世纪英镑地位确立背后,是大英帝国强大的海军作为后盾,而20世纪中叶以来的美元霸权,也是美国的核武器和遍布各大洋的12艘航空母舰捍卫的结果。
“美元的地位既是主权货币的问题又是主权货币的答案。如同霸权所带来的利益一样,它既造成了人们的不满,又是人人追求的理想。”他说:“就人性而言,超越自身的利益,恐怕是22世纪人类也无法企及的境界。人们即便可能超越主权,却无法超越利益。”
向松祚强调,中国人构想世界货币,必须首先弄懂“中国的利益何在”。人民币最应关心的现实问题,是强化自己“区域化货币”地位。比如,先将港澳台联系起来,形成“大中华货币圈”,然后逐步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合作,形成以新加坡、香港、上海为纽带的大金融圈儿。一个强大的人民币货币圈,未来会与美元、欧元等形成货币的“战国时代”,世界货币只可能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
他说:“当下你要先问问,自己有多大能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表示,在G20会议之前中国主动出击,全球金融改革大合唱中发出先声,这具有积极意义。
“以前的声音主要由政府首脑发出,一言九鼎,惜字如金;再就是学者之声,多为一孔之见,即有卓识,也是人微言轻。”他说,周小川既是官员又是行家,提供了庙堂和书院之外的另一种意见。
这位战略研究者也特别提醒,全球金融体系是霸权体系,“美国只生产美元,而全世界生产用美元购买的产品”。如今这个游戏有点玩儿不下去了。欧元也想用货币去占全世界便宜,但这次欧洲国家损失也很大,试图夺位的欧元有些投鼠忌器。
滥发美元是金融危机的病根,但别指望美国人自己会动刀子解决。乔良说:“病人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做手术。那需要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现在有吗?”
很多人怀疑《货币战争》的结论,但所有人都关注它所提出的问题:世界金融秩序的演进绝非是一个风平浪静、自由竞争、民主决策的过程,而是一个斗争、博弈的过程,每一次世界金融规则“升级换代”,都是一场充满周密谋划和残酷角逐的“战役”。
“周小川的建议是释放烟雾弹。”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彭晓光认为,中国人不是不明白IMF的底细,但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必须在审慎应对危局中谋求国家利益。
他说:“关键在于,中国已经参与了。”
本报北京4月1日电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