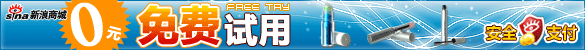|
|
无法回家的人(之三)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1日 17:44 21世纪经济报道
杨磊 子弹穿过后的伤口似一块荣耀的奖章,对于革命军人谭凯旋来说,这是价值非凡的一枪。从那一刻起,他告别青涩少年,一跃成为浴血重生的英雄。 在后来的见面中,他总是有意无意地亮出自己的伤口,在酒桌上一遍遍重复受伤刹那萦绕在脑海中的歌声。周围的人很用心地听着,露出或敬畏或艳羡的眼神,在这个时候,谭司令如英雄似的大手一挥说:"想当年,我们可从没想过能这样喝酒吃肉。" 很多人敬畏他的作派,没人知道在这个重庆人身上藏着什么样的故事。于是,大家开始叫他"司令"——在缅甸果敢这个龙蛇混杂的地方,某个人的称呼一旦被加上"营长"、"指导员"之类的军职,就意味着他曾参加过某个运动或者某场战争。 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即便是事件亲历者,也不可能完整回忆起所有的经历。很多事情于是成了传说,主人公真实存在,但故事有很多个版本。每个人都极力渲染自己的悲壮和激情。除非他们想说一个完整的故事,否则不要妄图从这些老兵嘴里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后来,我从一个人嘴里得知,其实谭司令只参加过一场战斗。当我去求证时,他很平静地说:"如果连最纯粹的理想都在事后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话,年轻时的那些经历到底是真是假还重要吗?" 我开始困惑。我接触到的每一位老兵似乎都是这样——记得过去,但似乎又不太愿记起。当别人对他们表示质疑时,他们会说出一个确凿无疑的事件,并找出很多旁证,但绝不肯再多说什么。我只好拼凑起这些记忆的碎片,然后再向当事人求证,有些被断然否认,当然,更多的是默认。于是,我一度确信,这些老兵逃避回忆,是因为他们已经彻底忘记自己的使命。希望有人能记得他们,但又担心别人知道得太多。战士失去战场时,使命感和青春的激情也同时消失。 我将这个结论说给谭司令听,等着他再次冲我发火。那是2003年底,我第五次进入缅甸。接触足够多的人后,我没有耐心再去听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版本的谭司令。我希望能激怒他,换取真实。 他好像中计了。在喝了很多酒后,我听到他念叨出一些我从未听过的人名——四川人边亚国、昆明人李俊雷、北京人张晓勇……他找出一张照片,一个个指给我看。站在红旗下的他们,一样的年轻,嘴角一律带着肆无忌惮的笑意,头发都是倔强地立在脑门上。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听到我的疑问,谭司令愣了一下,继而就哭了。我从来没听过如此凄厉的哭声,像是有鞭子抽在心上,我紧张得浑身发抖。 这是一群死人,谭司令说。在那场战斗后的第三天,受伤的他被战友拖回位于云南缅甸交界的根据地——距离云南腾冲不到30公里,后来被称为缅共101军区。在这里,他看到更多受伤的战士,操着云南、重庆、贵州等地的口音,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某一个晚上越过界河加入战斗的。 我开始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来自全国各地的青涩少年,受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感召去了农村,在理想武装下树立起"解放全人类"的信念,一场或几场战斗后,躺在异国他乡简陋的医院里,等着重上战场或者就此死去。 我因为自己的想象而有些发抖。谭司令摔了一个酒杯后说:"大家都在大声喊'妈妈',大家都想家。"这句话将我拉回现实。他说,当伤口疼起来时,哭爹喊娘才是最有效的止痛手段。谭司令很快也加入那些此起彼伏的哀嚎声里。对军人来说,伤口也是资本,哪怕他只当过几天兵。 休养期间,谭司令认识了这些战友,他们曾一起捉弄年轻的女战士,一起大声哭喊着止痛。直到一个月后的1969年7月,夜色中的营地被敌军偷袭。边亚国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等援军赶来时,营地几乎是一片血海,有人在战士的尸体堆里找到谭司令。他说,因为个子瘦小,战友们就把他压在身下,以至于援军发现他时,我几乎要被战友们压死了",回忆就此打住。 他又喝醉了,嘴里还是不停念叨这些名字。偶尔也会抬起头看看我,或者突然对我咆哮:"纪念碑呢?答应给我们立的纪念碑呢?"我不知怎么回答他。除了成片的知青墓地外,我在缅甸没有见过任何一座跟他们有关的纪念碑或是确凿的文字记录。他们呼啸而来,又迅速地消失,除了一些分辨不清文字的墓碑,好似从来就没存在过。 谭司令蜷在沙发里,让自己缩成一团。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浑身抽搐,"他们都死了,而我还活着。"声音含糊低沉,却重重撞击着我的耳膜。
【 新浪财经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