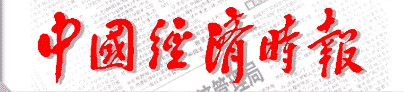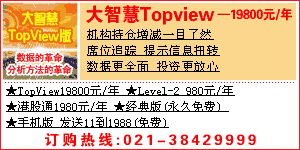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
从劳动到劳役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2日 23:41 中国经济时报
■刘诚龙 我们的小学课本上好像都写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军,学农,都在“兼学”之列,但我没学过军,我的姐姐学过,全身穿青蓝咔叽布,用一条麻绳带子捆住腰间,不爱红装爱武装,真个飒爽英姿,她们在山里打野战,这事情比什么都有趣,可惜轮到我读书了,学校不学这事了;学工我们都没学过,我们那里直到现在,还只有手工作坊味道的红砖厂,真正意义上的工厂还没有,无法学工;学农的资源特别丰富,我们也几乎天天在学农,但老师说,那是在“做农”,不是“学农”,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在学校里的,就不能叫做“学”。 就像现在什么都叫做基地一样,我们那时也叫做“学农基地”,我们学校叫“东岭学校”,坐落在东岭大队,属于大队办的学校,自然也就由大队划了一块山地做学农基地,那基地开垦之初,树林荫翳,灌木丛生,好一个“猛恶林子”,我也是小小的拓荒人,我大概读一年级吧,我的哥哥姐姐们“坎坎伐檀兮”,他们负责抡斧头砍树,我们负责把那些枝枝柯柯拖回学校,学校离基地怕有三五里路,我们一二年级三四个班百多号“虾兵蟹将”,各自拖一根两根枝桠,拖得飙走,络绎于途,首尾不可望,蔚然壮观,我一个上午要拖三四个回合,不觉其累,因为不要读书,所以还相当兴奋,干得特欢的,满头大汗,张开五指乱擦汗,把树脂泥巴全涂在了脸上,惟剩下两只清澈的黑眼珠发亮。荒垦出来后,那“猛恶林子”成了一座“红丘陵”,那模样就像青丝少女剃了个“尼姑头”,我们在“尼姑头”上开辟了一块块梯土,上面种红薯,种芝麻,种花生,种麦子,种茄子辣子豆角马铃薯……这些高级活计开始没我们的份,都是老师带领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干,每次看到他们拿起锄头、镰刀、铁锨、簸箕、扁担、箩筐到学校去,又不用读书啦,让我们羡慕不已。及长,我们到了三四年级,这活轮到我们来干,几十上百人,从山麓到山腰,从山腰到山头,银锄飞落,闹声漫天,各班还有各班的红旗招展,那情景现在想来依然动人。 春种秋实,春种一颗子,秋收万粒粮,收获时节,粮食确实爱人。红薯满簸箕地担,花生满箩筐地抬,辣椒茄子满篮子地背,谁不兴奋呢?十来岁十多岁的人能让泥土地里变花样似的变出红的、黄的、白的、方的、扁的、圆的等等粮食来,没有什么比这能有成就感的了。而那时,其实我们也是暴殄天物,我们乱挖一气,胖如小兔子的红薯常常被挖成两三节,吊璎珞吊念珠似的花生常常是挖一兜盖一兜,这就便宜了附近的农民,待我们前脚走,他们后脚跟进,把我们的土再翻一遍,总能大箩小筐,满载而归。其实,农民拣我们的便宜,我们也拣农民的便宜,每到打晚稻之际,老师们就放我们去田里检稻穗,老师在课堂里先带领我们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形同出征前喊着号子的誓师大会。许多年后,我看到莫奈的油画《拣麦穗》,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们也那样,像一群鸭子赶入广袤的秋后田野上,一穗一穗拾,一根一根地拣,一个下午能拣一大把,握在手头,背后是高秋,真像莫奈的油画。我是颗粒皆归公,有些狡猾的同学呢,他们往裤裆里塞了,往家里兜。 那时节,我心地干净得像一片白云,纯洁得像一泓秋水,我从来没想到禾穗还可以往家里兜,我也只管给学校干,也从来没去想我们种出来的红薯、麦子、花生以及蔬菜到了哪方,到了谁的仓里谁的桌上。每到收割,学校总是要给我们发一个几个作业本,老师说,这是你们的劳动成果。我们又跳又叫,欢天喜地,打着口哨尖声啸叫,老师这时候好像也挺开心与宽容,不以“扰乱课堂纪律”对我们绳之以法,让我们放肆表达心情。这是我们的半工半读?这是我们的勤工俭学?那时我们的学费特低,读小学一二年级好像只有一二块钱,高小也只有四五块,到了期末,老师还要“多退少补”,在我们的通知书上注明课本费多少,作业本费多少,总之,期末还要剩三毛两毛。我姐姐在我们那里的百年学府读初中,学费也不过七八块,期末返回最少有两三元。现在学校还会这样“期末结算”吗?恐怕是天方夜谭了吧。 人一长大了,人心就杂了。八十年代我读了初中,学费长了不少,再也没得到过不要钱的作业本了。学农基地还在,但很少去那里学农了,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教室里死读书,但偶尔也有劳动课程,比如学校要我们去煤矿挑煤。煤矿离学校十多里路啊,五六十斤担子压在肩头,来回三四十里地,也有少年不可承受之重,我们是腹诽多多了。我们在学校搭餐,交了搭餐费的啊,干吗要我们白劳活?我想起了我读小学那拖树枝,拖到学校里来做柴火,我们在学校里中午用餐,老师们给我们烧的就是这些柴火,我们不用交费了的,这是我们的“勤工俭学”吧。那么现在我们既交了搭餐钱,干吗又要我们无偿去挑煤?我们一路乱晃荡,那些煤啊,纷纷跳出筐来,到得学校,恐怕只有三四十斤了。人大了,人心真“坏”了。读初三上半期,我还去过学农基地,那是因为我调皮,放学了老师要留我的学,我以为会像以前那样把我关到教室上一把锁,老师回家去锄他家的红薯土与麦子地,结果不是,老师给了我一把锄头,叫我跟他们去。走啊走,走到的是学农基地。老师们叫做劳动,我叫做“劳动改造”,我也算是长大了,挖土是一把好手,我夹在老师当中一个劲地挖,边挖边听他们说笑话,甚至还听到那些带荤的笑话。我一直以为老师们是端庄无比的,听到那些笑话,我吃惊不小,老师也这样的?到了收工,老师们摘了茄子摘了豆角,当堂就分了,拿秤分,你几斤,我几斤。顿时,我对学农基地的美好情愫顷刻崩塌,我们的劳动原来是给老师做劳役?孔夫子教人学习,要人给束修,我没给老师束修,但我一把锄头在地里刨,是不是别一种束修?我当时真是那么想的,那种心理可以称得上半是天真?半是龌龊?这大概是介于长大了又未曾长大者的那心智吧。 而现在我想,不知道学农在那当口变味的,还是本来就是这个味,轮到我们学生这么来理解“学农”,不用其他什么“政策性因素”,学农基地这门功课肯定是开不下去了的。现在我再回到老家,回到当初的学农基地,都已被退耕还林,草长得很疯,灌木丛蓬蓬勃勃,树枝树桠直往上长,接天树叶无穷碧,总之,在那山坡上,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是荒芜,还是“茂盛”?几近又是“猛恶林子”了,那学农基地呢?好像是了无痕迹,不复存在了。
【 新浪财经吧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