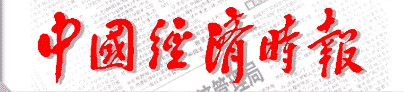|
不支持Flash
|
|
|
|
玄机与炫技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4日 09:39 中国经济时报
——读李洱的小说 ■张瑞燕 从1993年的《悲愤》、1995年的《缝隙》一直到2004年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坚持十几年精耕细作,构造出一个个丰富的“艺术谎言”。他的小说抓住了多元多变时代中人的生存实况,从知识分子到农民,写下了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中的各种生态,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共同遭遇时代激变。 李洱早期的小说一直关注人的日常生存,早年的李洱,写来写去,“都是日常生活的心灵悲剧”(梅特林克)。他自己也认为,“生存的困境,这可能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主题,是小说家思维交织的中心。作为具有一定长度的叙事作品,小说放弃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表现几乎等于找死。即便在最欢乐的作品里,生存困境也绕不过去,否则,它哪来的什么欢乐。” 套用一下诗人里尔克的两句诗“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似乎可以涵盖李洱小说中的众生相。或在背叛与猜忌中患得患失,或在现实和幻想中游弋而不能自拔,或将性爱与责任彻底分离,或“不知道什么叫生活,那活着还不是白活。”人处在既定的环境之中,无法选择和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论是位高权重者如《导师死了》中导师吴之刚,《加歇医生》中临终忏悔的加歇,还是学院知识分子费边、费定或孙良、华教授们,活着,谁都难逃命运的嘲弄和劫难。李洱早年小说,几乎将着力点都放在解读人的生存困境上。 存在主义的重要哲学命题“世界是荒谬的,令人恶心的”,世界中的个人,尤其知识分子,常对现实有陌生恶心感。存在主义常常用象征手法来处理其中重大的哲理、道德和政治问题。持存在主义观念的作家们常把人物放到特定的境遇中去,让环境来支配人物,不按传统的戏剧原则和手法来处理环境与人物的关系。李洱早年对加缪的喜爱与学习,使他对存在主义作品耳熟能详,他早年的作品中常常将人应有的崇高感使命感、责任感道德心消解完,将他们还原为肉身凡胎,让他们消磨在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男男女女蝇营狗苟无休止的生活旋涡里,让他们头顶的精神光环在俗世的烟火中渐渐褪尽。他乐于解剖这样一类灵魂给世人看,这样一群在急剧转型的社会生活中找不到方向,迅速被市场经济洪流掠到一边的曾经的理想者和知识精英,在他们眼里,语言已成为对抗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道屏障。 李洱由观察周边知识分子生活入手,到潜心于大量的古典文史资料,试图寻找突破点。《遗忘》的出现是令人惊讶的。可以说,《遗忘》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文本实验,李洱开始刻意进行一些文本实验,将大量的史料,神话传说和现实语境嫁接拼凑,《遗忘》几乎是一个新《故事新编》。这种依托大量文史资料研究的小说创作,史料与虚构互动的手法,在后来的《花腔》中又一次出现。在这部小说里,李洱试图梳理复杂的历史乱码,揭开纠缠已久的历史迷雾,小说叙述了革命知识分子葛任悲剧性的一生,反思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要重述这段革命史并不简单,李洱走进了纷繁复杂的历史迷宫,试图从尘封已久的文本、档案、史料,各种人物关系、语言、腔调混杂中拼凑出中国革命史中的一幅人物命运全景图,这又一次显示出学院知识分子的文本研读和操作功力。在他的笔下,历史变得疑窦丛生。 之后,李洱再一次转向,开始尝试农村叙事。李洱早年在《加歇医生》这部作品中曾展现过农村幻象,忏悔的加歇在弥留之际将一个来自农村的看护妇当作荒谬现实中惟一可以依靠的一个圣洁、光明的形象,将对她的依赖看作是一种精神上对纯洁家园的皈依。这显然不是真实的农村生活图景。李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小说既击中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弊病,又能及时发现要真正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充满矛盾的中国乡村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主题。 由描写知识分子、城市男女生活开始,进而进行神话和历史题材创作,终于,李洱触碰了乡村题材。提及转型,李洱曾表示其实写农村题材是为了成为更纯粹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如果只关注自己的生存状况那肯定不是知识分子。李洱试图反映农民在当代的现实生存状态,特别是他们的文化生存状态。《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一出乡村政治闹剧,他描写的是正在发生的“村民选举”,实际上却试图通过对当代乡村中国的描写反思千年积淀下来的民族性格。李洱笔下的现实乡村仿佛鲁迅笔下的旧乡村的重现,尽管今天物质生活上日益富裕,却依然充满种种凋弊的景象和陋习,精神的荒芜与简陋一如从前。 阅读李洱,乐趣不在获取一个离奇的故事情节,他的故事通常很日常,甚至很破碎,他大部分的小说,并不仅仅靠故事取胜,因此,读他的小说需要放慢速度,因他从不放弃一个细节,一句对白和叙述,任何一个打磨刷洗语言陈规陋习的机会。他擅用比喻,连篇累牍层出不穷的新鲜的比喻,常使人耳目一新。让业已陈旧的语言在流水似的叙事中焕发光彩,几乎是每一个现代汉语作者必要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洱的小说语言具有诗歌语言的特征和功效。他的小说无论篇幅长短,语言都一样干净、缜密、无可挑剔。在早期小说《悲愤》、《加歇医生》中,李洱的用语几乎是感伤的,彻骨的明媚,是诗意盎然的语言。李洱的小说,靠的不是宏大复杂的叙事方式或离奇古怪的故事构造,而是用深度叙事、细密叙事,来“密密缝补历史”。他的小说元素驳杂,但一直遵循着杂乱中的秩序,复杂中的精确。小说的玄机在这里,而炫技色彩则充分体现在《花腔》的语言特色上。《花腔》与以往小说不同,突破点在于他能沉着处理芜杂史料,轻松变换小说腔调;除此之外,小说秉承了李洱一贯的行文风格,无处不在的比喻、讽刺,缜密的行文逻辑,小说四处洋溢着语言更新的力量。 小说家李洱行踪不定,他的阅读和写作也常神出鬼没。李洱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调侃、讽喻和揶揄,将人生荒谬和悲哀凸现出来。而对人世的悲悯情怀又使他得以从日常琐屑的描摹中超拔出来,不至于沦落在细节絮叨中,在强调细节的同时,他的作品从未失去批判的力量。李洱显然不属于所谓后现代,他是一个典型的语言炼金术爱好者,讲究修辞术,他的小说量少质密,他巧妙地师承和超越了各种传统的技巧,他不允许粗砺的语言游戏,后现代式的市场意识和简陋庸俗的色情描写。后现代小说是反艺术和反严肃的,李洱则是最艺术和最严肃的,他始终是优雅和真诚的,信奉着小说艺术虚构的力量。
|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