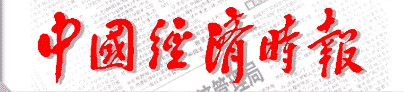|
不支持Flash
|
|
|
|
追忆一群赤子般的人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27日 08:56 中国经济时报
■慕毅飞 陈星教授是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他把自己写的“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一书,取名为《新月如水》,无疑寓意丰子恺师友之情如月皎洁,如水清纯。封面用丰子恺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漫画,切题应景,仿佛师友乍离,余茶尚温,留一脉真情供人回味。全书分“师生情怀”、“同门与同人”、“文友与艺友”和“附录:异国艺缘”四辑,笔触传神,叙述简朴,史料详实,细节化地再现了丰子恺和他二十八位师友的感人形象。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形容,似有几分轻慢,但随着李叔同、夏尊、马一浮、曹聚仁、章锡琛、郑振铎……相伴着丰子恺联袂而出,或行或吟,或喜或嗔……你会禁不住笑浮出一句戏评:真是一群孩子! 丰子恺喜欢为自己的居室取名,“缘缘堂”是丰子恺1926年请老师李叔同取的,后来成为他一系列散文的集名,足见他的珍爱。当时的李叔同已经皈依佛教,他让丰子恺在许多小纸片上分别写上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然后把每个小纸片都揉成纸团放在释迦牟尼的供桌上,由丰子恺抓阄。结果,丰子恺两次都抓了同一个字:“缘”。于是,就取其室名叫“缘缘堂”。 丰子恺说他若不遇到李叔同,就不会学画;若不遇到夏尊,就不会学文。可夏尊和李叔同一样,教会丰子恺的不仅是作文作画,更是如何做一个赤子般清纯的人。这个夏尊,原名“勉旃”,1912年,因不愿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怕在普选中当选,以读音相近改名为“尊”,有意让选举人填写“”时误写为“丐”而成废票。这又是何等的孩子气! 马一浮是丰子恺的挚友,被李叔同说成是“生而知之”的人。他游历美、英、德、日,第一个将《资本论》带进中国,却以研读佛学、理学终其一生。李叔同说,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读书,每天读厚厚的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一浮这个年龄,也不会读得如马一浮那么多。就是这样的马一浮,守孝期间,新婚妻子有了身孕,偷偷访药打胎,结果,新夫人因药中毒而死。从此马一浮埋首书海,作为一个国学大师,孑然一身,直至84岁死于“文革”的迫害。心之诚、才之奇、志之笃、情之专,浑然一天真未凿的赤子。 曹聚仁也是李叔同的学生,抗战期间,丰子恺一家路过曹家,曹聚仁以饭相待。随后,曹聚仁撰文,说丰子恺这样的佛门俗家弟子,也主张“慈悲”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的了……而丰子恺则以为曹聚仁曲解他的意思。在他看来,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这就是讲“慈悲”;宣扬“护生”,是为了下一代成长起来,不再成为杀生的侵略者。面对曹聚仁让他将《护生画集》烧掉的建议,他后悔自己吃了曹聚仁的一餐饭;惹得曹聚仁也怒而要求丰子恺道歉,否则,不再为友。一对朋友,就这样别如参商,形同赌气的孩子。 1948年,丰子恺应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之邀,携女和章锡琛一家同游台湾。在赴台的船上,章锡琛手表被偷,他说这手表是花75元港币买的。丰子恺说:那是一张船票的价钱,就如你家多一人来游吧。章锡琛却以生意人的精明答道:多一人还得买回去的船票呢!丰子恺说:那么,你再丢一支自来水笔就差不多了!惹得船上人哄堂大笑,两人调侃得如同一对顽童。 丰子恺终生嗜好绍兴老酒,在开明书店组建过一个“开明酒会”,入会的条件是一次能喝五斤老酒。上世纪二十年代,郑振铎在上海请他喝酒,喝完算账,郑振铎问他带钱了吗?丰子恺说有,掏出五元钱付了账。几天后,郑振铎来看丰子恺,拿出十元钱要还丰子恺,丰子恺不收,推让之间,边上的朋友抢过钞票说:不要客气,拿去喝酒吧!叫上夏尊、匡互生……大吃一顿,烂醉一场。这简直就是一群顽童! 最感人的孩子气,表现在丰子恺完成《护生画集》上。为宣扬不杀生的“护生”理念,丰子恺1929年出版了《护生画集》第一集,全集五十幅画,弘一法师配诗文,当时弘一法师五十岁。抗战时期,弘一法师六十岁,丰子恺创作了第二集,六十幅画,寄给弘一法师,请配诗文。弘一法师给丰子恺写信,要丰子恺在他七十岁时,作第三集,七十幅画;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八十幅画;九十岁时,作第五集,九十幅画;百岁时,作第六集,一百幅画,以求功德圆满。抗战还没结束,弘一法师就圆寂了。但丰子恺矢志不渝,在政治生活和艺术氛围极不正常的岁月里,仍然作画不已。“文革”期间,丰子恺遭受非人折磨,他预计自己活不到八十岁,就提前完成最后一集,拿到新加坡出版,完成老师所托。赤子赤心,可鉴可叹! 难怪弘一法师当年在虎跑断食时,给自己改名为“李婴”;也难怪丰子恺皈依佛教时,弘一法师为他取法名为“婴行”。尤其难怪马一浮为丰子恺的画集作序,道是“盖子恺目中之婴儿,乃真具大人相,而世所名大人,嵬琐忿矜,乃真失其本心者也”。再听听丰子恺的夫子自道吧!1943年,丰子恺的文章受到吉川、谷崎两个日本研究者的好评,夏尊把这两个日本人的评论译介到中国,叶圣陶索要了夏尊的译稿,发表在自己编的刊物上。丰子恺说:“我既然承认自己是孩子,同时又觉得吉川、谷崎二君也有点孩子气。连翻译者的夏先生,索稿子的叶先生,恐也不免有点孩子气。不然,何以注目我那些孩子气的文章呢?”只是丰子恺因此慨叹:“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令人怃然。 道学的最高境界,叫“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佛学五行中,也有婴儿行,在马一浮看来,是比老子所言更高的境界。所谓赤子,就是天真未凿的孩子;浑沌凿了七窍,也就一命呜呼了。成熟,增加的就是机心、圆滑与世故。人心不古之叹,可见之于孩子的越来越早熟。看看电视镜头前的孩子,一套一套的成人术语,就知道清纯世界在如何塌溃与冰释。读陈星的《新月如水》,不禁追忆一群赤子般的人!丰子恺三十年前就走了,是带着天天批斗炼出来的游戏心理,带着便于一喊就走养成和衣而睡的生活习惯,带着乡人依然把他看作“大客人”的满足,参拜给过他“爸爸的教育”的弘一法师和给过他“妈妈的教育”的夏尊老师去了……走了丰子恺这一个孩子,走了丰子恺师友这一群孩子,中国的孩子是越来越少了…… (《新月如水》 陈星 著 中华书局 2006年9月第1版 定价:20.00元)
|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