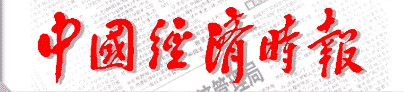|
不支持Flash
|
|
|
|
书缘与人缘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20日 09:46 中国经济时报
■高为 “红尘呀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总有时。”这说的是缘分,人与人的缘分如此,人与书的缘分也一样。 第一次大批卖书是在大学毕业后。刚回到家乡,马上就恢复了逛旧书店淘书的爱好。我把课本、课外读物、部分外语词典以及从前有兴趣现在无感觉的书如《九三年》等卖给了旧书店,再从那里买我喜欢的古籍、新著,如《管锥编》、《柳如是别传》、《莎氏乐府本事》(英文)等。郁达夫有诗句云:“卖得文章为买书”,我是“卖了旧书买新编”。小时候母亲就时常说我“五马换六羊”,大概的意思就是每次交易都会吃亏。俗话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也有例外。比如我们卖废品时,或把东西当作废品出售时,吃亏的总是我们自己。比如不论是洗衣机还是电冰箱或电视,收废品的或商场收购时一律只给你100—150元,不管它们能不能继续使用,也不管它们买时是多少钱。再比如我们把书卖给旧书店,遭受损失的还总是我们自己。 1995年换了工作,原单位收回了住房,十几年的青春虚掷,生活愈加狼狈。1999年家里人及亲戚赞助买了房子,钱更紧张了。我又打起了书的主意。卖给旧书店觉得太亏,于是就加入了每周六、日在市图书馆院里的卖书队伍,赤膊上阵去练摊了。在那里认识了《今晚报》社的记者王振良,把《清稗类钞》(十三册)、《古史辨》(共七卷九册)卖给了他,而且,我一高兴,还白送了他一本顾颉刚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十二本的《说郛》、散本的《笔记小说大观》(其中有《太平广记》、《容斋随笔》、《夷坚志》等)、两大巨册《经籍纂诂》(中华书局版)和两本32开的《经籍纂诂》(浙江古籍版)、杨树达的两大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训诂论文集先后也都卖了。因为我有中国书店版三卷本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和上海古籍社两卷本的铸雪斋抄本白文《聊斋志异》(此两卷本比那三卷本篇目还多),所以就把上海古籍社四卷的会校会注会评本也卖了。虽然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等大部头没有卖出去,前后也卖了两千多元,加上搬家前论斤卖的三十多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真正是损失惨重,至今仍令我心痛。 搬家后情况相对地好了一些,我的心里又蠢蠢欲动,为自己的短视行为而后悔——后悔搬家时没有定做顶天立地一面墙的书架;后悔卖了那么多的好书,那可全是自己日积月累的结果呀,整个一个二十年心血唐捐。我写下了“半生窘困,一世读书”的字样,又开始逛旧书店(市图书馆院里的书市取消了),把卖出去的书往回买。三会本的《聊斋志异》买回来了,可是不如我卖的那套新;《清稗类钞》也踅到了,品相差不说,还缺了第十一、十二册。钱钟书频频征引的《说郛》、顾颉刚一举成名的《古史辨》,却再难觅踪迹。似乎由于今是昨非的认识,或者说出于新我对旧我的一种补偿心理或惩罚情绪,再购书时就更加热情尽兴——《追忆逝水年华》(七卷本)、《莎士比亚全集》(英文)、海德格尔的两卷本《尼采》、塔西佗《编年史》……统统买回家了。 我把自己多年来读书、买书、卖书、编书、评书的生活和工作一篇篇写了出来,去年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随笔集《徘徊在门外的感觉》——在读书、编书方面,自己始终是个新手、门外汉。承蒙北京的《书摘》杂志抬举,他们于去年的第九期和今年第二期分别选登了书中的《两种自由》和《说“悔”》两篇。 《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爱书的我对待书的态度,是否像某些贪得无餍的官僚对待金钱一样,只是在满足占有欲,而并不看重其实用价值?有时我想:现有的藏书我一辈子都读不完,为什么“坐拥书城意未足”,还要不断购书呢?买到什么时候为止?我的孩子如果不从事我的工作,以后会如何处置这些书?沪上“补白大王”的藏书,在其身后被子孙送进了旧书店。这也挺好。书又回归社会,服务人类了。巴金捐给北京某机关的藏书,媒体曾报道有一部分已流落到潘家园旧书摊。与其绕一个弯,还不如直接送进旧书店。津门藏书家周叔弢,一边把大量的珍本、善本、孤本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一边在耄耋之年还逛书店、买新书。天津市图书馆前馆长黄钰生先生,七老八十了还去逛天津市第一届读者交换大会,并从我手里买走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周老、黄老都是真正懂书、爱书的人,懂得如何使书发挥最大的功效。生命不息,买书、读书不止。“身后是非谁管得”,藏书就由它去吧。 今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中新置地、今晚传媒集团、百花文艺出版社三家联合举办“大户人家丛书”启动暨研讨会,凑巧的是,我又见到了《今晚报》社的王振良,这次不是作为买主和卖主,而是作为作者和编辑的见面,也可以说还是买主和卖主的会合,只不过位置颠倒了,他成了卖主,我成了买主。他要写的“大户”是山西乔家大院的乔致庸。中午聊天时,我对他提起我卖出去的书有几种又买了回来,可有几种再也见不到了。王振良说他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三四种书卖出去又加价买了回来。我们达成了共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卖书。自己要想找本书或借本书太不方便了。市图书馆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书都成了“珍本”,不外借。有自己需要的书还不如自己买一本用着顺手。 在7月28日的研讨会上,我还见到了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馆长虞浩旭先生。他要写的“大户”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著名藏书家范钦。为范钦立传,没有比虞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说起天一阁,读过几本书的人哪个不知?提到范钦,当代读者不能不想起余秋雨的那篇《风雨天一阁》,想起为了读书而嫁入范家却终生被禁止登上藏书楼郁郁而终的钱绣艺;想起潜入天一阁偷走了大量藏书的薛继渭;想起先藏于天一阁、后藏于涵芬楼、最终全部毁于日本侵略者炸弹的大批古籍…… 范钦的政绩已经没几个人记得了,但他创建天一阁的功绩将与世长存,永远被后人铭记。范钦生活的时期并不是“盛世”,这就愈发显得他的所作所为难能可贵,非他人所可企及。在几千年“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否真正存在过盛世,我一直很怀疑。所谓的“康乾盛世”,到底是谁的盛世?是康熙、乾隆的盛世,还是广大知识分子、文人的盛世?如果是后者的盛世,那如何解释株连九族的文字狱、刨坟戮尸的秋后算账?盛世的国泰民安、君臣和谐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 天一阁重藏轻用的规矩使天一阁的藏书流传了几百年,但其重视藏书的价值而忽视使用价值,重视藏书的文物价值而忽视文献价值或文本价值的传统挡住了绝大多数读书人。“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余秋雨)那说的是过去的事情。无论如何,“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阮元)什么时候,我们也有缘到浙江游宁波去天一阁朝拜呢?
|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