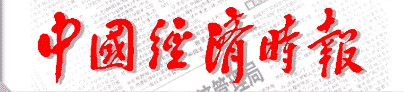|
不支持Flash
|
|
|
|
古月依然照今人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6日 09:19 中国经济时报
■安立志 唐代诗人李白的《把酒问月》是千古名篇,其中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不仅有着回环、互文之美,且有重复、对比之妙。说“今人不见古时月”,即意味着“古人不见今时月”;说“今月曾经照古人”,也意味着“古月依然照今人”。今月、古月实为一月,而古人、今人却非一人。古人、今人何止恒河沙数,然而他们见到的明月则亘古如斯。 此番议论,是我读了田东江先生的“报人读史札记”——《意外或偶然》之后,所产生的一点感慨。 我与东江先生素昧平生,从未谋面,但他作为编者,我作为作者,在《南方日报》的评论版上曾经有过一段文字之缘。正是因为这段文字缘,使我从他寄来的样报上,断断续续读到了他的几篇读史札记。由于他署的是笔名,开始并不知道这些札记的作者就是编辑本人。 今年6月,收到东江先生这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意外或偶然》。由于工作性质基本属于事务“行走”的缘故,加之尊臀有恙(医生称之为“梨状肌综合症”)不敢久坐,因此,用了较长时间,才将这本书读完。虽然书读的不甚连贯,仍然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精神世界的深刻和忧郁,也从书中读出了作者及其作品所体现出的情感的深挚、史料的厚重、文风的淡然。 研究历史往往为了现在。东江先生这本书的“上编”,其写作特点,基本采取了从史料入手,直接阐述史实的方式,即所谓历史随笔;而在“下编”,则往往以某一时闻作引子,然后,从史籍中寻找支持自身观点的论据,用鄢烈山先生《序》中的评价,即所谓“露出了时评的本相”。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以古喻今,借古讽(古代之“讽”,并非讽刺之义)今的良苦用心。月光悠悠,亘古如斯,人类的功过是非,都在月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太宗李世民有了这样一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倘若将这句话倒过来说,“欲知兴替,当以古为镜”,而这不正是许多明智的政治家常常提倡多了解点历史的初衷,不正是包括东江先生在内的所有希望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当代社会疾患治疗之方的忧患之心么! 一曰情感的深挚。这本书的“上编”,所有篇目几乎都以官场作为议论对象,文章标题中含有“官”“吏”二字的所在多多;而“下编”以新闻事实为由头,涉及世风、文风等诸多方面,但其中,关于政风的内容仍然不在少数。从客观上说,中国古代留存的史书,大部分属于宫廷史或政争史,以为皇朝统治提供史鉴为宗旨的史书,更是离不开这类素材。从主观上讲,东江先生作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秉持着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优秀传统,因此他的笔触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国家、民族、社会这类政治层面的东西。有意思的是,东江先生在每一篇的结尾处,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议论,这些议论当然针对的是文章中涉及到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然而,他的议论却是低回深沉,饱蘸情愫的,有的伤感,有的激愤,有所劝喻,有所期待。而这一切,决不是东江先生“看三国落泪,为古人担忧”,也不是酷爱历史的东江先生“发思古之幽情”,其所体现出的正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沉重的历史宿命和庄严的时代责任。 二曰史料的厚重。与东江先生电话交谈,得知他十多年来广泛涉猎,饱读史书,读遍了“三色书”,即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绿皮书”)、《资治通鉴》(“黄皮书”)以及《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白皮书”),而且他在文章中涉及的野史笔记也极其丰富。对我来说,《朝野佥载》、《池北偶谈》、《齐东野语》有的读过,有的听说过,至于《水东日记》、《巢林笔谈》、《不下带编》等等就闻所未闻了。作为历史笔记,就其写作风格而言,也见其厚重的史学素养。绝大多数篇目,倘论述某一主题,其所征引的史料,往往纵贯多个朝代,涉及多种史书,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由此想到,在当下急功近利、世风浮躁的现实生活中,倘若没有一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不可能读完这卷帙浩繁的古籍;没有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不可能如此娴熟地掌握和运用这些尘封已久的史料。这里提到的“三色书”等史书,作为记载中国古代历史的典籍,显然有着时代的、价值的、阶级的局限,其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其中蕴涵着漫长的、曾经真实存在的历史。从陈腐中发现神奇,从专制中筛选新意,必须充分占有资料。“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老话,但在任何领域从事研究工作,没有对该领域的知识、素材的丰富占有和透彻了解,要想取得研究成果是不容易的,何况“读史”?“读史可以明志”,而这正是东江先生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历史感、沧桑感的原因之一。 三曰文风的淡然。东江先生在对史料的运用上,用他本人的话说,“文章中的双引号极多”,“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标识征引的为原文,其神韵译过来的话要打折扣;另一方面,广东的明代理学家陈献章(白沙)说过:‘夫学贵自得,苟自得之,则古人之言,我之言也’”。对于东江先生的看法和做法,我也确有同感,在运用史料说明问题时,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不使用“硬译”或“软译”过的东西,以免伤害、歪曲原文的典雅和文意。这是其一。其二,东江先生的作品,无论你把它称为历史随笔,还是杂文时评,他所拟出的文章标题,既没有某些杂文的金刚怒目,也没有某些时评的故作学术,比如,上编的《“青词宰相”》、《“能说话者”》、《“何用碑为?”》,下编的《意外与偶然》、《象牙笔》、《前苏联·故明》等等等等,大多中性、平实,极其简明、淡然。不是因为在此问题上我与东江先生有着相同的追求,从而作出偏爱性的评价,正是这种淡定中渗透着稳重,平实处体现着深刻,从而与时下某些刻意追求“眼球效应”的种种文化现象,形成了巨大的素养与境界的反差。 古籍,当然不是古月,但却有着月光的功能。古老的银辉洒向人间,山川大地已物是人非,一些古今人士的咏史之作,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看到的不正是古月辉照下的景物么?元代济南籍官员张养浩曾有《山坡羊》一组:关于郦山的——“郦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关于潼关的——“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关于北邙山的——“碑铭残缺应难认。知他是汉朝君,晋朝臣?”古籍之于今人,是因袭的负担,还是前进的镜鉴?有的人热衷于复制古籍中的木牛流马,有的人孜孜于开发古籍中的宫廷膳食,有的人陶醉于古籍中的雄汉盛唐,有的人执迷于古籍中的“相斫之术”。更有甚者,有人将密布着蛛网、散发着霉味的玩艺——所谓“国学”,当作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拯救这个堕落星球的中华文明的“瑰宝”。而东江先生所作的则是从历史的教训中探讨社会痼疾的源头,从古老的经验中寻找当代文明的起点。这样的工作自然比不上所谓弘扬“国学”的殿堂宏宇、堂皇冠冕,然而,这却是每一个具有历史感的知识分子所应当尽力为之的时代责任。 断断续续读完全书,竟然生出某种莫名的伤感。东江先生青灯黄卷、伏案握笔,从正史中、从野史中,寻找“政疾”的良药,探讨时弊的病因,然而,又有多少贪官庸吏,热衷于声色犬马、得计于蝇营狗苟,又有谁寻求什么历史教益、又有谁吸取什么历史教训呢?东江先生有一篇名为《只恐有人还笑君》,这样的口吻,历史上本不乏其例,甚至涉及的问题还要大得多。比如,贞观名臣马周就曾对李世民说过:“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贞观政要·奢纵》)晚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也曾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就是关于历史周期律的那篇著名的“窑洞对”,不是也曾给予人们来自历史深处许多的叹惋与唏嘘么? 东江先生在《南方日报》主持时评版的编辑工作,因此,在他的文章中多少也出现了一些时评的痕迹,如本书“下编”中的一些文章。说实话,我更喜欢本书“上编”中的文字。东江先生具有深厚的史学素养,他决不会满足于在月光下寻找古老的痕迹,应当可以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形成“原创性”的成果。 (《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 田东江著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3月第一版)
|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