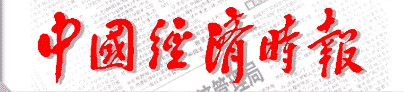|
|
|
|
|
我们离宽容到底还有多远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30日 08:48 中国经济时报
■慕毅飞 看完《精神历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仿佛听完36位当代中国学人的心灵倾诉。36条精神轨迹,交错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一幅精神地貌图。我想起林贤治《午夜的幽光》里的几句话: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精神有如阳光,恒在地悬浮于大地和云层之上。它超越于自然,不是无机的;它超越于生物,不是有机的;也还超越自身,不是可以束缚的。从这个角度说,知识分子的精神性就是无所依附的独立性。诸如何怀宏、徐友渔、李银河、葛剑雄……术业有专攻,秉持有专域,异样的精神历程,造就的却相同的精神品性。他们棱角鲜明,并不世故,各持一调,自成一说。叙述者款款而谈,倾听者心有所动。也许“精神历程”,触及了他们共同敏感的心弦,话头掷地有声,语锋鞭辟入里,全无应景之作的客套与敷衍。 “我们离宽容,到底还有多远”,这是邵建在《“走近”胡适先生》一文中让人不能不动容的一问。翻阅36人的“精神历程”,无一例外是沉郁的底色、沉重的语调和沉闷的情感。这固然是知识分子的天性与天职使然。谁都应该是社会肌体的一根神经,但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神经,注定是用来感受痛苦的。此外呢?还因为这一代学人的精神发育,无一例外处在最苍白、最怪诞、最荒凉的时代;整个成长过程,充满着病态的亢奋与变态的激昂;最多的是屈辱,最少的是尊严;尤其是与学术、学问、学人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几乎所有的精神痕迹,都是伤痕、裂痕和疤痕;而一切发生在精神领域的伤害,几乎无一例外地源自于宽容的缺失。对历时的传统,以反封建的名义,进行过最彻底的决裂;对共时的世界,以反帝反修的名义,进行过最广泛的批判;最后,对可怜的自己,也以斗私批修的名义,进行了最无情的自虐——必要的斗争,却没给同样必要“宽容”留下方寸之地。 于是,难怪徐友渔在他的“若干记忆片断”中,提及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没有脱帽的,除了江青,还有朱德,但人们只给了毫无“宽容”之心的江青以“不宽容”的诅咒;也难怪每万人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中国只有2.1个,但杨东平能在“宽容”的语境中,讨论非政府组织对于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终于让人获知这世界变了;尤其是蒋高明能以环保专家的身份,屡屡“向权力诉说真理”,先是因保住几颗古松差一点被轰出避暑山庄,再是为否定造林治沙成了内蒙古林业厅不受欢迎的人,最后为叫停怒江水电在网上遭遇群攻……这一次次不被“宽容”里,却有着整体的“宽容”在。 要知道,在“造神”的岁月里,“宽容”是人向神出让的权利,诚如徐贲所言,“人一站起来,神就颓然”;在功利的社会里,“宽容”是气度的衡器,诚如蔡定剑所感叹的,一个基层民主实践者的不为人所容,竟然是因为他干得极为卖力而且极为成功;在崇尚一统、迷恋一律的国度里,“宽容”是历史进步的标尺,诚如周永生所质疑的,像什刹海、玉渊潭这样的地方,怎么就容不得市民游泳?有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做的,为什么总是剥夺百姓少得可怜的那点自由?另一方面,作为“不宽容”的回应,连鄢烈山提倡对社会负责的公民写作,都招致“骨酥膝软”的指责而成为挥之不去的心头一痛。更不用说,在坚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人眼里,像楚树龙这样研究美国,常常把真实的美国说得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可怜与可憎的学者,就成了为人侧目的“亲美派”。至于要清算“不宽容”的专制,可以从丁东“打捞”顾准、遇罗克、孙越生这些“民间思想”的艰难曲折中,想象得到它的不易。但丁东毕竟“打捞”成功了,似乎又标志着世界毕竟是走向“宽容”的。 回到邵建的《“走近”胡适先生》,那场一百年前发生在胡适与陈独秀、鲁迅之间的分歧,看起来只是倡导白话文的同时,给不给文言留恋者以申辩权利的意见之争,其实,显露的是“宽容”与“不宽容”的分野。越“不宽容”越革命,越“宽容”越反动,由此成了近百年中国政治的基本生态。结果,学术的繁荣没了,人文的关怀没了,亲民的善政没了,连留什么发形、穿什么衣服的自由也没了……精神,就在这样逼仄的险道上失去了它的家园。长平喋喋不休念叨的是昆德拉的小说《无知》:两个逃离祖国的捷克人,回来梦牵魂绕的故乡,结果,时间扭曲的记忆,再也找不到一丝的归属感。于是,所有的叙述都聚集到这样一个起点:全球化的现实与大同世界的历史,能不能让所有新的精神历程,能从“宽容”出发。 (《精神历程》 曹保印 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定价:36.00元)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