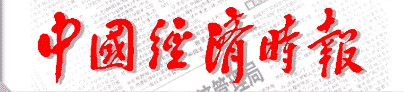|
|
|
|
|
青苗法的另类时空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30日 08:48 中国经济时报
■伍立杨 王安石当年搞青苗法,随之备见梗阻,最后面目全非,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但九百多年后的诺奖获得者尤努斯,他从基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其行之之法,和王氏用心同出一辙,却大见成功。天意欤,人意欤? 宋时集权盛旺,冗官冗费膨胀,国家财政负担增加,欧阳修文集卷五十九说是“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也痛心疾首之言,当彼之时,制度日益丛杂,王安石当然要想办法。他是在神宗任上得遂其政的。神宗当时欲克服燕云,恢复先主之业。这些都要先充实府库,而欲财政之丰,提倡生产,乃是根本。 青苗法是新政六种之一项。让农民估计将来粮食余数之量,由官家贷款,谷物收成后还。先已局部实施过,后推向全国。 民国经济学家朱伯康论说这一段史实,他说:“资本由常平仓、广惠仓之钱谷充之。放款期分夏、秋二季……归款时期,在收成之际,若遇荒则展至下期,手续则由人民自由申请为原则。利率以领取时规定之斗斛为度,若改还钱,取息十分,不得过三十分。在乡村之放款全为信用放款,十户为一保,即可请领;在坊郭,则五家以上为一保,须以自己物业为抵押。此法行之十六年,流弊丛生。韩琦、范镇、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皆反对之”(《中国经济史纲》商务印书馆1946年初版)。 其噎塞不通之患,大要在于,下层人员执行不善,例如提举官(管理员),以多散为功,不问贫富,均摊配之;贫者到手用去,无力缴还,吏督之急,则逃散四方。还有散给之时,为多给,又请客设倡,不会来事的甚至只有自杀,地方豪强则于此时贱买田宅,大搞兼并;他们转手之后,贷款已无异于可怕之高利贷,而这一切在相当于立法的背景下强制推行,为富不仁者,更藉王氏之名而行凌虐掳掠之实,积弊已深,高人束手…… 但是千年以后的另一个地方的实践者几如依葫芦画瓢,却大为成功。 2006诺贝尔和平奖,奖给孟加拉人、经济学教授尤努斯,他在30年前创办Grameen(格拉明)银行,向那些有需求者提供小额贷款。尤努斯的理念转为实施,令几百万人受其惠,除了孟加拉人,还有其他国家的百姓。诺奖委员会指出:“只有当大批人口找到消除贫困的途径,才能取得永久的和平。” 小额信贷在上世纪70年代发端于孟加拉国,它是满足穷人信贷需求的一种信贷方式,贷款对象仅限于穷人,额度很小,无需抵押。Grameen意思就是“小型乡村”,其模式是一种非政府组织从事小额信贷的模式。“格拉明”以小组为基础的农户组织,要求同一社区内社会经济地位相近的贫困者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贷款小组,相互帮助选择项目,相互监督项目实施,相互承担还贷责任。 王安石,梁启超说他是伟大的金融家,超前的金融意识,说他的惠民之政,相当于现代的劝业银行,甚至说“夫中国人知金融机关为国民经济之命脉者,自古迄今,荆公一人而已”(梁著王传第十章),这就未免抬举过分了。现代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必以民治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前提,信用、规则、法治、责任,在在有所依循……贯穿不可或缺的相关背景相关环节。 而王安石的时代,全无此种社会氛围。他的“官方语言”,等于没有合适的“翻译”渠道,又拿什么来保证它的适切畅通呢。行政系统行政机制成为遏止青苗法的瓶颈,好心而又霸王硬上弓,结果太半是面目全非。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不如苏轼、司马光等的“保守主义”来得适切。改革看你是否以人为本,是否改在结点上。而非只要有理想的运作或好心的改动就是好东西。王安石年谱记载其当新法实施之际,颇自负,以为“我宰天下有余”,实已以昏聩为聪明。荆公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芸芸众生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牛皮啥呀? 当时农民在组织上一盘散沙,其得贷款,将与打酒喝,买副食等等,和今之偏远区的农民一样,可见王氏的光输血而无造血功能的改革,毕竟会功亏一篑。再说利息那么高、中间的暧昧环节那么多,王安石这项工程,既非输血,更非造血,事实上简直是抽血了。在社会保障系统一无依循、生活资料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偏远区农民将贷款率先用之,最后所能归还的只是排泄物而已——再生产无从谈起,本金又归诸乌有,若追索迫近,则只有弃家而走,造成新的不安和隐患。 朋友,须知在一个没有权益保障的社会空间,今朝有酒今朝醉,乃是普遍的社会心理。人民怨憎污吏,掌权者同样心存异志,权力物化,寻租放任乃是其必取之途。皇权制下,看似因权力集束而高能高效,但这只是对朝廷的需求而言;至于下层极宽泛的社会,因其反人性反规律一言堂暗箱操作等等特性,反而产生循环迭起的离心力。安石的固执武断,每好以偏概全,最后竟将错就错了,事情当然就变本加厉,更加旁逸斜出了,全盘的纠葛,王荆公恐怕始料未及罢。 林语堂《苏东坡传》写这一时期的朝廷运作:“……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法。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要力行自愿,并无实际用处,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 结果是凭想象办事的大吏固执己见,中下层人员各有怀抱,都暗中向各自期许的方向用力,而社会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形成撕扯,坏账烂账,尽要百姓买单,强凌弱、众暴寡,颟顸腐化,遗患无穷,整个就是苏东坡所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 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固然是动听的。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现代经济学范畴。黄仁宇先生以为,很可惊异的是,王安石当时就已经懂得: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他的经济思想远较司马光高明,但黄先生也说,这恰恰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因为就实质而言,他的高明,并非什么思想,只是一种念头而已。 王氏、尤氏的出发点都迫于当时和当下的实情的需要,但一个铩羽而归,一个却得以登堂入室。王安石先前也是基层小吏,那时他搞贷款就较为完满,为什么呢,空间的相量允许他施展腾挪,但那是一个特例。到了宰制全国的时候,上下游离、行政的弊端就非其力所能羁控。指令经济、想当然经济自然就“骏马下注千丈坡”,难以收拾了。尤努斯则可以说是另一个时空的王安石,尤努斯“平稳过渡”的背景也在行政不干预,至少不成其为障碍,故使其可依日常经验、规律及实际情况从容操作。他们的路数很相似,性质却很不同。 尤氏的具体保障也渗透在细节上,他在小组基础上建立中心,作为贷款交易和技术培训的场所;无抵押的、短期的小额信贷,但要求农户分期还款,定期参加中心活动。对于遵守银行纪律、在项目成功基础上按时还款的农户,实行连续放款政策。经营机构本身实行商业化管理,特别是以工作量核定为中心的成本核算。简而言之,是清明吏治作保证和必要的专业人才相配合。从性质而言,他的贷款理念和高利贷竟是相反的,渐渐地,他的“乡村银行已不须担保,还款率高达98.85%,农民的合作性和接近商业的能力大大增加,透过小额贷款,农村彼此合作免遭剥削,并创造出自产自销的小商业模式”(参考消息,2006-10-25)。他的每一个步骤都卡位卡得很紧,像齿轮的咬合,而其施之于无数个体的优惠,因这卡位形成良性循环,造成社会经济的整体提升,在此,制约机制良善无弊,它施之于相当区域的穷人,大家在制约中获得自由,机会均等,权利平等。此所谓形势比人强。 从他1974年第一次借出27美元给农民开始,到现在他已建立了一千多个信用社,为贫困村民提供了几十亿美元贷款。梁启超加诸安石头上的惠民金融家的头衔和光环,要改移到尤努斯头上才算合适。 几十年来,小额信贷为穷人所深喜,在亚非拉美诸发展中国家,衍为固若金汤的扶贫方式。梁启超的所谓惠民之政,若是用在尤氏身上,那就非常贴切了。同样是好心肠,一个是古代的玄之又玄,一个是现代的行之有效。结点其实就在政经体制的适切与否。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