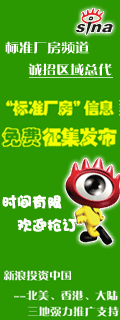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虽然原定于4月23日举行的北京出租车价格听证会改在了26日举行,却丝毫没有降低这场涨价风波引起各方争论的热烈程度。
其实,在今日听证会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围绕涨价的辩论已经开始,三大焦点问题已然浮出水面,各种建议也纷至沓来。有建议指出,应在租价油价联动关系中建立起出租车公司、政府、司机、乘客四方合理均衡的分摊机制,并明确政府在该行业中的位置和权责
。
焦点一:该“减份儿钱”还是该“涨价”?
面对油价上涨,国内诸多城市纷纷通过上调运价化解出租车行业高油价压力,然而,油价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向消费终端传递。出租车司机和消费者也纷纷发出质疑:出租车公司的高额“份儿钱”雷打不动,油价上涨压力却要由消费者主要消化,这是否合理呢?
“其实公司完全可以下调份儿钱的。”北京首汽集团一位司机说,司机的承租金降了,其它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若夏利、富康两种车每月都降低1500元“份儿钱”,则司机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就可收入1500元,而现在出租车司机几乎每天工作11小时左右。
这种质疑不只是一城一地的声音。在沈阳,出租车司机们也建议政府对出租车公司凭借垄断地位,单方面定价的现状予以改变,制定政策,规范出租车公司的收费行为。而深圳市率先降低出租车公司租金的做法,无疑向全国其它城市表明,出租车公司减租完全可行。据悉,为减轻油价上涨带来的出租车司机负担增加,深圳市政府要求从4月1日起,各出租车公司下调出租车月缴定额(月租),每月每车减少315元。这已经是深圳第二次以降低月租来冲抵油价上涨给司机带来的负担了。
但从4月18日北京市公布召开出租车租价上涨听证会至今,接受记者采访的几家出租汽车公司没有一家表示愿意降低“份儿钱”的。
焦点二:出租车公司是不是“暴利”经营?
一位出租车公司管理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租车行业利润不高,虽然租价上涨后将取消燃油补贴,但仍然要花更多钱在车辆年检和给司机上社会保险费用上。
但经济学家郭玉闪指出,在2003年度每公里1.2元的运营成本表中,首汽公司有1748030元的“工作餐费”,而2004年度银建公司共有6093136.94元的“福利费”。如此巨大的数字让人震惊。以一辆伊兰特为例,假定出租汽车公司完全通过银行借贷来融资,其它条件也按上表运作,那么,9万元投资一辆新车,8年之间(新车报废年限)会产生13.1万元的净现值,而其内部报酬率为49%。
一份长达42页的由北京嘉信达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关于北京市出租车租价体系六家总汇评审报告”,对首汽、银建、京朝、凤凰、天安、昌华德六家出租车公司成本利润等状况进行了评审,尚未对外公布。郭玉闪说:“我看到,银建公司党委书记的月工资为21544元,这一点就能说明北京市的出租车还没有到上涨租价的时候。”他进一步解释说,决定价格的应该有直接运营成本、组织成本、企业家贡献、制度费用4个因素,其中“企业家贡献”一项在出租车行业指的是司机个人的经营才能,而不应该是出租车公司的管理者。
焦点三:出租车垄断经营该不该结束?
相关管理部门此前认为,全北京有出租车数万辆,如果取消出租汽车公司而改为个体经营,管理这些车辆将耗费更多行政成本。但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对此表示,出租车行业本来可以个体经营,北京市现有的个体经营户没有每月几千元的份儿钱,都是依法自主经营车辆,税后收入颇丰。目前北京的出租车公司在政府特许之下的垄断经营,反而叫苦叫难,不断要求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去保证企业的暴利,“这种行政特许经营的方式早就应该结束了。”
“为什么不考虑租价与车价联动机制呢?”专家表示,北京市出租车行业最根本的问题是垄断,解决这个行业的问题,政府必须坚决抛开这些利益集团来做决策。
专家建议建立租价分摊机制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研究部副主任、经济学博士胡迟认为,应当在租价油价联动关系中建立起出租车公司、政府、司机、乘客四方合理均衡的分摊机制,由出租车公司、政府、司机、乘客共同承担上涨的成本,前两者应该负责大部分,其中公司负担比例又应当超过政府部分,比如说按照5∶3∶1∶1,或是4∶3∶1.5∶1.5的比例分摊。
胡迟表示,之所以是由于公司的高利润并非来自市场竞争,而是来自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即行政管制之下的垄断租金。
政府之手应在何处
在谈到为何北京出租车行业不能引入多元化竞争,并鼓励个体化经营问题时,有出租车公司管理人员表示,北京作为首都,社会稳定是大问题,而且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经常要承担一些全国性的会议和活动,例如每年举行的“两会”等。这些重大会议的用车、公益性用车都是免费的,只有公司才能承担起这项任务,个体经营无法负担。
有专家认为,作为出租车承担一部分政治和社会任务,这是必然的。但是,相对于日常的社会需求来说,这部分政治和社会任务的负担并不算重。政府部门在出租车行业中扮演的角色,更多的应该是监管和门槛控制,把政府之手放在行业之外。如果我们跳出行业看问题,会清晰地发现,本来可以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采购来解决的简单问题,变成了一个需要政府直接调控利益各方的复杂问题。政府某些部门如果能换个角度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会更好。
本报记者 文婧 勾晓峰 实习生 梁佳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