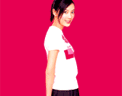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房煜 北京报道
有着四分之三法国血统的华新民,从1998年起就为保护北京胡同而奔走、疾呼。但是不久前,她却失去了自己出生时所在的那条胡同。2005年,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红星胡同(原名无量大人胡同)被拆除,这里有她的祖宅。
华新民的父亲——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儿童医院的设计者华揽洪先生一纸诉状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告上了法庭。93岁的华揽洪无法亲自诉讼,华新民就成了父亲的诉讼代理人。
该案于2006年1月5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因是涉外案件,法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兼领事尚多礼参加了旁听。
“这不是一个私事。”华新民说,“当我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受到陌生人的侮辱与威胁时,这就不再是我自家的事。”
在华新民保护北京胡同的“八年抗战”中,她首先关注的是胡同的文化内涵,她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个代表老北京的文化符号。但是,随着一个个胡同被拆除,随着一个个胡同家庭被强行赶出属于自己的家,她已逐渐认识到,与消灭文化符号同时进行的,还有对公民财产的公然掠夺。
如今,这两种劫数,同时落到了她的头上。
“他们能把猫变成狗”
让华新民的祖宅消失的,是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东城分局于2000年和2005年先后两次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0规地字0157号和规(东)地字0001号。这两个许可证,均颁给房地产开发商用于金宝街工程建设。所谓金宝街工程,就是要在此地建设高档写字楼、商务酒店、高档住宅公寓以及容纳高档会所的酒店。第一个许可证在颁发两年后已经失效,但是在第二个许可证颁发前,华新民家的私宅已经被拆掉了。
按照国土资源部9号令(2001年10月22日发布)的“划拨用地目录”之规定,被划拨出让的土地,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即用于国家机关用地或军事用地,或者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非营利性公用事业用地,或者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用地。金宝街工程显然不属此列。
在法庭上,华新民陈述了这一案件中的种种疑点——在自己和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家的私宅为什么轻易被划拨出去?这是否侵犯了她与她的家人的私人财产权?
同时,整个金宝街工程项目涉及胡同众多,在这些胡同里,有蔡元培故居和鳌拜府所在地。在法院开庭审理之时,蔡元培故居已被拆毁。
华新民家的私宅,分别位于遂安伯胡同27号以及红星胡同53号和55号。其中红星胡同家的院子,曾是早期中法建筑师沙龙所在地,如今一并拆毁。
华家的私产是如何被轻易划拨出去的?
早在2004年,华新民就撰文分析过这类情况:任何经营性项目在立项之前,都要先进行土地财产权的转移,而不是在立项之后。但是,现在很多开发项目的“立项”,在程序上是颠倒的。所谓土地财产权,是指国有土地使用权。1990年国土局曾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厅发出关于城市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等问题的复函(注:【1990】国土法规字第13号),其中指出:“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后,公民对原属自己的土地应该自然拥有使用权”。
根据相关规定,对于已经有土地使用权拥有者的土地,要发生使用权转移时,一种情况是开发商直接从居民手中购买,然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另外一种情况是国家对原土地使用权人进行补偿并收回土地使用权后,才能把该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另外一个民事主体。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审批步骤中,受理条件之一就是要提交国有土地使用权来源证明文件,提交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这也就意味着要经过原土地使用权人同意转让他的土地财产即有价的土地使用权,才可能受理审批。
华新民向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2003年4月,金宝街的开发商在申请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填写道:“此处无墙已定界”。也就是说,开发商是把当时熙熙攘攘的市井说成是无人无墙无房之荒地,从而申请到了相关证件。对此,华新民感叹道:“他们简直可以把猫变成狗。”
为了证明自己家人是真正的权利所有人,在庭审中,华新民出示了这两处私宅的民国时期的房契地契,以及上世纪50年代国家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此证即文革后归还私产的凭证),还有颁发此证的时任人民政府地证局副局长的亲笔信和家住房客的证明信。“如果谁想表示此宅不属于华家而属于他的话,就请他出示他的房地产所有证,如此简单。”华新民在法庭上说。
事实上,在金宝街地区,因为胡同拆迁问题而提起诉讼的并非华新民一家。2005年3月1日,东堂子胡同55号院房主也将北京国土局告到了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状告其非但不向自己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反而将其转给了开发商,侵犯了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但是这场官司没有进行下去。如今,多数原住居民已经搬离了金宝街。
曾有开发商表示,在北京,没有一起拆迁官司打得赢。
华新民自2005年9月递交起诉书后,等了四个多月才开庭。她对这场注定艰辛的官司仍充满信心:“我的父亲一生都在建设北京,给那么多人筑了家,自己今天反倒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以一堆无效的‘公文’推出了家门。我现在要维护的,是我祖父的尊严,我父亲的尊严,和我自己做人的尊严。”
第三件事
在追讨自家房产的同时,华新民也没有忘记自己8年来坚持在做的事——保护胡同和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她在代理辞中指出,作为诉讼第三人的开发商,其拆迁行为同时违反了有关文物保护的规定。
华新民矢志不移,保护胡同,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基于她的家庭背景。她生于一个建筑世家,祖父华南圭,1948年受中共地下党邀请,担任即将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现北京市规划局)的第一任总工程师,并为缺水的北京设计了最早的官厅水库。华新民说到自己的家人自然是充满崇敬,但她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与家世有直接关系。
这个胡同保护主义者的产生,首先是1998年北京西单改造的结果。当华新民看到西单大街动土改建时,便跑去问专家,这是在干什么?专家告诉她,建设新北京,依据的是规划。她就非要别人帮她找到“规划”。当她看到指导着1991至2010年20年间北京城市建设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一下子傻了眼——她看到一个示例图,上面用不同色块标注着未来北京的城市格局,其中受保护的旧城区用灰色块表示,那些灰色块寥寥无几。
她明白了,北京所要面临的,是大面积的“新建”行动。
“我后来把这称为造楼运动。”华新民经历过文革,她觉得用“运动”这个词更合适。而英国《卫报》也曾经这样形容北京的城市化改造:“这是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只不过人们手中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当时的这个规划,为华新民和很多胡同主今天所要面临的纠纷埋下了伏笔:“要用房地产开发和土地有偿使用推动城市建设,把房地产业作为首都地方财政自我积累的重要手段(规划书第90页)。”华新民说,当时她看到这句话就留了心。后来,许多了解华新民的人都意识到,华新民保护胡同,并不仅仅是保护文化的问题,还是一个保卫自身居住权的问题。
从那时起,她就开始了这场一个人面对无数推土机的“战争”。
华新民原来从事翻译工作,生活本来很从容。她把生活中的事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吃饭必须做的,就是工作;另一种是自己能够获得快乐的。据她说,写点小散文,是她最快乐的事情。但是,1998年之后,她的生活里有了“第三件事”——保护胡同——并且最后主宰了她的生活。她每天的日程都安排满满的,全与胡同有关。——这既不是为了谋生必须做的,也没有任何快乐可言。
“昨天我还想,希望今天这一切可以停下来,我可以结束。我每天都希望明天可以结束。”她看着地板上那些和女儿油画习作混在一起的各种资料,不无伤感地说。
她常常拿出被拆掉的胡同的相片说,这么好的地方,他们怎么下得去手?这个高鼻蓝眼栗发的中年女子,每天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冲到各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去,用西方人的思维直白地大声争辩:“这么做是违法的!”
她不理解的是,8年来,居然没有人对她说过:我就是要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她表示同情、理解,说自己也不想拆。“但是等我一转身,他们拆得更快。”华新民说。
为了中国还是中国
在一次展览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木卡拉先生,指着一张即将拆除的院落照片惊奇地问华新民:“难道这也拆吗?”也有人对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被拆除大为震惊,因为那里已经被确认为曹雪芹故居——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自己拆曹雪芹故居,好比法国人拆雨果的房子,疯了。
但在华新民等人致力于保护胡同的同时,也有学者积极主张拆掉以胡同为代表的旧北京城,认为反对拆掉胡同的人都是没有在北京胡同生活过的“老外”,是不了解胡同的种种不便,是叶公好龙。他们认为,北京的老胡同,实际也是贫穷落后的象征,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人不会留恋胡同。
华新民出生在已经被拆掉的红星胡同,并在那里长到十岁。长大后,她经常往返于巴黎与北京之间,往返于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和一个一心要背叛历史的古老城市之间。可是,巴黎的繁华愈加使她眷念北京的胡同。
“如果想让胡同里的人生活得好,不是这样。这让他们更加贫困。”华新民反驳说。她记得在拆香饵胡同时,一个居民对她说:“这是逼人买房,强买强卖。”
关于北京城的改造现状,另一种解释是: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由于梁思成方案没有被采纳,几十年来北京的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一直混在一起,改变旧城的原有格局在所难免。
华新民不同意这一看法。她认为,这种混杂格局并不必然带来北京旧城格局的改变与消亡。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间,北京旧城所体现的元大都规划也受到了一些破坏,但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非正常观念所造成的。现在,保护北京的古文化特征已成各方共识,但是,由于钱在背后的作用,拆迁之风才会如此盛行。
有人对她讲,老北京已经快拆完了,你还能做什么呢?但她还是停不下来,每天还是要风风火火的冲出去。
华新民记得法国作家雨果写过一篇名为《向拆房者宣战》的文章,谴责路易、菲利浦时期对古建筑的大肆破坏。雨果的反对理由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
现在,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的华新民的反对理由是:为了中国还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