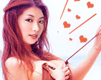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
□本报记者 胡劲华
离93岁生日还有26天,一代书法大师安然而去。
乐天知命
6月30日,启功离开的消息传出没多久,就在北师大中文系内引发了比较大的震动。在启功的灵堂门口, 中文系的师生已自发组织了现场吊唁活动,他们每人均佩戴着小白花,向启功先生默哀悼念。
一位1997年入读北师大的学子写下了一篇不忍删减的挽词。
“午休时间,习惯性的打开新浪,浏览新闻,一则启功先生逝世的消息震惊了我,毕业时候就听导师说先生身体大不如前,没想到如今已乘鹤西归,在这六月的最后一天。”
“大学里唯一听过先生的课是一堂关于声律的讲座,地点在五百座,大概是大一吧,内容大都记不得了,只记得阶梯教室的楼梯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先生以驴声的变化来讲解声韵的变化,实在是深入浅出。”
“始终认为,大学正因为有了大师,才得以称为大学。师大七年,白寿彝、钟敬文、启功……如今的校园,学富五车的教授、博导不少,大师却难觅。”
这个学子的表白就是最好的悼词,正如著名画家黄苗子所说,“其实启功是个魔术师,本来要变个凤凰,最终变出个金鸡也不错”。
实际上,早在1978年,启功先生66岁风头正劲时,他就曾经撰写过一篇《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这段《自撰墓志铭》让人充分认识到,启功先生实在是一个超然而又乐天知命的人,或许他对自己的离去比众人的哀痛更安然、更平静。
教育情怀
启功先生没有学历,一位校长就曾以上讲坛绝不能像小孩那种教法为由解聘了他。当时北平沦陷,启功先生不得不卖字画养家糊口。
尽管启功先生学养深厚,但他永远都是那么谦逊并富有童心。有个例子让大家很感动,安徽教育出版社曾出版《陈垣全集》,启功先生认为直呼老师名字,作为学生实在不忍,就要求出版社让他写副标题,里头写上“受业启功敬题”。
启功先生曾回忆校长陈垣给他的教育启迪,“陈校长自己也教一个班,30几个人,教国文课,经常围绕全班走一圈,看你字写得如何。当时他在黑板上写字,一行只写四个,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后面的学生根本就看不清,而这本不是作为校长必然要教的课。打这起,我就知道做一个教师应如何深入体验学生的需要,也知道了做教师的甘苦。”
就因为这个,启功先生再也没离开教育,教育其实是启功的主业,也是他最深刻的情怀。
国家良知
文革时,当时单位凑比例把启功划成右派。
“当时划到我爱人时,她很害怕。我告诉爱人你不要害怕,不要着急,不公正又如何,接不接受,毛主席自己说的只要服从,就完了。”从此,启功先生多了另一个练字的机会:为造反派抄写大字报,并因此成就“大字报体”。
对此,启功的态度是,“大字报故事整天写,在文革时那是光荣的工作,容许你写大字报已经不错了,有的能写还不让你写呢。这其实是件很幸福的事。”
这一点解读起来就是:苦中作乐的玩笑,比干其他的强。
实际上,启功先生就是打扫厕所也是十分超然的。
有人回忆,一次下楼时,从厕所里传来交流如何扫厕所的声音,仔细一看是启功先生在教一个老教授扫厕所的捷径,“启功先生说,‘扫地从四角,靠着一拖把’,和一个老教授讲这个,这真的很让我吃惊。”他说。
那几年,启功先生的生活非常艰苦,进了他的房间,你绝对会感到惊讶。顶棚纸糊着很多窟窿,地是泥地,墙高低不平且潮湿,就十几平米的地儿,而且还是借住侄子家,一住20多年。
作为一个国学大师,同时又是满清贵族的后裔,这样的生活条件实在是让人感喟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启功先生也一直保持着乐天的精神,而且就是在那些年里,启功先生完成了自己的很多重要著作。
启先生写起学术著作来也与他的人、他的诗一样没有架子,完全是“老实交代”。
大师唯一的遗憾,可能就是不知道身后将由谁来继续引领中华的传统文化。很多人都敬重这位白发苍苍大师,热爱他那孩童般单纯的笑容,喜欢他那空灵淳厚的笔墨,然而,所有这一切如今都成了追忆,尤其是他身上所凝聚的那种传统文化的博大精神。
钱钟书,费孝通,启功……一个又一个承载了民族良知的国学大师纷纷离去,在现今这个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难道真的是“教授、博导不少,大师却难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