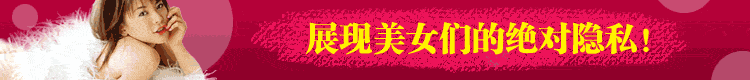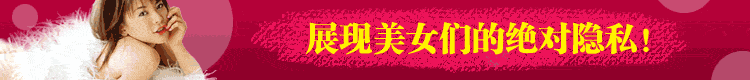|
谢忠荣
男人生下来就欠债,欠父母亲的,欠儿女的,欠女人的,一辈子也还不清。
何以为男人?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实际的问题。一直以来,我身为男人,以为这仅仅是一种性别,不管想不想它,也绝不会变性,可一旦思索这个问题,便陷入困惑之中,引起我
无限的感慨。
站在大山前,我想大山就是男人,巍峨、沉静。有不倾倒的头,有宽大的胸怀,希望是顶上的星月,丰富是肚里的矿藏;漫步在河边,我想河流就是男人,有着清亮的河面,有着深邃的河底,沿途获取一家老小的养分,该激情时汹涌,该温柔时浅显,遇到阻力,跃起来拍打,遇到悬崖,奋身扑下去。
夜里做梦,我想男人要嗓音宏亮,吼要吼个众山应,唱要唱得水欢腾;男人要睥睨天下,生得辉煌,死要雄壮;春太嫩了,冬显老了。
我以为,漫漫长路,男人只对女人存在永恒的幻想。别的,已在现实的规劝、现实的胁迫、现实严酷的推拉厮磨中消失又诞生,诞生又消失。但对女人的幻想,男人注定在劫难逃!女人是男人的骨架,没有骨架的男人就软了。白天,骨架支撑着男人的门面,夜里,骨架接受男人温柔的抚慰。
儿女是男人的血,没有血的男人是苍白的。血让男人有充足的活力,血让男人有了顺畅的生的意义,增加男人体魄的分量。
身为男人,我在思索。
这棵大树应该是男人,枝叶茂盛,根深蒂固,撑起一片天,伤痕累累依然挺拔,依然向天。
那条帆船应该是男人,乘风破浪,载着一家老小,顶着惊涛骇浪,驶向理想、驶向光明。
好斗的公牛是男人……
翱翔的海燕是男人……
奔腾的骏马是男人……
宁静的湖泊是男人……
思考死亡,是男人一门必修课,以形成一种豁达的胸怀,视恐惧为无聊,从生命中衍生出男人的激情,为爱情、诗歌、音乐、自由……披上一层太阳的光芒。
男人要真,说真话,做真事,唱真感情的歌。男人要美,风骨美,气质美。男人要以天下为己任,演出历史、演出辉煌……
何以为男人?我依然茫茫然。也许天生男人的我,每走一步都在圆一点男人的梦。早晨起来,活动活动筋骨,鲜灵灵地投入到工作、生活中去,我想这就够了!
《市场报》 (2005年05月10日 第二十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