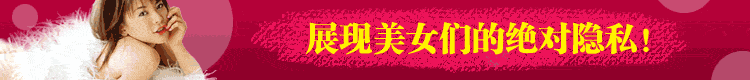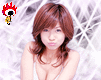|
葛丰
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放弃内地、香港同步上市计划,转而选择先行赴港上市。由此联系一段时间来该行“先A”、“先H”、“A+H”传闻不断,不难窥见内地金融业改革之步履维艰。
交通银行上市悬疑直接源于境内外股市市盈率之差以及内地股市持续6年低迷市道,而从更深层次来看,新一轮以国有银行注资股改为标志的金融业改革由来于内外部环境的倒逼,种种先天性的不足实则决定了上市计划之摇摆不定,其他国有银行也不会例外。
《经济学家》杂志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上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制定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知道了实现强劲的长期增长与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通常要强于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这种来自于成熟经济体的舶来品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较为明显地表现出效率优先的取向,而在另一方面政府又会一再调用优势资源直接救助困境中的国有企业———除去根本国情的约束外,笔者认为上述情况的出现是可以解释的,尽管其效果往往又是值得怀疑的。
现在,中国的金融改革似乎更在努力实现这一预期,即通过对国有银行的公司化改造优化资金资本的配置机制,从而使微观调整与长期增长产生某种良性互动,而在这一过程中,上市无疑成了“花钱买机制”最具观感的一环。
但是“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的“三步走”方案仍未触及此项改革的最难点,即打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几乎必然走向的国有股“一股独大”宿命,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杠杆作用,引入多元战略投资者,完善内外部监督,从而真正营造起适应现代经济条件的公司治理制度。关于这一点,现成的反例可谓多矣。
值得指出的是,论证上市是否提升国有银行绩效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并非本文的目的,事实上,面对真实世界,我们赖以生存的大量因果性知识,很少经得起“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的推敲,这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而就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真正的警觉应该付于这样的可能:中国的改革不会因为无谓的反对而嘎然中止,但极易由于不断取得的成就的支撑而产生持续改进的倦怠,以及对于大量经验事实背后客观规律的不置可否。
中国经济长达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验证了政府主导下的“渐进主义”与“增量式”改革的成功,而在具体手段采用中,“试错”与“模仿”亦不失为有效的方式,而现在的问题是,在必然出现的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挑战性的问题将不再是逐步的市场化是否导致了经济的增长,而是如何避免对于为经验所支持的增长路径的过度依赖。
中国金融改革的长期滞后或正合乎这种情况。马克思曾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还没有铁路。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间相互需求、相互支撑的一般规律在我国则表现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与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存的奇异局面(当然其间不乏成功处可资发扬),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曾两次对国有银行施以巨资救助。
具备某种关联度,以往两次不甚成功的财政支付促成了这一次“花钱买机制”决心的形成,这实在是一次重大的观念的进步,问题则在于“如何花钱”,买“怎样的机制”。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
诚然,针对这一观点,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另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场论战存在大量前提性的语境,且未必适用于本文的论题,尽管如此,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认识,笔者认同这样的争论是有价值的,其中当然包括两位学者创造性的工作。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的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无法遵循任何已有的成功经验,但至少,如何破除杨所提出的“后发劣势”以及发挥林所认为的“后发优势”,这是值得思考的命题。
回到银行重组这一问题上来,汇金公司的组建以及上市目标的提出系这轮改革颇具标志性的两大特点,可以认定的是,这仍然体现出“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以及“模仿”加“试错”的应用。在中国微妙的文字系统中,“机制”与“制度”可以是一回事,也可以是两码事。所以说,笔者对于不无误导的媒体关乎国有银行上市持续高涨热情,虽不难明白但始终很难理解,很显然,在大量根本性的问题依然不甚明了的情况下,所谓悬疑云云,其本身并无悬疑。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5月10日 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