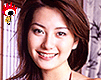|
谁是“中产”?由收入和财产量化得来的数字分野,对这个群体的描摹和探究而言,究竟是原始起点,还是陷入数字化想象陷阱的开端?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问题。相对于“中产阶级”这个定义,中国的学者更乐于在“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和“中产阶层”这三种表述中进行选择和界定。中国社科院研究者张宛丽认为,对于这个群体“社会意义”的评价,远远超过对于其具体收入的考量
30万份问卷,有效问卷263584份,诸多的数据分析之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综合处处长程学斌给出了国家统计局目前的最新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年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这次历时4个多月的抽样调查,最终的数字结论是否值得信赖?
程学斌用另一种计算解答这种疑惑,“假定完成一份问卷的成本是20元,30万份样本,仅仅最低人工费的支出就是600万元。不仅如此,沿海和东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完成一份问卷,没有40元根本下不来。”程学斌反问,“如果不是为了最真实的数据,有必要动用这么大的调查规模吗?”
程学斌说,原本他们想定的名称是“中产阶层研究”,“考虑了多种因素”,最后还是选择了“中等收入群体这个十六大报告里的说法”。而只选择城市,放弃农村的样本调查,同样是考虑到中国中产阶层研究的特殊性,“这个群体在城市的比例和现实性远远大于农村”,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城市社会成员中收入丰厚的家庭群体”,这是国家统计局给出的界定,相对简单,将“收入”作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显然让他们对于这个群体的描述完全具备可“数字化”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这个“收入”指的是当年获取的能用于个人支配的各种收入,其前提不一定是合法收入。
“6万元~50万元”标准,程学斌解释,“并不只是一个单向的推导,也是用结果验证了的”。记者仔细询问了这一数据的推导过程发现,这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推导,作为任何一个非核心权力机构,甚至无法来验证它。
测算的起点还是透明的,来自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和上限,分别为3470美元和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相应的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首先是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程学斌说,这两者之间有着相应的比例关系。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研究,2004年,GDP的增长为9.5%左右,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为8.5%左右。第二重换算是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在这种换算存在的问题是,汇率仅仅只是一个国家货币的价格水平,它代表的只是国家进出口水平和竞争的平衡点,并非真实的购买力。所以还有第三重最为关键的换算指标——购买力评价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在中国同样的生活水平,换算成其他国家需要多少钱?但是对于这个最重要的指标,程学斌只能表示歉意,因为“这个指标在我国是保密的,不能公布”。
程学斌也承认,关于购买力评价标准,我国和西方国家的计算存在差异。1993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其根据购买力评价法重新估算的结果,199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3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4740亿美元,在总量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排名世界第三。这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海外报刊如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英国《经济学家》等有影响的报刊都对这一新闻作了突出报道和评论。一时间,中国一跃而被捧为世界经济巨人。同样,用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经济实力,美国政府有一年计算整个经济实力排名是这样的,中国GDP已经达到6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60%,相当于日本GDP的1.7倍,相当于德国的2.7倍,相当于英国的4倍,英国GDP总量是1.5万亿。
根据三重换算而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高收入省份中的10%高收入组的收入水平是最低收入省份的2.5倍,所以,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成为6万~50万。
只是因为购买力评价标准的保密,验证推算的努力显然无法再继续下去。这种难题,对张宛丽这样的研究者而言也无可奈何,“我的一个同事,在国外参加一个会议,就曾经被国外的学者追问某些统计数据的来源的推算,那种情况当然很尴尬”。
“忽然中产”的想象
事实上,263584份有效样本的最后结果在标准的确立中同样重要,重要到甚至并不需要取得那个保密的购买力评价标准,和几重复杂推算,同样可以得出相同结论。
程学斌说,最后确定标准,“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标准必须要考虑到20年的发展速度,十六大讲话中明确提出来,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要达到相当的比例”,有效样本中,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家庭为241746户,占到全部比例的91.7%,5万元到6万元之间的家庭为8471户,6万元到7万元之间的有4747户,7万元到8万元之间的2540户,如果把标准下限定为8万元,“那20年的发展,也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但如果定成6万元,“那很多人努努力就可以看到希望了”,而且按照这个标准推算,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为45%。
即便是考虑到了城市之间的差异,6万到50万家庭年收入的界限,看起来的确是让人充满希望的“中产”指标。但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界定中,收入并不能成为被强调的起点。
吕大乐说,在香港对于收入的讨论并不多,“这不是一个太有用的分类”,就香港而言,月薪2万到5万港币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这并不等同于你就成了中产阶级”,“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你的消费方式,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吕大乐说,香港中产阶级的特殊性,在于楼价和股市对于他们可以形成相当直接的刺激和影响,“负资产”是吕大乐描述过的香港资产阶级在金融危机中的必然结果。吕大乐认同的中产阶级概念,类似于美国社会学者赖特·米尔斯的界定,赖特·米尔斯按职业界定的方法,将农夫、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归之为老中产阶级,将随着美国20世纪公司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经理、雇佣职业者、推销员和诸多的办公室职员归之为新中产阶级起点是职业和上升方式。同样,吕大乐界定中的香港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而这样的一个群体,对于香港社会而言,“实实在在参与建立了一个开放社会与其相关的价值和文化规范”。
在这样的评价标准中,吕大乐认为,香港的中产阶级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到25%,这个群体并非是家财万贯生计无忧,事实上,本来一直在相对安逸的就业环境里工作与生活的中产阶级,现在也逐渐被卷入裁员、失业的漩涡。与此同时,稳定的工作环境、长期雇佣的安排及阶梯式内部晋升的制度亦随之而改变。说中产的“组织人已死”,并不夸张。吕大乐甚至还认为,即便是被称作有着庞大稳定的中产阶级的美国,按照他们的评价标准,中产阶级的比例也不过是30%到40%之间。
如此看来,中产究竟是什么?在物化的指标和社会意义的评价之间,不同的视角甚至可以得出差异相当大的结论,在社会学者和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中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经济状态,或者说,起码不只是一种经济状态。地位声望、教养职业、经济收入、社会交往,这些统统都是不能回避的指标。如果过分关注收入,关注的中心实质上会发生改变。-
“权力中产”的中国现实
中国的现实,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中高层领导干部成为“中产”的机会最大,因为他们占有资源,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
学者张宛丽指出,目前中国的分层研究,是以职业为基础,参考经济资源、政治资源以及文化资源三项指标,从而得出的综合评价。不论是学者的研究视野,还是国家统计局调查所得的结果,两者在某个层面上实际是不谋而合。
根据统计局的调查结果,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中高层领导干部成为“中产”的机会最大,因为他们占有资源,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由此而来的中国“中产”的特征相比欧美国家显得更为多样化。张宛丽说,在中国,“收入于社会地位事实上并非正相关”,换言之,收入的评价和现实的地位评价之间可能存在极大差距,比如学者教授,在发达国家,都属于社会的中产,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也有丰厚的物质收入,可以支付文明生活所需的开支。但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学者的收入甚至还有可能低于城调队得出的中等收入群体底线。
同样,在拥有政治资源的群体中,收入也成为并不可靠的指标,这个群体的工资并不高,但是他们可能由职务而来的可支配收入很可能远超于我们的视野,同样,在不同的级别中,等量的金钱也会有不同的含义,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处级干部的月薪2000,和一个局长的月薪2000,虽然字面上一样,但事实上并不具备可比性。
对于拉高收入平均值的一个群体——私营企业主而言,是否将他们纳入中产,同样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在西方的事业中,这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不属于新中产,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整个群体却是中产强有力的支撑部分,这也是一个尴尬的问题,对私营企业主有多年研究的学者张厚义给出的数据,是目前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400万,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素养,消费方式上并不能达到社会意义的中产标准,但是,“你却无法将他们从这个群体中排除”。在更隐蔽的层面,政治资源和财富的结合,使得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不可割裂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