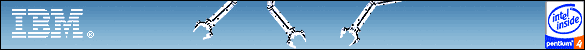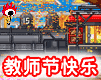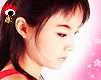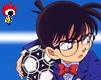| 农村土地为何日趋细化?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4日 13:00 21世纪经济报道 | |||||||||
|
文贯中 农地改革初探(之二) 上期回顾:作者提出了中国农村的逆淘汰概念,即富裕农民选择离开农村,使中国农村出现了逆淘汰趋势,这个过程和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截然相反。大部分农民
中国如果选择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独特道路,将大大提高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本。对中国而言,这条道路将是十分不经济的,也会使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人为延长,对农民十分不公。 3 如果中国的农地越来越细化 社科院的报告佐证了另一报告的发现。据美国麻省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教授布瑞纳的研究,中国农户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499下降为1995年的0.378。考虑到土地的生产力会因灌溉之利的有无而大有区别,布瑞纳将有灌溉能力的土地转化成无灌溉之利的标准土地单位后重新计算基尼系数,结果发现土地分配的不平均性依然由1988年的0.465下降为1995年的0.365(布瑞纳,2003)。也就是说,土地在农户间的分布越来越细化了。照理说,由于东部城市化明显快于中西部,中西部农村人口大量向东部城市转移,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应该逐渐向种地能手的手中集中。为何这种集中趋势远远抵不上细化的趋势呢? 其实,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土地的细化是必然的。农民获得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不是所有权。如果向村里上交土地,他们得不到任何报酬。所以即使他们外出打工,也会想尽一切方法留住土地,因为不留白不留。在现行土地制度下,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土地细化必然加速发展。快速的城市化无法减缓这一趋势。 纯农户的困境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纯农户收入问题,特别是纯粮农的收入问题特别严重。原因有多种。首先,粮食生产的周期长,一般一年一到二茬。由于投入的成本高,粮价低,种三茬的农民大都感到得不偿失。其次,粮食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低。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对粮食消费及其价格的带动非常有限。只要粮食产量稍微过剩,粮价便大跌。对小农来说,本来粮食的商品率就不高,如果碰到粮价大跌,往往入不抵出。所以,粮农除非能扩大经营规模,单靠耕种几亩地是无法获得平均收入的。相比之下,菜农,花农,药农等所需的土地规模就要小得多。以菜农为例,他们大多靠近城市,因而靠近市场。其次,大多数蔬菜的生长周期较短,往往只需几个星期。所以菜农一年能有十几茬收成。作为健康食品,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的提高,蔬菜的收入弹性也变得较高。如果菜农掌握时令,往往获得较高的收入。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菜农和粮农相比,不需太大的土地规模和较多的资金周转便能获得平均收入。 在市场经济中,种植不同作物的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是由价格调节而自然形成的。粮农所需的土地经营规模必然较大。如果一些粮农无法得到平均收入,他们或者退出经营,或者改种其他作物。这样必然造成粮价上涨。退出经营的农户为其他粮农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创造条件。粮价上涨则有助于粮农收入的上升。 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户土地经营的规模主要由集体已有的土地和该农户在全村人口中所占比重所决定。尽管政府出台了土地承包法,允许土地的转包和出租,然而布瑞纳的研究表明,种地能手通过转包和出租扩大经营规模的速度至少不足以改变土地分布基尼系数的不断下降的总趋势。 这是因为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下,转包和出租带有种种限制和不确定性。例如,转包或出租双方要获得集体同意,交易成本比土地私有制下农户之间的直接交涉高得多。特别对来自外村的接包者来说,手续之复杂令人兴叹,对土地和劳动在全国范围内,更不要说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组合,构成严重的制度障碍。 例如,根据中国现行的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如此高的交易成本,往往使协议双方不得不瞒着集体交易。然而这样一来,又使承包协议的有效性缺乏透明性和法律保障。这些原因使土地流转的速度很慢。 村集体是“社区型企业”吗? 中国农地细化仍在不断发展,农户收入相对城市居民又呈每况愈下的趋势,国内的一些关心农民收入的学者,在不动中国的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企图找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 例如,最近有机会看到张宇燕、时红秀和李增刚(2004,以下简称张文)合写的“中国农村的社区型企业:辽宁省海城市东三道村为例”一文。他们通过对一个案例的考察,“试图对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村集体’的性质和功能进行深入思考”。他们“将‘村集体’看作既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的延伸,又是有着明确产权边界和利益要求的企业。”在他们看来,“与经典企业相比,这种企业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社区性’特征。在权威和激励、社区成员与企业的关系、企业的目标与行为方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村集体都有着突出的社区‘共荣’秉性。”为此,他们称“村集体为‘社区型企业’。这种企业产生于特定的产权制度、市场条件和农村社区的自然禀赋与人文环境之中,既为辖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又替个人承担市场风险”。他们并且认为,“不同于大规模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和城镇化过程,社区型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或普遍化,或许为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工业化和市场化途径,并可能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种选择。” 对此,我想作以下评论。首先,如果这种社区型农业企业真是中国农民自发和自愿进行的组织试验,自然应该支持。但是,历史上,自然村,更不要说包括几个自然村的行政村,从来不是一个经济体。只是到了人民公社时代,由于政府的强加,它们才成为一个效率低下的经济单位。所以,出现整个村子加入一个社区企业,而且还能整个“兼并”邻近的村子,使人怀疑农民究竟是否有选择的自由。 其次,如果这样的企业确实很成功,那么,在土地私有制下,农民同样会踊跃入股,不然欧美各国不会涌现那么多股份公司。所以,私有制并不会阻止农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对生产组织的各种形式进行自由的试验性组合。第三,有了土地私有制,可以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利益和迅速淘汰无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这种企业真是基于完全的自愿,那么,当某些农民感到自己所在的企业带给他们的利益不如单干或重新组织一个新的企业时,在土地私有制下,他们有完全的退出自由,或重组的自由。张文没有对退出机制作比较细致的介绍。我很想请教的是,这种股份合作制的试验有没有失败的例子,是否对此作过调查、分析?万一企业失败了,谁承担后果?如果个别农民首先看出企业的败象而要求退出,他对土地的权益和其他经济利益又是如何得到满意的补偿呢? 第四,如果大面积地由政府推广这种组织形式,由于这种企业不但政社不分,而且政企不分,这会使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有更大的权力指挥农民和控制农民。一旦这种控制掌握在坏人或无能的人手中,或一旦企业经营失败,后果是严重的。 第五,张文认为股份合作制能够避免“大规模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和城镇化过程”,为“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工业化和市场化途径,并可能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种选择”。也许并非完全如此。城市化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其通过积聚效应,大大降低所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降低现代化的成本。凡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无例外地是通过高度的城市化完成的。中国如果选择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独特道路,将大大提高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本。对中国而言,这条道路将是十分不经济的,也会使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人为延长,对农民十分不公。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未完待续)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国内财经 > 聚焦农村土地纠纷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