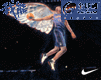| 甲午战争与“历史三峡”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0日 16:55 中国经济时报 | |||||||||
|
甲午战争110周年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附近海域对中国运兵船及护航舰发动突然袭击,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也发布宣战诏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战争结束,至此洋务运动全面失败;有见识的政治家,如李鸿章已认识到国家面临的困局是“三千年一大变局”,而这一变局中最重要的是帝国转型…
张剑荆 晚清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曾经向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询问中国复兴之道。事情发生在1896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与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出使欧美,6月抵达德国。媒体记述他与德国前宰相俾斯麦答问情形: 李:我专程前来拜访殿下,有一事想“乞垂清诲”。 俾:什么问题? 李:“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 俾:辱承阁下明问,“惜敝国去贵国较远,贵国之政平时又未尝留意,甚愧无从悬断。” 李:“请问何以胜政府?” 俾:“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故各国大臣,遇政府有与龃龉之处,非俯首以从命,即直言以纳诲耳。” 李:“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 俾:“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 李:“中国非无人之为患,特无教席亦无兵法之为患。”“惟异日回华,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且需聘教习之武弁,仍惟贵国是赖。” (《李鸿章传) 甲午何以败?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一年前的惨败,并无反省。他向俾斯麦讨教中国复兴之道,问了两个问题,一是“何以胜政府”,二是“政府何以图治”。第一个问题中,包含着他对甲午之战失败的解释:甲午败于日本,只是他这个臣子没有办法“放手办理”,最后导致“兵不练”的结果。因甲午清朝海军惨败,《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遭到国人痛诋,在失意中,李鸿章回顾其一生事业时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犹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在这短暂的赋闲期间,他抨击“言官”:“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游历欧美之后,得出欧美“上下一心”,而中国却“政杂言庞”。他把失败归之于政府受“言官”左右的结果,如果更为专权,就不至于这样了。因此,在向俾斯麦寻求复兴之计时得意洋洋地告诉俾斯麦,有人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就毫不奇怪了。作为当局者,李鸿章确实执迷顽冥得很。中国的复兴竟然归结为“放手让我干事”,可见他的复兴概念,不过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中兴”的同义语。只要中国出现一个威廉二世那样的能让俾斯麦干事的领导人,就可以了。至于第二个问题,表明他仍然深信自己一生练兵事业乃中国复兴之关键。表示回国后,要学习德国军制,“惟贵国是赖”。 历史学者很重视外部刺激对变革的影响。但是,在李鸿章这里,外界刺激似乎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他一直延续着练兵强国的思维路线。 李剑农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这样评论李鸿章:他相信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之俗好,不过亟则治标,非取外人之长技以为中国之长技不可。故他的洋务事业的范围,不外造船、制械、筑军港、设电报局、招商局、织布局、矿务局,概括地说,不出于军事,经济的两方面,而经济方面又以裕饷为目的。就是兴学堂派遣留学生,也是全为军事起见,否则为造就翻译通使人才起见。对于政治、教育思想及制度上的根本改进,完全没有梦想过,因为他认定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好的缘故。所以梁启超批评他,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他所办的事业,郭嵩焘在中法战役以前,已知道不是根本救济中国的办法,不能靠着作用,不如日本模仿西法的方针正确。 李剑农的评论可谓中肯。李鸿章所开药方不外两种,一是军事,二是经济。前者是要建立强权,后者则是为军事强权提供条件和支持。其整个构想,概而言之曰“练兵”。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在兵与民上,他选择兵,在内与外上,他选择外,在朝廷与国民上,他选择朝廷,在洋务与国务上,他选择洋务。民生被遗忘了,内政被遗忘了,国民被遗忘了,如此强国,国可强吗?从李鸿章与俾斯麦的对话,可以看出,李鸿章实在是缺乏反思,梁任公对李鸿章的“只知练兵”的评价,也不是什么苛评,而是知人之公论。 李鸿章对甲午战败的检讨,是那种空言“复兴”而实则顽冥不灵的例子。试举两个学者的分析以于李鸿章的分析作对照。 马士和宓亨利在他们的巨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总结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时说道: 甲午一战,中国不但战败,而且蒙垢受辱。中国军队始终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形胜之地一一委弃,临阵不战而逃,中国殷殷寄以厚望的舰队被可耻地驱逐到设防的港口内匿不出战。中国的将领们个个显出无能,而且很多是懦夫,政府的颟顸腐败,在国家危急之秋并无异于承平之际;而中国人民虽则有了一点国家意识,还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其惟一的原动力就是个人利益,但知盲目的愤怒,却不知为国家利益而发愤图强。在战争期间,中国并不是以最大的精力用之于杀敌致果,而是用之于乞求列强的干涉,中国的统治者们指望不须认真努力救治其积弱的原因,而但求借外力以挽救中国免于自食其积弱的后果。挽救中国面与侵略与瓜分,是列强的义务,而中国却不负任何责任……随着和约的缔结,中国的大臣们已普遍不为人所信任,就连中国的惟一政治家李鸿章也不例外。中国是屈辱备至了。在一切有经验(是西方所谓的有经验而不是东方所谓的那种有经验)的观察家们看来,帝国的瓦解似乎已显然迫在眉睫而无可避免了。 甲午之战是中国学生都熟悉的。但是,他们熟悉的是清政府所表现出的战斗意志和将领的英勇。在马士和宓亨利的眼中,战斗意志不过是“盲目的愤怒”。有些怀疑精神的中国学生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或许感到奇怪,以四亿人口的大国,何以落败于小日本?再往前推一下,从1840年开始,战则必败,总是远离本土为数千人的西方军队,把数以万计的中国军队打败,把首都占领,难道仅仅是军队的问题吗?仅仅是他们船坚炮利吗?马士和宓亨利的描述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在这个答案中,没有谈到武器装备上的差异。如果总是临阵而逃,拥有什么武器才能打胜仗呢?更何况,虽曰有四亿人民,但是,这是一些有很少“国家意识”的人民。 对于这场战争,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剑农做出了大致相似的解释。他认为,这场战争的失败除了政府和官吏腐败和政令不统一两者外,还有一个总的原因:就是日本已经成了一个近代新式国家的组织,政府是一个国民结合体的单位,有一个主脑的神经系,五官四体运用灵活,无障无碍。中国还是停滞在旧时代中的国家,政府自为政府,人民自为人民;国家的各种机关是皇家的机关,立于皇家最高位的人,又成了没有活动能力、没有灵敏感觉、没有振作精神与纯正德性的偶像,立于这个偶像之下供他役使的人员,无异于衰败之家的奴仆,各图各的利益与快乐,懒惰、偷窃、斗争无所不为;有一二个忠实有为的人站在里面,想把那个衰落的门楣支撑起来,纵具三头六臂也无所施其技。当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马关会议,彼此应酬的闲谈中,李氏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之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伊藤博文答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语见《中东战记本末》这虽是应酬的话,却是实情。原来日本所以制胜,因为日本已经过一次政治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维新党先制胜于内,故能制胜于外。中国此时最需要的,也是政治革命,但是主持西法的新人物还是拘束在旧偶像之下,不敢作政治革命的活动,内部国民全无整个的活动新精神,对外安得不失败呢﹖不过有了这一次的失败,旧偶像的威力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政治革命的势力要开始发生了。 1896年,李鸿章在向俾斯麦求教的时候,仍然孜孜于如何处理大臣同朝廷的关系,把复兴之道还寄托在练兵一项之上,自然是愚钝的。导致这种愚钝的根源,首先是皇权主义世界观约束下的局促视野所限。在这种视野之下,他所能想到的,也只能是如何中兴,就像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那样。每当王朝陷于重重困境,那些忠臣总是希望革除积弊,重新振作,恢复王朝鼎盛时期的所谓繁荣。可以把这种世界观称之为复兴世界观。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公允地说,在晚清政坛上,李鸿章并不算最颟顸之人。他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疏反对取消福建造船厂时就提出,国家面临的困局,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是很有见识的,是极少几位有全球视野的大臣,也是极少几位有地缘政治知识的官员之一。他看到,中国的地缘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数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且他也看到,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乃在于洋人的枪炮轮船。他也知道,传统的处理危机的办法,皆已失灵。这种见识,在清朝宫廷内外,堪属罕见,无怪乎西洋使节都看中李鸿章,只买他的帐。 但是,李鸿章仍然是愚钝的。他把洋务的失败,归结为“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这是他一再重申的观点。 而对于导致三千年一大变局的真正原因,他一直不清楚。那么,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变局是什么呢?答案可以有多个,比如工业革命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但是,比较而言最为重要的,应当是帝国转型。 表面上看,当时主要大国的政治形态,还都是帝国。俄帝国,日本帝国,德意志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奥匈帝国等等,大国之中,真正不是帝国的只有美国。清帝国从国家组织的形态上看,与上述帝国是类似的,亦即都有一个皇帝位于权力的最上层。 这种类似也只是仅此而已。这些帝国已经经历了长期的转型。到19世纪40年代开始对华战争以后,西方诸帝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帝国转型的最后阶段。帝国最表面的象征,亦即君权的合法性,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岌岌可危。帝国转型的核心,从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角度看,是人民对国家及统治体系的认同问题,这个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运动,一是民主化浪潮,一是民族主义浪潮。帝国能不能顺利转型,取决于君权国家是否能够把民主和民族整合进国家体制中。进入19世纪后半叶,欧洲的政治形势已经变得很明朗了,就是帝国必须完成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转型,否则就无法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竞争的需要,使欧洲君主国家把民主和民族主义视作十分实际的问题,因为,没有这两者,国家就没有力量,公民就无法成为可资利用的资源。比如近代战争越来越依赖一般国民的支持,这迫使君主政权采用征兵制。而这样,就需要承认公民的政治权利。 欧洲和日本的帝国转型并不是在平静中发生的。 从17世纪开始的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同时也是帝国权力体系转型的开端。皇权在这几个世纪中,可以说一直处在危机的形势下。皇权与社会新兴力量间的博弈,是国家权力体系变革的基本动力。经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进入快速变迁的时期,民主成为革新社会生活的动力。为了挽救革命中的君权,君主国家必须将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这构成帝国转型的两股最强有力的动力。 当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发表权利法案、法国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把“朕即国家”扔近废纸篓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王朝的鼎盛时期。这个新起的王朝自以为秉承天意,统和万邦。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人民,重新匍匐在皇权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想办法成为新朝的顺民,知识分子进入了新一轮科举取士的生存通道中。人民被更加强固地纳入皇权秩序中。自然地,对于欧洲一隅发生的革命,也是闻所未闻。然而,这却是欧洲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关键一步。马克思把1648-1688年和1789年的这两场革命,称作“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显然,马克思没有注意东方这个正在产生完全相反要求的国家。 1840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距离这一转折点最近的欧洲历史事件,是1848年的革命。可以说,当时的欧洲社会,远比清朝皇帝统治下的中国紧张不安。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当时对于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1848年蔓延全欧的革命却不然。 1848年2月,巴黎爆发二月革命,摧毁了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浦弃位逃亡。革命者重申了1889年的共和主义原则,组建了新政府,通过了新宪法。发端于法国的革命,从一个国家传向另一个国家。3月维也纳发生骚乱,梅特涅被罢黜;接下来,是米兰起义。 对于这场革命,当时的观察家已经十分清楚地明了其意义。托克维尔在革命爆发的一个月前就说道:“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火山口上睡觉……你们没有感觉到……欧洲大地又在颤动了吗?你们没有感觉到一阵革命之风已在空中振荡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改掉政府的精神状态吧,因为,我再说一遍:这种精神状态正把你们带向深渊。”在他说这话的前一年,托克维尔分析了即将来临的革命的原因:广大的人民大众被法律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欧洲民主史》的作者在评论这场革命的时候指出:“这场革命是由政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群众之间、政府与臣民之间严重的分裂、对立引发的”,尽管这场革命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诉求,“但是这些事件的主角却都是人民:人民走上街头,人民筑起街垒,人民参与集会,人民群情激动地表达自己的谴责。全欧洲的报纸都赞扬人民的勇气、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无私。人民被称为政治变革的英雄。”在1848年的革命中,人民被推上了“王位”,他们成为新的崇拜对象,代替了昔日那些王公贵族。在这场全欧范围的革命中,人民的“公民意识”最终形成了。这场革命“标志着欧洲人民思想方式的一个转折”。 与欧洲革命的混乱相应的是,东方的中国,却陷于另一种混乱,因欧洲帝国主义者带来的惊扰而产生的惶恐、敌意和不安。马克思1853年评论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预言,这场战争将引起中国的解体和革命。他所谓的革命,指的就是类似17世纪以来,尤其是1848年那样发生在欧洲的社会革命。 但是显然,在清朝中国,这场革命并没有发生。帝国固然已是危机四伏,可是帝国转型的问题并没有被严肃地提出过,有些先进思想的人,提出的不过是如何中兴而已。甲午战争失败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帝国体制是无法对抗革新过的国民国家的。1894年的中国还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政府自为政府,人民自为人民,“国家的各种机关是皇家的机关,立于皇家最高位的人,又成了没有活动能力、没有灵敏感觉、没有振作精神与纯正德性的偶像,立于这个偶像之下供他役使的人员,无异于衰败之家的奴仆,各图各的利益与快乐,懒惰、偷窃、斗争无所不为”。 而日本已经成功地转型为一个近代新式国家组织,政府拥有合法化的资源动员能力。 “历史三峡” 由于清代中国社会内部和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无法形成自我主导的转型,中国近代的转型只能在外力强制下被迫进行。其结果是转型的失败。中国现代史上的众多问题,都与帝国转型失败有关。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历史三峡”一说。他认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转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转型“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亨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晚清七十年》) 这是一个很见眼光的判断。他恰当地把这第二次转型称为“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也是准确的。确实,绵延200多年的大转型,其实质,乃是政治社会制度的转型。 笔者认为,可以把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这次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转型时期,最后的结果是:国家在帝国解体后陷于军阀混战的大崩溃状态,这一阶段持续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立。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对应事件是1929年西方世界经济的大崩溃。世界进入到一个强国危机和两极世界开始形成的时期。这一阶段历时90年。 第二阶段,从1930年开始到冷战的结束,即1991年。这是国家主义转型时期。民族国家的建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在这60余年间,中国一直处于两种类型的国家模式冲突之下,即先是德国、后是苏联模式与英美模式的冲突和争夺。在这一时期的后期,中国开始了更加积极的而且主要是和平的探索。中国的改革探索终于走向做出“同世界接轨”的选择。中国的选择对于终结冷战,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阶段,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从1992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将一直持续到中国建立起来稳定的、普世宪政体制为止。稳定、富强、民主和自由的中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以后,大致需要花费60年以上的时间。 以选择市场化道路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中国崛起舆论也恰恰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在此之前漫长的近代史上,中国崛起只是一种可能性,拿破仑那句名言,即不要惊醒“中国睡狮”,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固然起着慰藉的作用,但是,雄狮毕竟是沉睡的,对于一代一代精英而言,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当他们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追求“站起来”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中国的崛起,并不被国际舆论认真对待。当中国不再以挑战者身份出现,而是加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中国崛起,反而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市场化道路,推动了全球主义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一选择,使市场体制推进到了全球市场在地理上的最后边界,而全球体系的形成,又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战略,使她决定性地走向渐进转型的道路。全球主义与中国崛起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中同时态的革命性事件。两者是相互促进和互为条件的。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长期转型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一个事件。如果忽视了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这一事件。以往阶段转型的成败,也与全球主义的发生史相关联。全球主义的“史前时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转型进程。在中国转型的每一历史阶段,其特定的历史问题和基本目标深深地镶嵌进全球主义进程中。而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在于,在每一历史时期,转型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事件。帝国转型失败了,国家主义转型也没有完全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也是中国命运的歼语,可以说是对中国转型过程的恰当描述。其结果是,当我们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其史前时期的问题。不得不继续同那些未终结的幽灵周旋。这些先前时代的幽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时常穿着新的衣服,来到我们身边,与当代人迫切的议事日程一道,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滚动新闻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