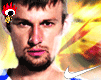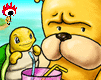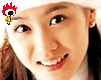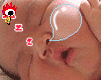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瞭望东方周刊:律师难做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6月16日 12:12 《瞭望东方周刊》 肖山 | |||||||||
|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肖山/北京报道 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常常把被告人和罪犯当作“一伙的” 走出看守所,麻广军没有丝毫的轻松感觉。尽管法院一审宣判他无罪,但二审结果还没有出来,他心中的石头还不敢落地。
麻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律师。2004年3月20日,内蒙古宁城县法院宣布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妨害作证罪”的麻广军无罪释放,至此,麻广军已经在看守所里呆了210天。不过3天后,宁城县检察院提请抗诉,要求中级法院“依法改判”。 直到6月1日,最新消息传来,赤峰市中级法院终审裁定麻广军无罪,他才终于舒了一口气。 “死亡条款” 事情源于一宗强奸案。2002年12月20日,宁城县农民许某因涉嫌强奸同村聋哑人魏某而被公安局刑事拘留,许承认曾对魏实施强奸两次。 2003年2月11日,许某翻供,称自己是冤枉的。但法院仍然认定许强奸犯罪成立并判刑5年。 此前,麻广军于2002年12月30日接受许某儿子的委托,同意为许某出庭辩护。 麻广军在法庭上出示了7份证据材料,试图证明许某无罪。同时,张玉兰、高金英等7名证人均证实许某没有作案时间。在此情况下,控方提请休庭。 休庭第二天,宁城县检察院和宁城县公安局相继把7名证人带到宁城县看守所。其中,53岁的张玉兰在看守所被置留36小时。期间,张玉兰一直被询问是受谁指使作证的,是不是受律师指使。审讯之后,7名证人承认自己作了伪证,并说是由律师麻广军指使的。 因此,许某被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麻也因涉嫌“妨碍作证”被关进了看守所。 后来,赤峰市中级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法庭上,原来承认作了伪证的7名证人再次称许某没有作案时间。宁城县检察院和公安局再次将证人传唤到看守所进行讯问。证人又相继推翻了法庭上的证言。许某再次被判有罪。 2004年3月10日,麻广军涉嫌妨害作证案在宁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内蒙古律师协会委派律师为被告人麻广军进行无罪辩护。 麻的辩护人认为,“证人在法庭上讲的是事实,而在庭审结束时由宁城县检察院和公安局带走证人去看守所讯问后又改变了在法庭上的证言,存在证词因环境因素而变化或者有刑讯逼供和诱供之嫌。”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江晓阳博士认为,导致麻广军被无端关押210天的,就是在律师圈内备受质疑的刑法第306条。 这个被律师们戏称为“306死亡条款”的刑法条文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于该条写法模糊,特别是对‘引诱’的界定不清,导致很多刑事辩护律师容易被扣上引诱作伪证的罪名。”江晓阳律师说,“在某些时候,辩护律师由于慷慨陈词得罪了检察官或者办案的警察,或者由于指出了警察和检察官的违法行为,威胁到警察和检察官的命运和利益的时候,律师就很容易被扣上伪证罪名。” 比如,昆明律师王一冰因涉嫌触犯“第306条”而历经两年牢狱之灾,二审法院却又宣告其无罪,最后这位律师愤而出家。 全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11个案件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错案率近50%。新刑法实施后,律师执业中涉及“伪造证据罪”、“妨害证据罪”的案件占全部律师维权案件总量的80%,仅2001年,全国就有几十名律师涉嫌律师伪证罪。 《法制日报》曾发表文章说,1997年-2002年间,至少有500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80%由司法机关“送进班房”,“绝大部分(占80%)又最终宣判无罪”。 正因为这柄利剑高悬,律师越来越不愿意做刑事辩护。北京律师朱勇辉坦言,在办案中,他们总是小心加小心,尽可能避免让警方和检察官找到报复的借口。还有律师称,在刑事辩护中,“能不取证就尽量不取证”。 第五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全国律协维权工作报告》披露,北京律师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数量已从10年前的2.64件下降到0.78件。而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则称,目前中国有70%以上事关被告人生死攸关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介入。 说到“死亡条款”,律师们都乐于提及“刑事辩护责任豁免权”。 1990年9月7日,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国际性法律文件《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该文件第20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 中国政府已经在该文件上签字。有鉴于此,人们呼吁,中国应该明确律师的刑事辩护责任豁免原则。 律师“三难” 一位资深律师说,对于办案的中国律师而言,再大的困难,都不如“三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 “会见难”,就是律师在接受委托后会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所遭遇的重重阻力。 “按照法律的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案子,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并经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以后,他就有权会见律师,”江晓阳律师告诉记者,但通常,“这些法律规定只是水中花,因为侦查机关根本不会让律师尽快见到犯罪嫌疑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兵博士解释说,显然,对于侦查机关而言,律师的及时介入可能成为侦查过程中的麻烦和绊脚石,因为嫌疑人获得了法律帮助,就可能对侦查方可能的违法侦查行为构成对抗和阻碍。更重要的是,律师的提前介入,还使辩护人可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从而对以后可能进行的公诉造成更大的麻烦。 为了加大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难度,公安机关层层出台规定,将会见“层层加严”。比如有的看守所要求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出具批准通知,有的检察院公安局则故意拖延安排会见时间。 《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规定相对于刑诉法修改之前律师在执业的任何环节都可以查阅案件全部材料的规定来说是一个倒退。 但即便如此,律师的阅卷权仍然被不合理地限制。例如最高检规定律师的阅卷、摘抄和复制应当先提出书面申请,且将可查阅的材料严格限定为程序性文书。 律师的工作离不开调查取证,但恰恰是这个问题束缚着律师们的手脚。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律师调查取证须经被调查人同意,这就意味着律师的取证随时因被调查人的拒绝而可能进行不下去。 对比之下,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和单位有义务向司法机关作证,这实质上使得本应处于平等地位的控辩双方信息获取权不对等。一些律师不得不采取违规行为。 收费之惑 在中国律师圈,关于收入问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非诉讼收费比诉讼收费高、经济民商事诉讼收费比刑事辩护高,而它们的风险程度则恰恰相反。 中国律师圈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在收费问题上,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以白条甚至不开任何收据的方式直接收取委托人的钱。一位律师解释说,这样做“一是规避税收,一是规避律所的提成”。 司法部胡占山处长说,由于有关方面至今未就律师收费监控问题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司法部一直没有制定详细的律师收费细则。 一个有趣的矛盾是,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律师属于“高收入群体”,而另一方面,多数律师又抱怨收费限制不合理,应当“完全放开”。 《中国律师》杂志总编辑刘桂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律师业每年的总收入应该在100亿元人民币以上。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曹树昌律师则说,据他所知,中国律师非诉讼业务收费的单宗最高额已经超过了1000万元人民币。司法部胡占山处长则以北京市为例说,北京市的律师人均年收入达到了30多万元人民币,而美国律师的年均收入只有7万-8万美元。 一位业内人士提醒说,人们不应当被这些巨额数字所迷惑,而应看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比如说,城乡律师的收入差距甚至比一般的城乡居民收入差更大。“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单宗案件的收费如果低于1万元,可能就很少有律师愿意接手了,而在偏远的农村,每件案子收费100元也是常事。” 这位人士还提醒说,律师的收入,相当部分被集中到了少数大所和名牌律师,而更多的律师可能还在为案源和生计发愁。 对于律师收入问题,田文昌律师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人们光是看到了律师收入高的表面,而有意无意忽略了律师的智力成本和其他高额成本,比如风险成本。“如果将这些成本充分考虑进去,你就会发现律师的收益率其实并不高。” 全国律师协会一位工作人员认为,寻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让律师的收费既体现工作性质、职责和价值,又不至于高得离谱,是管理者必须面临的问题。这也才能减少律师的腐败。 “为刘涌辩护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原主任,同时也是现任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如今深陷挫折感之中。因为对黑社会头目刘涌进行了辩护,田律师在互联网上遭受灭顶之灾。 许多网民的逻辑是:为刘涌这种“罪大恶极的坏家伙”辩护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为‘坏人’辩护就该骂吗?”田文昌哭笑不得。 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刑事诉讼法专家指出,对刘涌案件辩护律师的指责,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观念: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总把被告人和罪犯等同起来,在这种观念驱使下,律师为刑事被告人的辩护,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被接受。 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主任、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革分析说,这种逆反心理不只存在于不懂法的普通民众心里,甚至还存在于广大政府官员、司法人员心中。 田文昌的同事杨航远律师在5月8日再次碰到了尴尬的一幕。这天下午,接受指定法律援助的杨前往北京市昌平区某看守所会见一名在押的被告人,这个人因为杀人而被逮捕羁押审判。 在看守所值勤的警察一听说律师的来意,就对杨不屑地说:“你们这不是瞎挑事吗?他犯下这么大的事,难道你能让法院放了他不成?” 在反复解释后,杨律师总算让看守警察同意会见,不过麻烦接踵而至。按照当事人的要求,杨依法为其写了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状,但是,杨打算让上诉人签名的要求又一次遭到了阻拦,看守所警察和随后赶到的看守所长都表示,看守所从来不让律师为被告人写上诉状。 “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办案过程中司空见惯。”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另一名律师王天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一些地方,甚至检察官、法官都对律师尽力为被告人辩护取证的行为表示不解,在他们看来,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是给国家打击犯罪添乱。 王天槐律师认为,这样的认识和阻碍,从本质上看是对律师的歧视。 亟待解决定位问题 《中国律师》杂志总编辑刘桂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业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来源于一个因素──对中国律师的定位不准。 刘桂明说,20多年来,律师经历了多次定位的变化,至今无法真正落实其定位,“让律师成了‘四不是’”: ──不是官:律师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无法进入行政管理体系担任领导人。但实际上,律师应该是政府官员的最佳候选群体之一。以美国为例,至今为止的全部43位总统中,有31人具有法律教育背景,其中25人是律师出身。 ──不是师:“律师”一词出自佛教语,其原意是熟悉经律的导师。现代意义上的律师理应在传播法治理念、推动法治进步方面担当类似于“导师”的角色,但是,中国律师一方面由于整体水平不够,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评价不太高,难当此殊荣。 ──不是家:这里所称的“家”,包含专家和法律职业家两个层面的意思。律师应当学有所专,成为精通某一门或者某一类法律的专家,应当是专家性的社会工作者,不过,中国律师离这个水平还差得远。 ──不是“行”:律师首先是一个职业,然后才能形成行业。在这个行业里,大家遵守共同的规则和准则,平等地进入和退出。不过,中国目前实际缺乏律师行业环境。 “要解决当前面临的律师管理难题,当务之急,就是对律师进行准确定位。这个定位应有3个方面的含义,即政治角色定位、市场角色定位、社会角色定位。”刘桂明说。 改革关键在于“自治”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喜欢“从根本问题上宏观考虑中国的律师改革”,他认为,在“政治文明”的口号下,作为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律师制度需要得到重新审视。 贺教授认为,中国律师目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律师本应是独立的、自我主导的职业,这样才会形成足够的力量,但现实却是律师无法独立生存。另一方面,律师职业化程度不够高,使得这个群体不能形成一种同社会上其他权力抗衡与交涉的能力。 中国律师门槛较低,现在尽管有考试制度,但很多非法律专业的人员通过3个月的突击复习就可以考进来。贺教授透露,一些统计资料表明,全国10多万律师中真正受过良好规范法律教育的只有三分之一。 在他看来,中国律师还不大可能通过自己的专业化的知识来获得一种应有的专业化权力,以此赢得社会的尊重。 贺卫方的观点是,中国律师改革的关键在于解决律师的自治问题。他举例说,英国律师很早就形成了自治机制,因此,律师关心法律这个行业的发展,关注法律环境是否良好,他们为此争取更大的权利,即所有的法官都必须从律师中挑选。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律师还通过组织化的力量更多地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贺教授告诉记者,西方议会中,法律人占有很大比重。越来越多的法律人进入到政府部门,对国家行政权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滚动新闻 > 正文 |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