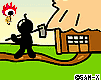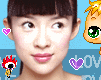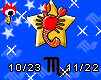| 第18章 印度工作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3月22日 20:24 中信出版社 | |||||||||
|
{米尔顿} 1955年夏天,当时担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阿瑟·伯恩斯,请我和尼尔·雅各比前往印度为印度政府做顾问,当时印度得到美国国际合作署(其实就是对外援助部门的名称)的资助。尼尔过去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当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商学院的院长。我从来没有去过印度,所以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我决定秋季学期离开大学,投入这份工作。
当时印度政府正在制定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受到苏联经验的影响)。印度政府请求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这一计划给予援助。美国政府意识到这是一个平衡左翼顾问影响的机会,决定派两个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去担任顾问。雅各比被直接派往计划委员会,而我则担任印度财政部长的顾问。 不管此事对印度的意义如何,我个人是极有收获的,尽管由于在芝加哥发生的不幸事件让这次经历美中不足—我被迫提前回国。我在10月8日,星期天离开洛杉矶[1]。 当时还没有喷气式客机,因此从洛杉矶到新德里是一次长途旅行,要在东京、香港和曼谷转机。我去东京乘坐的是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该机有两层,乘客层在上面,下面是行李层。这种飞机上有少数几个非常舒服的卧铺,美国政府考虑周到地为我提供了一个,而一位同机的乘客没有搞到卧铺,愿意出100美元(相当于1997年的600美元,或者如我在给罗斯的信中说的,相当于“睡1分钟10美分”)换我的卧铺。我抗拒了诱惑,安然入睡。去东京途中,我们在夏威夷停留,第二天早上到达威克岛,停留了1小时,吃了早餐,然后前往东京。总而言之,当时的空中旅行要比现在费时得多,但是比坐在当今人满为患的庞大飞机中愉快得多。 由于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少了一天,我星期一到达东京,住在原来的东京帝国饭店,这是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惟一幸存的大型建筑,它也因此而闻名于世。正如我给罗斯的信中所写的:“它有点让人失望。看上去非常像罗宾别墅的扩大版,但是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东西。内部很精致,但是总找不到路,你要转过来转过去。”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北村(Kitamuru)教授的陪同下逛了东京,去了歌舞伎剧院,北村是一位经济学家,我和他曾经通过信,头一天晚上在都留重人(Shigeto Tsuru)教授家里的晚宴上才第一次见到他,都留重人教授是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我将在第20章中讲到他们。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商店里的货物排列整齐、包装漂亮,街上的人群拥挤,再有就是贫困。我在信中写道:“贫困现象既引人注目又令人压抑,我真的不知道人们有多么穷,不知道穷人如何生活。”在后来的数十年中这一现象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加深印象,让我认定没有一个人们不能生存的最低收入水平。 按照今天的标准,即使考虑到在此期间发生的通货膨胀,价格仍然非常便宜。但是按照我当时的标准并不便宜。正如我写给罗斯的信中所说的:“饭店的房间很好,有私人浴室,但是价格并不便宜,相当于8~9美元。”我和北村教授在日式餐馆吃了一顿午餐,这在当时是一顿相当奢侈的饭,“大约每人3美元—当然是我付了两个人的餐费,而根据日本的礼节,我的日本朋友没有反对,这笔钱可能是他们一个星期的工资,因此我不能责怪他”。与饭店住房的费用比,这顿饭的费用似乎很高。在我重读写给罗斯的信时,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当时印象中的日本与今天对日本的印象之间的反差非常之大。40年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我当晚离开东京乘夜间航班前往香港,美国政府为我在半岛酒店订了一个房间,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饭店之一。我问了一下饭店职员我的房间的房费,当他说是50元时我大吃一惊。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他赶快告诉我这是港元。当时6港元可以兑换1美元—在高档的半岛饭店1个单间的房价大约是9美元。通货膨胀不能说明当时和现在的差别,差别是由于香港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输出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为了换机,我只能在香港停留一天,因此用来看风景,上午在九龙,下午在港岛。 第二天早上(星期四)我从香港飞往曼谷。虽然我的旅行安排中没有要求在曼谷停留,但是因为我所乘坐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航班要停曼谷,所以安排我乘坐第二天的航班去新德里。结果是“着陆时,我得知,星期五的航班推迟一天,星期六前不会有飞机,这让我更高兴,因为星期六夜间到和星期五夜间到是一样的”。 关于曼谷,我在给罗斯的信中写道: 这是一个肮脏、没有魅力的城市,到处点缀着真正美丽、还算保存完好的庙宇和政府建筑,但是这些点缀几乎不能使之显得好一些。它留给人最主要的印象是肮脏和拥挤。你走到哪里都是成堆的人。比你想像中多的商店和市场(我相信这里的店主比雇客还要多),每条街和每个肮脏的小胡同中都排满了这些小店……想像一下马克斯韦尔街,比它脏几倍再延长几倍,你就会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泰国人似乎非常快乐和有礼貌……游览水上市场是这里最有趣的活动。游览几乎都是在船上,先到河里,然后再到遍布这个城市的运河里。人们,或者说是非常多的人,生活、工作在河上。到处都是运河和河流,到处都会看到人们用小船运米,有些地方会看到大一些的船,他们生活在上面,或者用来运货,或者作为水上商店,或是用来供应食品。运河边上排列着房子或是棚子。我们下到河里时,看见许多人在河里洗澡,或是给孩子洗澡(这里到处都是孩子),或者是洗碟碗,或是洗衣服,或是浸泡正在染的布等等。这条河要向下游流500英里甚至更远,把这些垃圾废料带到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河水是褐色而又浑浊的……上午我们参观了庙宇和王室游艇。虽然印度一直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是宗教界和与之相关的东西都非常豪华。 我终于在星期天晚上到了新德里,这一天是10月15日,我离开洛杉矶正好一星期—实际旅途时间是4天,相比之下,现在取道新加坡的直达航班只需15小时。 “麦克莱兰夫妇到机场接我—麦克莱兰先生是我夏天在华盛顿认识的老熟人,当时他回国探家(他是驻印度技术合作使团公共服务处的经济顾问);麦克莱兰太太是很久以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学生,当时她叫安妮·弗里德曼,所以我清楚地记得她和她的名字。同时来接我的还有一个印度小伙子,莫汉·玛尔霍特拉,他曾经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们立即把我带到一个鸡尾酒会,估计是为了欢迎我。” 我在写给罗斯的信中总要不时地提到价格:“现在,至少是暂时,我住在大使饭店,一天11美金,包括餐费。我正在想办法弄到便宜的房间,我知道能够弄到,但是此刻他们说没有便宜房间。”在后来的信中我又报告说,我和尼尔·雅各比还是弄到了一个套间,“每人每天6美金,包括膳食”。 东京、香港、曼谷向我展示了可怕的贫困,但是印度的贫困要严重得多,即使是在新德里,虽然也像多数国家的首都一样,相对还是比较繁荣的,但是情况也很糟。最好的例子是老德里周边地区,人满为患,许多人住在街头,几乎所有的人都衣衫褴褛,剃头匠在路边耍手艺,牛车走在街道的中间,许多道路未经铺砌,乞丐比比皆是。正如我给罗斯的信中所写的:“人们衣衫褴褛已经让人震惊了,但是更让人震惊的是人们骨瘦如柴。”7年后,我和罗斯在加尔各答度过几天,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儿贫困有所减轻的迹象。正如一位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新德里办公室工作的同事所说的:“你可能能忍受一个1/4平方英里的贫民区,但是就像在加尔各答一样,当这些贫民区一平方英里一平方英里地延续下去,就无法忍受了。” 和大多数贫穷国家一样,普通群众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差别极为鲜明。在新德里,后者主要是由政府官员构成的,包括高级文官、外国政府及商业代表、少数成功的商人、地主等等。头一次来访的人会被上层社会的铁石心肠所震惊,但是很快就会明白,除非采取这种态度,否则富人就不能生存,要不然就像甘地那样与民众打成一片—可以理解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多。 在这种境况下,劳动力非常便宜,对劳动力的使用也就很浪费,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小例子是打网球(为了躲避炎热在清晨打),一场双打,有3个男孩捡球,“还有一个被称为‘记分员’的职业教练陪我们打。打完球后,我问带我来的朋友要不要给小费,他说,不,这都包括在每个月5美元的费用中了”。还是在给罗斯的信中我说:“你要是看到我走进在印度的办公室的情景,一定会笑得前仰后合。先是我的‘听差’从大厅跑过来,抢过我的包,提着包跟着我……每个办公室门口都有长板凳,坐着两个‘听差’,专为办公室里的人服务,看见我走过来,就站起来敬礼。这种景象非常可笑。我记得告诉过你我的门外有一个‘听差’,只要我一按铃他就跳起来!我一天只在这里待几个小时,这是多么大的人力浪费啊!” 美国国际合作署的官员和驻印大使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官员们非常投入,对印度存在的问题非常关心;这是一个有奉献精神的群体,他们的工作确实意义重大。”关于约翰·舍曼·库珀大使,我写道:“我和他在一起很愉快。他是一个能干、有效率、讨人喜欢的人。我们的政府干得不坏。” 同样,印度高水平文官的素质也给我留下了比预期更好的印象,尽管我坚决不同意他们所推行的某些政策。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前,英国人建立了印度文官制度,由所能吸纳的最有才干的印度人组成,并将这些人送到英国受训练。这是一个精英群体,几乎所有人都毕业于牛津大学或是剑桥大学,他们在人数上很少,但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与独立性。他们统治着这个地广人多的国家。我接触过的印度文官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有才干和最具奉献精神的文官群体。因为具有独立性,所以这些印度人又建立了印度行政管理官制度,这是一个人数更多、选择不太严格、训练不充分的群体,现在已经完全取代了印度文官制度。 我为之做顾问的财政部长C·D·德什穆赫(C.D.Deshmukh)是一位典型的印度文官,“他确实是一个聪明而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很平和而且善于倾听,有着敏锐的头脑而且很好相处”。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尼赫鲁是名誉主席)是P·C·玛哈兰诺比斯(P.C.Mahalanobis),一位知名数学家,印度统计研究所的所长。他是尼赫鲁在剑桥大学时的同学,既是尼赫鲁的朋友又是他的主要顾问。雅各比就是为计划委员会担任顾问。 我认为,数学家(无论他是纯数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或是统计学家)都倾向于主张推行中央计划经济。在印度时与玛哈兰诺比斯先生的密切接触强化了我的这一看法,并让我对这种现象有了一个解释。首先,数学问题不是对就是错,而“一流”数学家都会同意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第二,数学才能经常在年龄很小时就表现出来。结果,有着超常数学才能的人年轻时就得到重用,因此一般都很自信。当进入经济学领域时,他们继续相信所有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他们有能力找到答案。正如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所言:“当权者总是以为他能像摆弄棋盘上的棋子一样,得心应手地安排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中的各类成员;他没有考虑到的是:那些棋子自身没有运行规则,而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一个单独的人都有他自己的运行规则,与立法机构可能要强加于他的法律有所不同。”[2]在经济学领域内,经常是没有明确的“对”或“错”,这些答案只需由一个或另一个能胜任其职的经济学家认可。 我不想做个不称职的顾问。玛哈兰诺比斯确实是一个开明的人,他愿意倾听不同意见,愿意讨论和考虑这些意见。例如他虽然没有听从但是却认真考虑了我的一个建议—我建议印度拍卖供私人使用的外汇,而不是配给(虽然我认为拍卖只是取消外汇管制及制止通货膨胀的一个次好办法)。但是一到做出最后决定的关键时刻,他就选择计划委员会的决定而不是市场的要求。玛哈兰诺比斯并不特别反对市场经济,这可能是他第二年辞去财政部长职位去担任一个不太重要的大学资助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原因。 离开美国之前,我已经尽我所能地了解了印度的形势,其中包括印度经济学家对后来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评论,还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印度经济的大量数据,因此我到印度时并非一无所知。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和各部门的印度官员、美国技术合作使团的人员、美国使馆人员及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驻新德里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深入研究了财政部和计划委员会为我准备的数据;还参观了几个私人企业—正巧,其中有一个在阿格拉,我们得以同时参观了泰姬陵(“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建筑”)。这次是参观“那里的小型制鞋业,一个由政府管理的保守、落后的部门”,“同时也是一个更有希望和更让人受到鼓舞的村庄”。 3个星期结束时,我写了一份11页的备忘录,日期是1955年11月5日,标题是《对目前印度经济发展中问题的初步评论》。从下面列出的一些标题可以知道其中的内容: 1.目标 2.投资政策 a.过分强调资本-产出比率 b.在两个极端上强调投资政策而忽视了中间 c.在公共部门方面想要做得太多 d.对私人投资控制太严,形式过细 3.对私有企业的政策 a.保护低效率生产方法 b.特别照顾某些行业的企业而对其他企业严加限制 4.货币政策 a.政策不稳定 b.赤字财政 5.可用于公共部门的资源 6.外汇问题 a.外汇缺口 b.外汇管制 c.改变外汇管制 7.结论 我全文引结论如下: 如果这些评论主要集中于金融机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印度所面临的惟一的或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是因为,一方面,这是我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是现行政策中最可能改进的一个领域。 我个人认为,印度的基本问题是提高她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唤醒希望,打破僵化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引进灵活的机制,让人员流动,向所有阶级的人开放社会与经济阶梯。要让我这样的外来者对印度的未来充满了乐观与希望,觉得一切都在发展,而且将继续发展,觉得政府已经做了许多努力,而且这个好的开端正在为富于活力而又不断进步的经济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写下这个结论的40多年后来看,显然我当时的乐观至少是为时过早。但是过去几年中,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后世界范围出现的新形势已使印度开始更为重视市场经济与私有企业,开始放开对外贸易与投资。因此最终可能证明乐观是有道理的。让我们希望能如愿以偿。 我惟一知道的当时对我的备忘录的反应是《政治家》(The Statesman)(印度的一家主要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通货膨胀的影响》,副标题是《美国经济学家对赤字财政的看法》。这篇文章显然依据的是流传出来的备忘录,参考了我估算的可能避免通货膨胀的财政赤字极限。 政府组织了一个由专业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担任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顾问。到后不久,我在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首席顾问J·J·安贾里亚(J.J.Anjaria)举行的宴会上,见到了这个委员会18或19位委员中的8位。不巧的是我后来很熟的一位委员不在其中,他就是B·R·谢诺伊(B.R.Shenoy)教授,他是一位杰出而又无畏的人。委员会最后完成了一个包含不同意见的报告,不同意见是什诺伊提出的,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签字。依我所见,他的观点在雄辩与见解方面都远胜过报告的其他部分。不同意见与我的批评有许多重合,尽管是各自独立提出的,但是却比我的观点更得不到认可。一个美国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印度这样一个墨守成规的僵化社会中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与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采取不同立场,坚决捍卫市场经济与私营企业而不是支持政府计划经济。什诺伊继续表现出这种勇气。他绝对是一流经济学家,只要看出不妥就要指出。他后来成为朝圣山学会成员,我们和他很熟。他1978年去世。他的妻子是一位发表过诗作的诗人,他的女儿继承父志,既是经济学家又赞成发展自由私营企业,她已经移民澳大利亚。 虽然我最初准备待三个月,但是大约是在一个月后,我几乎是在一完成备忘录就离开了印度,因为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我在前面提到过。让罗斯来讲这个故事。 {罗斯}米尔顿去印度时有点儿犹豫,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人这么长时间。我出于同样的原因甚至比他更犹豫,但是最终我们认为这次经历对他非常有益,而且因为有孩子们在身边,时间会一晃就过去。除此之外,我和米尔顿还有一个用来为我做补偿的重要计划,等他的工作完成后,我们一起去旅行。 大学区的安全状况正在逐步恶化,但是我们并未亲历过任何暴力行为,在家里感觉非常安全。但是正所谓再好的计划也会出错,我们就是这样。米尔顿走了没多久,我遭遇了一生中最痛苦而难忘的经历。 一天晚上,我去实验学校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家里时,孩子们已在楼上睡了,我做了一些走前没做完的事,然后就睡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意识到有人在摇我的肩膀,接下来就像是在梦里,因为当时我处于半醒半睡状态。我只记得起一把枪、一张戴面罩的脸,还有一句话:“你的钱放在哪里?”我当时肯定是回答说:“在楼下书桌里。”因为我总是把自己的钱包放在那里。他说:“给我拿来。”我像机器人一样,下了床,走下楼梯。当时我穿着睡袍,光着脚,枪指着我,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到了楼下,我指着钱包说:“这就是。”他没有拿而是说了一句话,让我突然清醒过来,尖叫“不”。这时吓了一跳的人成了他。此前我一直很顺从而且合作,我突然的反应让他飞快地冲向开着门的厨房,他显然是想从这个门逃走,但是我肯定他没有料到我会有这样突然的反应。虽然我已从梦中惊醒,但是并不是真的清醒。我冲到前面的窗子,开始大喊米尔顿、阿伦和其他男人,包括我们的邻居迪克·迈耶斯。如果我是清醒的,我应该知道米尔顿在印度,阿伦在两个街区之外,都不可能听到我的喊声,但是迪克还没有睡觉,他听到了我的喊声,立刻就跑过来。我并不知道邻里之间有一种报警方式,因为经常有类似事情发生,都是在丈夫出国、只剩下妻子在家时出的事。几家邻居立刻来到街上,想要追上入侵者,但是没抓住。 而我自那夜以后就头昏眼花。有人通知了阿伦,他立刻就赶来,在我们家待了一夜。有人叫了警察,他们除了带来一条狗没有提出什么有用的建议。警察说,那个人是从窗子进来的,窗上的栏杆也没能阻止入侵者出去。我不可能再和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应该想些办法,但是我当时无能为力。我的表兄波林·莫斯利住在几个街区之外,第二天晚上他暂时把孩子带走,我住在阿伦家里。广播电台的警事报告栏目将此事通告了这一地区,同时新闻传到了芝加哥和华盛顿。我们的一个好友玛格丽特·里德去了华盛顿,她在那里见到了我们的朋友多萝西·布雷迪,她当时在华盛顿工作。这就是多萝西,她来不及和我联系,就坐上头一班飞机来到芝加哥,第二天就出现在我们家里。多萝西照料一切,直到我姐姐贝基从里诺赶来。与此同时,阿瑟·伯恩斯得知消息后,立刻打电话或是拍电报给米尔顿,让他回家。米尔顿确实缩短了访问日程,但是仍未能立刻赶回来。 {米尔顿}由于长途通信的困难,当时难以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曾经不断地给芝加哥打电话,但是打不通。最后我们求助于电报,这是惟一可行的快速联络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更早结束访问的原因。当我最终决定结束访问时,美国援助办公室和印度政府的人都表示同情和遗憾,他们还建议可以安排我明年春天再来(这个安排未能成功,我和罗斯7年后才再来印度,但没有正式任务)。 我没有任何关于返回的记录,不像我出去时那样有详细的记录。我只知道不是像出来时那样悠闲,我已经记不得是走欧洲航线还是从太平洋返回的。罗斯记得,天气原因使我搭乘的飞机不能在芝加哥降落,被迫改由另一个机场(也许是底特律)降落。 {罗斯}在米尔顿回来前,一直是姐姐陪着我,此外,厄尔·汉密尔顿和其他人一样对发生的事情非常不安,认为我们家里不能没有一个男人,他因此安排一位学生在米尔顿回来之前住在我们的空房间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这位学生(鲍勃·斯奈德)在米尔顿回来后搬进了三楼的一间房子里,一直住到离开芝加哥大学。不用说,只能取消去东方旅行的计划,因为我根本没有心思了。我当时真想离开这所房子,离开芝加哥。糟糕的是我不能这样做,直到夏天我们去了牛津,一学年后又去加利福尼亚待了一年。我应该感到幸运的是,米尔顿回到家里,此后我们再也没有长期分开过。 我所有的朋友对我当时的心理反应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几年内这一社区暴力犯罪案件急剧增多。我在身体上并没有受到伤害,伤害主要是心理上的。那时,强奸还是比较少见的,也很少公布这类案件[3]。遭遇暴力犯罪的个人和家庭的反应是相同的,但是我估计许多自己没有受害的人反应就不一样了。虽然女权主义运动已经使对强奸的判罪更容易了,但是性道德观念的变化也使强奸罪罪行减轻了。 {米尔顿}我1955年所写的备忘录没有发表,但是1957年我在《交锋》(Encounter)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4]。1989年夏威夷大学东方-西方中心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主题是“现代印度的政治经济”。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一位年轻的印度学者,名字叫苏博洛托·罗伊,他知道我写过一个备忘录,邀请我参加讨论会,并希望我能同意在与会者间传阅这份文件。会议的内容在1992年出版,因此我1955年的备忘录终于在它写成37年后出版!编者在评论时说: 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印度政府从英国和美国经济学家得到的所有建议中,米尔顿1955年所写的备忘录在内容上是独一无二的,而据作者与编者所知,实际上它却一直无人问津,从未发表过。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要创造条件使民众的收入与消费水平迅速提高,这在当时是从P·C·玛哈兰诺比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但是建议的手段却各不相同。玛哈兰诺比斯主张由国家发挥主要作用,强调实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的增长。弗里德曼认为国家的作用虽然必要但显然是有限的,应重视人力资本的大规模投资,鼓励国内竞争,实行稳定与可预见的货币增长政策、将卢比作为可兑换硬通货而实行弹性汇率制,这些措施将使印度在世界经济中有一席之地。现在已不可能说清如果40年前历史选择另一条道路,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当时能认真讨论这样一种选择,似乎会更容易确定国家在今天的印度如何发挥更恰当的作用,确定人力资本与实质资本之间的恰当比例。[5] 最后,我这次访问还有一个可笑的副作用,就是我长期要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出使印度负责。让加尔布雷思来讲这个故事: 我们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理查德·卡恩一起吃饭……另外一位客人是一位瘦高、眼睛深陷、自信的印度人,他就是P·C·玛哈兰诺比斯,当时62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是剑桥大学一流的物理学家……他现在是由政府资助但是相当独立的统计学研究所所长……玛哈兰诺比斯同时也是印度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委员,尼赫鲁是该委员会的主席,玛哈兰诺比斯是他的顾问、朋友与亲信…… 玛哈兰诺比斯那天晚上谈了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特别讲到他成功地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请了学者,到他的研究所商讨新的五年计划和印度发展的一般性问题。他已经向艾森豪威尔政府请求过帮助,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我对这个消息所做的反应是指出让弗里德曼为经济计划提建议就像让圣父参与商讨一个人工流产手术一样。玛哈兰诺比斯非常欣赏我的比喻,建议由我去印度担任顾问……我们同意明年初前往。[6] 据我所知,这是加尔布雷思头一次接触印度,从此他对这个国家产生了长久的兴趣。 注释 [1]因为我是独自前往,罗斯和孩子们留在芝加哥,所以这是一次留有最好文字记录的旅行之一:长时间乘飞机非常适宜写信。我到新德里后继续写了很多信。罗斯保存了我写的所有的信。可惜我没有把她的信保存下来。本章中引用的内容,除了特别指出的,都出自我写给罗斯的信。 [2]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first published in 1759;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69), pp.342-43. [3]据报道1957年的强奸案件是每100 000件中有8件,严重殴打案件是每100 000人中有65件;到1989年,相应的数字是38.1和383,大约是5倍。 [4] The Indian Alternative? Encounter 8, no. 1 (January 1957): pp. 71-73. [5] Subroto Roy and William E. James (eds.), Foundations of IndianPolitical Economy (New Delhi, Newbury Park, a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p. 19-20 . [6]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81), pp. 323-24.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滚动新闻 > 正文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