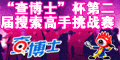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黄宇
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包括:国情与增长、农村产权问题、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农村政治体制与税费改革、农业的稳定性等问题。曾经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等中央五单位联合颁发的“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
毫无疑问,温铁军得以进入公众的视野是因为当选了2003年度的CCTV十大经济人物,进入第三年转而以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为主力的央视经济人物评选,且不论它招致的关于格调和品位的质疑,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转向鲜活而有实力的经济实体,是这岁末年终林林总总举不胜举的人物评选活动更为现实而可行的选择,即便是CCTV也不能例外。
但无论如何,温铁军的学者身份,尤其是一个“三农”问题研究学者的身份,他的入围和当选总还是有些突兀而引人注目的。令人忍不住想要追问的是,在进入公众的视野之前,他是如何得以进入CCTV的视野。
以学者的身份
把“中国研究‘三农’问题最权威专家”的帽子戴在温铁军的头上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了,但要说“之一”便毫不夸张了。应该承认,在学术领域和温铁军处于同样高度的研究者总还是有的,但学术的水准和优劣高下难以准确地度量和比较,较之于学术的个性品格,学者的个性人格真实可感且容易突显得多。温铁军取胜的无疑是后者。
在很多场合温铁军被形容和赞许成一个“用脚做学问”的学者,这容易让人误解是对“用脑做学问”的某种颠覆,甚至对碌碌于书斋殚精竭虑的学究们的某种嘲讽,事实上,温铁军一直在努力试图消除这种误解,对于“做学问”一词因人而异的界定,媒体、公众、温铁军本人以及像温铁军一样的经济学者,都是难以评说或被评说的。
温铁军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调研员或实验者,在CCTV的颁奖典礼上他有过类似的表述,不过吴敬琏老先生周到而巧妙地化解了他的自谦。温铁军的注重实际,既是研究领域决定,似乎也和他的专业不无关系。从1985年到1991年,温铁军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学习统计和调研分析方面的东西,也许这段经历让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他那时未必知道自己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声音。
除此之外,想要探寻出温铁军对农民及农村问题热情的来源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说是他17岁起长达11年的插队生涯培养起来的“亲民”感情未免有些牵强,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的是更多人因此急于脱离和与农村划清界限,或至多不过是小心翼翼怀旧般的缅怀。温铁军读新闻系,参加世界银行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课题和培训,学会的是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三农”问题,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超乎寻常的理解。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的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似乎9亿农民的无语追问透过一个羸弱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呐喊,便有了穿越电子机械和光影数码层层壁障的力量,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吴敬琏说,“中国的农民不容易,9亿中国农民就像是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温铁军说,“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看病和告状。”于是吴敬琏又说,“温铁军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因为肯为农民说话,求告无门而找温铁军解决问题的人之多可想而知,让我们得出这一印象的是电视荧屏中那些挥舞的手臂,他们写信,递条子,或不远千里去找温铁军北京体改研究会的办公室。
这些问题不知道温铁军能解决多少,又解决了多少,这毕竟不是振臂一呼那么简单,后者只需要勇气和正义而已。温铁军曾说起一段自己在川西某贫困村扶持一个农民养猪互助组织的经历:一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且规模非常小的农民互助合作经济组织,在它稍有起色时,当地各个部门的人员纷纷找上门来了,有要收费的,有要求办证的,有要求取缔的……几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吓坏了,他们只好写信向温铁军求助。
得知此情况后,温铁军说,自己本可以给四川省的有关负责人写信解决此问题,但他考虑到这种从上往下压的办法只能一时奏效。过后,各种麻烦可能还会降临到那些农民身上。于是,他决定“委曲求全”,亲自给当地县、乡、村三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写信,解释这个互助组织的作用、意义,并在信末特别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是支持的!此举果然奏效,该互助组织至今仍安然无恙。这是温铁军颇感得意的一笔。
做农民的代言人,这和学问无关,而和责任有关;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建设,这也和学问无关,而与体制有关。温铁军是清醒的,他说,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是温铁军切切实实用脚做出来的学问,又是温铁军用脚改变不了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温铁军在获奖感言中说的,也许不仅仅是自谦而已。
以晏阳初的名义
不知道能不能把温铁军的横空出世看成“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另一种形式的登场。虽然恐怕此前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偏居河北定州市翟城村一隅的、以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名字命名的乡村建设学院,但事实上,温铁军出任这所学院的院长,较之于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甚至“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头衔,对于其作为一个经济人物人格魅力的彰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意义。
尽管晏阳初已经从很多人的记忆中淡出,尽管一度闻名世界的“定县实验”的十年一页已被翻了过去,尽管翟城今天只是中国千万个乡镇当中普通得让人没有理由知道或记住的当中的一个,但是,当一段历史的脉络被重新梳理出来,温铁军和他的乡村建设学院,俨然有了某种民族英雄般的光彩。
对关心中国农民及农村问题的人来说,这应该是难以忽略的一页。1926年,以晏阳初为干事长的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址定县为实验区,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平民教育实验工作,遗风犹存,口碑尚在。晏阳初针对中国“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提出的“四大教育”,即识字(文艺、文化)教育、生计(生产)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及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数十年来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赵元任、俞平伯、张学良、斯诺等著名人士,定县因此成为闻名世界的乡村建设实验区。
1977年后,温铁军选择在定县实验的旧址重开乡村建设学院,继承晏氏遗风的心愿不言而喻。温铁军原本就是坚定的实验主义者,他说,“不做实验你怎么知道哪个观点是对的?不做实验你又怎么知道哪个观点能够符合中国国情?”温铁军深信实验的结果既是做学问的必须,也毫不怀疑实验的过程对一乡一地一人一户的点滴改变。
因为这也许是温铁军也料想不到的事实:今日的翟城村见过晏阳初的人也已寥寥,村支书米金水却能执着支持着把乡村建设学院复兴起来。2003年2月,米金水征集了村民意见后,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集资40万元买下当年平教会农业实验场旧址,竖起晏阳初的塑像,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温铁军决意并相信自己能够主导这个乡村建设学院的改革实验方向。
在学院的招生简章中,温铁军说,“有机农业本来就是中国农民的传统,不必追求高价的现代能源,别种‘卫生地’,少使用农药化肥。在乡村建设学院的培训中心,鸡鸭牛羊都养,还要种上蔬菜、果树,要充分利用沼气,形成生态循环,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样板。”
这是温铁军一贯的观点,他向来以为,对一个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加快城市化建设的后果,首先是生态环境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即使实现了55%以上的城市化率,届时中国仍会有7亿至8亿人生活在农村。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再高,也不会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
现实的办法是,帮助农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体办法,把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用于改变家庭和村社的面貌。通过劳动力的合作,把人力资源转变为社会资本,温铁军同样将在乡村建设学院进行农村社区的实验。
看温铁军为乡村建设学院设置的课程:农民学、农村学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理论;政治经济学常识与农村(农业)合作社教程;可持续生计/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历史及国外乡村建设与另类经济的理论及实践;现代科学发展概要、文化艺术常识;参与式农村工作方法、传播与沟通;社会心理学与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的社会心理现象,等等。这不是定县实验的简单复制。
温铁军的培养对象,是来自全国各地具有建设乡村、改变乡村面貌的理想,同时认同乡建理念的城乡居民、农民带头人(维权、致富、普法等)、乡村医生、农技人员、基层农村干部、志愿为乡村社区服务的青年志愿者,这和晏阳初的治愚、治穷、治弱、治私,也不可同日而语。
1985年9月,旅居海外多年的晏阳初重回定州。耳闻目睹现实情景,老人感慨万千地说,“中国农村建设的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好的制度。”一所乡村建设学院将晏阳初和温铁军联系在了一起,但他们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温铁军今天可以说真正为一种乡村建设制度的开拓进行有益的探索。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一场广泛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1月09日 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