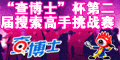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仲伟志/文
那些令人晕眩的崇山峻岭
最大的力量就是使我们学会沉默。
而两年来更多的这样的旅行
使我逐渐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
在中国奇迹造就的新一代浪漫主义者的包围中,
我的悲观似乎不合时宜
2001年春天的风暴曾经使我们绝望。但风暴过后,我们很快淡忘了它,就像水分在到达植物的根部之前,迅速被高温蒸发掉了。我们不愿承认我们的21世纪是在沙尘暴中开始的。我们中的很多人更是拒绝承认他们在这次灾难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不愿去强调自然机能的相互依赖性,因为我们有着比环境限制更重要的经济目标。
2001年10月,从贵州的镇宁、关岭、晴隆,再到四川大凉山的西昌、喜德和普格,我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穿行了半月,初衷是考察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些地方推行的人居工程以及小额信贷项目。为了让他们学会用小额贷款经营生计,为了把那些在数千米高山上生活的彝族人搬迁到山下,慈善机构和地方政府费尽口舌与心机。晴隆县的布依族县长带着我们翻山越岭去回收贷款,县长的诚实敬业和穷人的恪守信用,让跟在后面的我们唏嘘感叹。
有关方面期待这些扶贫项目能够改变这些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按照惯例我应该就此写一篇报道,通过事实告诉大家,少数民族也可以做到吃苦耐劳,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批评的那样“自我满足、自我封闭、因循守旧”,如果有足够的机会和条件,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创业和生活,参与商品市场的竞争。那几个县的县长一直等着我的报道出来。但我一直没有写。因为我感觉到,这些结论只是来自我们固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一种所谓的“客位文化量度”。因为在高山大川之中,我看到有更多的人坚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自以为是幸福的——如果他们认为目前乐天安贫的生活状态是幸福的、合情合理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改变呢?
对自然的崇拜与敬重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这种可以称得上是信仰的风俗,倒是具有生态意义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傣族人就居住在森林内外,但家家还要另辟薪炭林,不能砍一棵野生树木。如果按照某些学者所呼吁的那样建立绿色GDP,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时候把生态环境成本计算在内,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并不低,而有些高速增长的所谓发达地区,说不定还是负数。
改变一种生存模式的成本极其高昂,从全人类的层面来说,还有可能是得不偿失。因为你付出的不只是一些扶贫与开发资金,还会导致新一轮对资源的强烈渴求与攫取。我们希望用开发带动消费,用消费带动增长,因为增长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进步。但是,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在更广大的西部,追求这种意义上的增长就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透支,舍此别无他路,这已经为诸多事实所证实。那么,谁能够为如此进步的残酷代价买单?
常常提着行李生活事实是一种自由,但2001年10月的旅行使我感到痛苦。那些令人晕眩的崇山峻岭最大的力量就是使我们学会沉默。而两年来更多的这样的旅行使我逐渐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在中国奇迹造就的新一代浪漫主义者的包围中,我的悲观似乎不合时宜。
但是我的确看到,许多关于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能够协调发展的美好假设正在一个个破灭。河西走廊的城市化如火如荼,自然成为必须出卖的资本。地下深井给新一带农业产业经营者带来了巨大利润,公共福利高于私人利益的土地利用原则有可能被视为发展的阻力。红色沙漠边缘的土地正在散发着用国际贷款买来的化肥和杀虫剂的气味。庞大的矿业社会继续榨取着脆弱的边际土地,钢铁机械根本不知道对自然的使用应该从敬畏开始。
结果会是什么呢?我们谁也不愿看到,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能像1930年代的美国一样,成千上万人辛辛苦苦埋设的输油管道被挪用来向西部送水。但如果我们的扩张始终无视自然的限制,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国家“购买”的就将是一个个巨大的荒漠。
我坚持认为,只有当我们重新确定社会发展模式的评估标准,不再用社会发展阶段论来指责或埋怨少数民族的“落后”与“愚昧”,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规划才具有了操作的可能,西部大开发才有可能摆脱误区和歧路。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的治理模式和组织结构使西部地区走向进步。
有人认为,将环境危害上升为“亚政治”有可能伤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可能影响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效率。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说,无限期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可能的——就像其它商品一样,如果任何资源逐渐变得稀缺,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上升,它的消费量就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供大于求。他们甚至认为,全球变暖是一种并非由人类活动带来的自然现象,自然所拥有的自我复制能力远远超过了人类对环境可能施加的任何影响。
够了吧——我不是极端的环境主义者,我深深知道我们的国家必须沿着持续繁荣的道路开拓前行,我们的人民不能总是依靠调节自己的欲望来适应这个自然世界——但是,我仍然反对这种布尔乔亚式的盲目乐观。
同样是在2001年,大同成为一座被传闻笼罩的城市——据说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大同整座城市将搬迁到新疆,从而为城市地下的优质动力煤的开采让路。这样的传闻使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在一座丧失了未来的城市里,人们纵情快乐,得过且过,不再做长远的打算。在弥漫的疏离气息与莫名兴奋的人群中,贾樟柯很快拍完了《任逍遥》。这部没有完整剧本的电影,讲述了一群失业工人子弟的生活。在山西人贾樟柯的镜头中,大同是一座悲观的城市。
那一年我和我的同事张梦颖在大同采访。我们看到了更多在电影之外的大同无业青年。即便他们的头发直立着,并染成了金黄色,也掩饰不住那种渗入到血液中的落寞与脆弱。他们无所适从。
贾樟柯似乎比我更加悲观。他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要鼓励人们悲观,它能让人们慢慢理性。——或许对于有些人来说,最深刻的悲观是真正力量的源泉,而乐观主义者往往是那些愿意被人利用和操纵的人。但是,悲观一定能够带来理性吗?理性就一定拥有未来吗?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擅长区域经济报道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