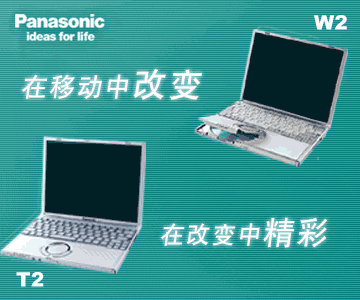|
[周末会客厅]
2001年7月的一天,一本《财经》杂志改变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和方向
本报记者 张刚
前年7月的中国之行,为陈志武开启了一道门。
这位在全球享有盛名的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此前并不太关心中国经济,虽然1986年之前他在中国生活了多年。
“启蒙”的是当年7月的《财经》杂志,陈志武至今还对那本杂志上的多篇文章记忆深刻。此后,他先后在中国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两所学府——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及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做特聘教授;良好的平台,为他研究中国经济夯实了底座。
做人、做事、做文章、做学问,如今,陈志武在每个方面都留给人们近乎完美的印象,也为他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聚拢了“人气”。
偶然机缘80%精力转向中国
从1986年到2001年的15年间,陈志武每年至少有50周的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他潜心研习着美国主流金融学,并关注着美国市场的细微变化。
惊叹于英文之美的他,还在闲暇的片刻,翻看英文版的《茶花女》或者《大卫·科波菲尔》,尤其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更是深深打动了他。
《财经时报》:你为什么在2001年7月以前不太关心中国经济?是什么改变了你?
陈志武:1992年前后,作为留学生,我也订过国内的报纸,一看,哎呀,太痛苦了,没办法读下去。再加上当时首先考虑的是要把饭碗稳住,没有太多心思回国参加各种活动,特别是,还要为终身教授做努力。我是199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被评为终身教授的,1999年被挖到耶鲁大学时,首先承认了这个称号。
2001年7月15日,我从上海坐飞机到纽约,临上飞机买了本《财经》。当时一看,大吃一惊,感觉写得都很实在,没有那些官样文章的气息,很像美国的《商业周刊》,我想,这个变化真大啊!我现在还能记得杂志里的很多文章。因为我是做研究的,当时感觉有很多数据其实可以搜集起来。从上海到纽约,飞机飞了14个小时,我就看了14个小时,把杂志从头到尾全部看完了,感觉启发真的很大。
2001年7月15日,对我来说可以说记忆很深,因为这一天,使我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回到美国后,我把以前的研究放到了一边,开始把80%的精力转向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财经时报》:如今,经常能在国内报刊上读到你评说中国经济的文章,你还记得第一次写文章的情况吗?
陈志武:2001年12月,我应约为《新财富》写了第一篇文章。在那之前,从1986年到2001年15年间,我没有写过一篇中文的文章。当时写得非常辛苦,因为在美国呆得很久,我还记住的中文更多的是日常词汇。其实你看我的文章,一般没有用成语,因为都忘记了,我也知道,用成语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看了很多书想补过来,并搜集、整理了很多资料,而且,我以前写得更多的是学术文章,发在美国学报上的学术文章,光审稿就要两年时间,一般是我把文章写好给他们,他们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修改、再沟通。这篇文章,我也按照以前的习惯,认为需要很长时间,至少有几个来回的,但没想到,不久就发表了。
《财经时报》:你的文章很多是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分析。身在美国的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了解国内证券市场的信息?
陈志武:信息的来源,很多是中国报刊杂志的网站,还有深交所等的网站。我的感觉是,在北京,除了可以直接到书报亭买到杂志报刊外,其他跟在美国没有太大差别,因为同样的内容都可以在网络上查询得到。
海龟?土鳖?参照美国看中国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的排名是第202位,他的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如今,陈志武充分利用了他渊博的学识,紧紧把脉中国经济。
《财经时报》:你对国内证券市场进行分析时,更多的参照是不是美国?有人可能会这样想,“中国的国情是否跟美国一样?有无可比性?”你怎样认为?
陈志武:确实像你说的,我在研究中国证券市场时,参照物肯定是美国,还有其他发达国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国情不一样,不具有可比性。表面上看,这样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像我们这些职业做研究的人,都会尽量用分析的眼光来看;我分析之后发现,除了表面上的美国特色、中国特色之外,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我们首先的出发点就是,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等,在本质上都一样。
《财经时报》:有人认为你是“海龟(归)派”?
陈志武:中国是有“海龟(归)派”和“土鳖派”的说法,我觉得这个总结太概括了,相当于给每个人一个标签,用这些绝对的标准来看待不同的人群。对“海龟(归)派”,用绝对好的标准,如果一个不好,就放大说所有的“海龟(归)”都不好;但对“土鳖派”,却用相对宽松的标准,有一个好就说全部都好。我不太赞同这样的区分。
《财经时报》:近年来,中国股市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揭黑热潮”,你印象最深的几个案例是什么?以“银广夏”与“安然事件”为例,它们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陈志武:我对银广夏的记忆最深刻,还有蓝田、亿安科技等。
银广夏和安然事件的发生,肯定是必然的。只要“宽松的制度环境”存在,媒体和司法制度继续受到限制,对于违规者、作假者,肯定没办法处罚。这样,即使是一个笨蛋,也会知道作假,因为他们作假首先不太容易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会被处罚,很多时候就是警告;就算处罚了也不会处罚到他们个人头上;还有,处罚的钱,可能也是股东们的钱。这样,“纵容保护违法者”的环境,简直造就了“违法者的天堂”,不作假才奇怪!
诚信失灵造就“背离现象”
2002年,陈志武在清华大学附近发现了“万圣书园”。在这里,他发现了一批非常好的历史、社会书籍,有助于他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于是,他迅速成为常客。
通过大量的研究,他发现,中国千年的“乡土诚信”正经历着异常的考验。
《财经时报》:中国的宏观经济最近几年表现非常好,但很多人搞不懂,为什么股市却好不起来?
陈志武:这其实也跟中国股市没有足够的诚信、没有足够的权益保护有关,如果有了这些,股市才会上涨、才会好。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是:你可以看看,现在有多少人会把大把的钱借给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很多人可能不会乐意,因为钱很可能会“打了水漂”,最后收不回来。
按照这个简单的道理,投资者为什么乐意把大笔的钱通过买股票的方式,委托给自己从未见过甚至一辈子都不会见到的陌生人?相比亲戚和朋友,他们更没有信任和了解的基础;虽然上市公司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人们还是没办法相信它。
中国经济与股市,两者是脱节的,如果两者不偏离,我倒觉得奇怪了!那样,投资者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权益会不会得到保障,会不会有风险,大家盲目地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很好的表现投资,这反而不正常。
《财经时报》:所以,你最近一直对诚信问题比较关注;你觉得,中国人有没有不讲诚信的传统?
陈志武:以前,中国人特别注重诚信,中国的“乡土诚信”也延续了数千年,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一辈子就生活在一个村镇里。之所以在诚信上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不讲诚信了,其实,我更觉得这是因为相应的社会制约机制没有跟上,而现在的中国人或许跟过去的中国人并没有多大本质差别。
主要原因还是在全国经济向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跨地区交易往来增加的同时,相应的制约机制没有跟上,才使得人无所适从、无所顾忌,有了空子可钻。“诚信”和“不诚信”是人的一种行为选择,而不是人的本性。
《财经时报》:重建诚信,政府、企业及个人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陈志武:在中国,一谈到诚信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应该做什么,实际上,通过政府一家来做,是不会成功的,即使再加上企业配合,也不会成功。
最近,有人呼吁成立全国性的诚信数据库,我觉得真是这样的话,如果不让媒体发挥作用,成功可能性还是不大;因为如果没有独立第三方介入,这个数据库的信息本身就会有问题。比如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法律法规要求上市公司真实地披露信息,因为没有第三方的印证,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可信度。这样的思路,本身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对于企业和个人,更多的需要市场来调剂,前提当然是资信环境、媒体监督和司法环境充分地发挥作用,这样,那些企业和个人才会在乎自己的未来,才会注重诚信。
保护?约束?立法思路应商榷
被中国人熟悉之后,陈志武也成为一些立法研讨会的座上宾。但这位睿智的学者发现,部分立法其实在思路上即存有问题。
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提出解决之道,陈志武正在实现着自己的转型。
《财经时报》:你特别注重媒体对中国经济的监管作用,但媒体也可能会“被利益集团操纵”,财经媒体因“揭黑”而被起诉的事情也频频发生,这些应该怎样有效地解决?
陈志武:在中国整体诚信状况不高、职业道德不高的情况下,不能指望媒体会是“模范”;可以说,整体环境决定了媒体的现状。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中国的法院在办理新闻侵权诉讼时,有采纳判例的倾向。很多法官还是很认真谨慎的,想通过法理来为其判决提供足够的依据,他们会参照许多的案例。
《财经时报》:你曾经提出证券诉讼实行“判例法”以及集体诉讼制度,那么,通过立法解决这些是不是更好?
陈志武:我参加过很多立法研讨会,发现很多立法者习惯性的思维就是约束某个行业,有些立法甚至每一条都是约束性的,限制了很多权利,而没有从保护和赋予权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的立法思路,其实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不能否认,很多的立法出发点是很好的,但立法后,却是偏离的,有些甚至与初衷有180度的大偏离。
而在美国,立法会更多地强调保护某个行业,更多地确认权利。所以,美国的立法很多是中性的。
《财经时报》:据说,你有打算“从纯学术研究的职业生涯转入第二个职业,即转入中国问题、法律问题的研究”,如今你是不是已经转型了?
陈志武:我现在可以说转型已经成功了,经过两年多努力,我重新进入了一些领域,对这些领域进行了很多了解和研究。
□陈志武其人
他是全球著名经济学家,更是一个随和、热情、有思想、有良知的人。
他生长于湖南农村。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
如果没有在1986年之前通过《自由选择》那本书了解哈耶克的经济理论,他的前程或许会另当别论。最终,他放弃了攻读了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在,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