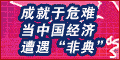| 农村与农民工之一:谁在返乡路上?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19日 18:30 《财经》杂志 | ||
|
同一社会环境下生活的人都是“利益相关者”,城市人或当地人独享利益是不可能持久的 谭深/文 为何返乡 在SARS高发地区,出现了返乡潮,其潮流的主体之一是农民工。与春运对公共交通和输入地的压力不同,这次不寻常的返乡潮直接威胁的是脆弱的农村公共卫生现状,因而引发了各地政府的非常措施和人们对农村健康问题的特别关注。 据最新数字,广东、山西、北京的民工SARS患者分别占当地SARS患者总数的10.2%、6.7%、6.2%。北京民工SARS患者所占比例次于医务人员、干部职员、离退休人员和大中小学生,居第4位。之前,笔者曾做过一些零星的调查,结论是:由于SARS病毒的特殊传播方式,它袭击的首要目标是那些在有中央空调的“大楼里”工作的人群和为患者治病的医务人员,农民工大多不会在封闭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感染机会相对要少。然而,他们集中居住的方式和卫生条件的匮乏,使他们一旦染病就可能发生群体感染。现在的数字虽不能详尽说明哪些职业的农民工最容易染病,但已经可以看出情况的严重性。另外,急于返乡的农民工作为农村的传染源,被各地围追堵截,又造成了新的问题。 在疫情高发时期,采取隔离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措施,但与此同时,有必要将农民工返乡与他们在务工地的健康状况和总体状况联系起来作一反思。 稍加分析即可看出,民工返乡的原因和大学生不尽相同,他们不完全出自对SARS的恐慌。特别是在早期,很多人并不知SARS为何物,如一位被拦截在广东的洛阳农村打工者,只知道自己得了“很重的病”。生病,而且是在务工地无法应付的重病,就要返乡。这是历来农村外出打工者的策略,也是无奈之举。 生病对于在外打工的农村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他们在生病期间没有了收入,有些雇主和工厂还规定病假要扣工资。其次,看病需要花钱,在现有情况下,农民工是没有医疗保险的,大病小病都要自己负担,而农民工的收入分配中,除了必要的开支,一般都寄回了家乡,很少为意外的伤病预留。据媒体报道,在政府对SARS患者“免费治疗”的政策出台之前,有的民工因经济困难,被送进医院后闹着要出院;还有的交了住院押金之后,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如果是一般的病,农民工依仗年轻,往往随便吃些药就抗过去了;病情稍重一点,朝亲友借钱;倘若不幸遇到重病,基本上就是走投无路。 而更大的威胁是,因伤病而被解雇,沦为失业者。换句话说,生了病就不能工作,不能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不能治病,甚至连居住和基本的生活费用也没有。这就是农民工的经验。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怪圈的农民工,除了返乡,还能怎么办呢?农民工在外最恐惧的,就是生病和失业,二者具备其一,农民工就失去了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基础。因此,就不难理解农民工对传染病比一般市民更加恐慌。 但是,绝大多数农村外出务工者并没有在疫情期间回乡的打算。因为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也没有感受到病魔的威胁。健康而有工作,这是农民工稳定的基本条件。对农村人外出和回流的调查显示,事实上在劳动力大量外出的农村,在外挣钱是年轻人有能力的表现,如果不是回乡创业或特殊原因(如生育、双抢)而返回,往往被看作失败者。因此,年轻人不会轻易选择返乡。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那些急于返乡的民工,由于生病(不一定是SARS)、失业或经营亏本而造成的经济困难是多数;其中也不排除对传染病的恐慌和可能遭受强制措施的恐惧。 中央和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近日接连出台针对性政策:医疗费用方面从实行救助性的方式到全部免费;劳动用工方面规定不得解雇转移或遣送农民工,治疗或隔离期间工资照发。这对于在非常时期控制疫情、保护农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北京和广东对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建筑工地和工厂还采取了改善生活条件和隔离的办法,都不失为有效的应对措施。 以上措施主要是针对成建制的或是在正规单位工作的农民工,但是对那些散工或自营者,作用就比较有限。据统计专家分析,中国流动人口中自营劳动者占1/3强,在私营、个体中就业的占1/5,两者相加占到流动就业者的一半还多。这部分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往往更差,工作更不稳定,从管理角度来说也更困难。以往的经验是加强出租屋和市场的管理,但那主要是惩罚而不是服务,很难达到使流动人口安下心来减少流动的目的。如果务工地和输出地动辄采用强制堵截措施,而不能体察民工的实际困难,可能会无意中加剧原本已经存在的社会紧张。 在健康边缘 近年来,关于外出农民工安全和健康的事故不时见诸媒体,触目惊心。总结起来有这样一些问题:职业安全(比如频频发生的矿难、工伤事故、工作或居住场所的火灾、化学品中毒等职业病,以及失业等),人身和财产安全(比如春运高潮中的交通事故、平时的交通事故、被杀、被打、被拐、被收容、被抢、被偷、被强奸、失踪,等),生活中的安全与健康(如食物中毒、一般疾病、重病、传染病、人工流产,以及身上没有一点钱等),精神健康(如一般心理疾患、精神病、自杀等)。几乎可以肯定,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上述安全和健康的事故的发生率,要高于稳定的人群。而其中除少量事情外,任何一个事故发生,都可能导致农民工命运的逆转,滑向弱势群体的最边缘部分。 近几年笔者在对农村外出务工者的研究中,开始比较多地关注到类似问题,曾分别参与或组织过对全国和广东的调查,其中全国的样本(299人)包括农村在外打工者或有过打工经历但已经回乡者,广东的样本(595人)全部是外来工;清华大学李强教授也对北京农民工(307人)进行了连续几年的调查。当这些调查询问到打工期间的健康经历时,结果如下(%): 以上的数据没有包括那些在意外事故中丧生的数字,否则比例会更高。此外,尽管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件,农民工一般的安全健康状况也令人不容乐观。我们的调查也涉及到类似问题:当问到工作场所有无有害健康的情况时,广东的外来工中有11%的人认为“严重”,45.7%的人认为“轻微”;而问到每天下班以后的感觉,有近一半的人回答“非常疲劳”和“比较疲劳”;另外有9.2%的人出现过工作时晕倒,27.4%出现过精神极度紧张的情况。 对于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唯一可用的资源就是打工收入或者亲友的帮助(也是要偿还的)。那么,他们的收入情况如何呢?广东的调查显示,调查前半年月平均收入(如有包吃包住全部计算在内)的中位数是700元;其中500元以下的占1/4,1000元以上的占1/5;在调查的前一个月被扣除的各种费用的中位数120元,也就是说,每个外来工每月可支配的收入平均在600元左右。但这是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在广东的调查和李强教授在北京的调查都显示,有1/3的农民工曾经遭遇过“身上没有一点钱”的情况,“失业一个月以上”的情况更加普遍,广东调查中有1/3,而北京调查达到100%。 许多在外的农民工年轻力壮时,没有为可能的伤病做什么准备,生病或其他事故这样的意外支出,他们会尽可能减少。广东调查显示,在外期间,农民工用于个人医疗费的平均数是835元,中位数是200元。其中1/3的人仅用了100元以下,10%的人用了1000元以上;北京调查看病的人均支出是891元,其中100元以下的有1/4,近20%的人用了1000元以上。按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如果得了比较重的病,单是住院的押金也难以承受。因此,健康的支出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它不仅使农民工外出辛苦挣的钱付诸东流,还可能欠下沉重的债务,使家庭经济难以翻身。难怪我们访谈中农民工说,“生病就像塌了天”。 农民工公共卫生系统如何建立 SARS的冲击,使得建立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共健康系统变得异常紧迫。据说,为加快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基础设施建设,国务院决定加大专项资金投入,支持中西部地区,并要求东部地区安排自有财力建设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公共卫生专家也在着手进行“中国农村互助医疗保险”试点研究,探讨重建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的可行路径。由于中国城乡、东西部的事实差距,专家们又提出分而治之的思路。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农民工是连接城乡的一个人群。从农民工与家乡社会割不断的联系来看,他们的卫生和健康似乎应考虑在农村公共卫生系统之中;但他们的主要工作生活又是在城市或其他地区,他们的健康状况与当地整体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按照现有的制度,农民工安全和健康的成本,最终是由本人、家庭和输出地社会所承担的。但是SARS的流行给了我们严重的教训:其一,同一社会环境下生活的人都是“利益相关者”,城市人或当地人独享利益是不可能持久的;其二,农村再也负担不起由于城市和部分地区发展的代价了。保卫农村,就不能不保护农村的有生力量——那些为农村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年轻的打工者。 当然,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是一个太大的话题。这里只就农民工的安全健康系统的建立提一点思路。首先,笔者认为,政府的公共卫生系统应针对弱势人群的需求,而不是分城乡覆盖所有人群。所谓弱势人群,大致包括不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城市的贫困人口以及流动人口;其次,在发达地区,特别是聚集了大量农民工的地区,当地人应适当让渡福利利益,给予在此务工的外来人口,建立社会救助的形式或其他形式,以帮助危难之中的外来人口,同时缓解由于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紧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滚动新闻 > 《财经》号外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 |||||||||||||||||||||||||||||
| |||||||||||||||||||||||||||||
网络营销成新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