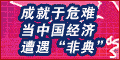| 神异男婴:民间谣言现代翻版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15日 18:42 南方周末 | ||
|
“神童”谣言及鸣放鞭炮的行为,其实都是数千年以来当地民众驱鬼逐疫时常用的方式,大都能找到历史根据。 这些传说、仪式活动,是农民在用他们熟悉的知识体系来应对非典这种灾难性的突发事件。尽管这些行为可以理解,但它同时反映出农村在灾难面前各种资源稀缺的现实。
我们也要慎重地分析研究谣言,不要简单地以科学与迷信的对立来解说。 回望历史,社会进步和自然灾难往往并驾齐驱。灾难的不可控和认识的局限性,使民间传统的解释系统——传说、神话、迷信、谣言盛行开来。伴随着灾难的流行,民间传言暗流涌动。 谣言有其历史渊源 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蒋非非副教授告诉记者,近日在各地传播的“神童”谣言及鸣放鞭炮的行为,其实都是数千年以来当地民众驱鬼逐疫时常用的方式。 众多“非典”谣言中,“出自诞生不久的男婴之口”这个版本的接受度最高,其实,这是古代中国人常用的制造舆论的方式。史料显示,早在《左传》、《史记》等史书中已有关于“童谣”的记载。 据蒋非非分析,谣言假托婴儿,其目的有二:神童发布——利用民众遇到突发性灾难时渴望“救世主”的传统心理以增加谣言的神秘感与权威性;童言无忌——借此躲避追查。 事实上,此次流传的非典民间谣言的几个版本大都能够找到历史根据。 蒋非非介绍,《说文解字》中释“疫”为“民皆疾也”,可能古人发现病死者会将疾疫传染给他人,这是病死者在作祟,所以要用巨大的声响驱鬼辟邪,禳灾纾难。 喝绿豆汤,蒋非非分析有两种可能根据:既然“非典”由病毒引起,而中医认为绿豆可“解毒”,故有喝绿豆汤一说,这是农民因为不了解此“毒”非彼“毒”而致。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旧时民间认为豆子可“驱鬼”。 此次非典传言的传播,与中国社会自古就有的民间传言相比有同有异。 据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副教授萧放总结分析,相同之处在于:其一,结构手法相同,伴随着灾难降临的是逃避灾难的神谕,神意的传达往往通过特殊人物之口宣讲出来。这种为神灵代言、指点迷津的方式,在中国社会有着久远的传统。 其二,重视特殊的时间点。时令节日在传统社会有着特殊意义,它们往往是时间转换的关口,是人们表达愿望、瞩目未来的特殊时刻。鞭炮放得最密集的是5月6日———立夏的到来代表一种期待:由春天所行的疾疫,也该终止于立夏之前。 其三,服食特定的食物进行身体保健。在特定时间服用特定的食品、饮品以保障生命是传统社会的通常做法。这次传言要在5月6日(立夏)晚上12点前吃绿豆粥,就隐含着传统立夏的服食俗信。 不同的是,与历史相比,此次非典传言呈现出它的“现代”特性。其一,传言直接利用了现代通讯手段。其二,传播面广,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因为有了现代的通讯媒介而愈益密切。其三,传言变异程度缩小。邻近数省都传递着同样的传言,变化甚少,这与旧时的传言有较大的差异。这同样与现代通讯技术有关。 民间谣言的现代翻版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认为,我们能够发现乡村的民间谣言主要利用的还是传统的口播方式。这种区别并不仅仅具有学理性的意义,因为都市和民间谣言传播所依赖的路径不同,我们能够发现有关谣言传播的传统解释构架需要某种修正。 按照奥尔波特的经典说法,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会发生磨尖、削平和同化的现象,即人们会在传播时突显某些符合自己口味和想法的内容;人们会把接收到的信息中的某些似乎不合理的成分去除;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信仰经验加工所接受到的信息。但是,对比这次的都市谣言和乡村的民间谣言,我们能够发现,后者的变异性要远远大于前者。 换句话说,奥尔波特的理论更适用于解释民间的谣言传播,而不适于解释网络时代的都市谣言传播。因为网络和手机短信的高度复制性,它为传播者个人留下了较小的“创造”空间,所以尽管广东和北京的谣言波及到整个中国,但它的版本似乎并没有发生过度的歪曲(比如,广东抢购板蓝根,江浙抢购的还是板蓝根);但是,乡村的民间谣言因为主要是通过口头的方式传播的,它自然成了一系列传播者“添油加醋”累加个人“智慧”的杂烩。对面的交往和绘声绘色的谣言转述,增加了人们的焦虑不安和集体性的歇斯底里,酿就社会不安。 传言彰显“灾民心理” 在现代人或者是城市人看似荒诞到歇斯底里的“神童谣言”,为何在中国农村却得以最大可能的传播和实践? 有学者把民众在危机事件中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盲从,比如对谣言的听信、传播和身体力行,称为一种“灾民心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高丙中长期专注于民俗学和农村研究,他将此次农村的非典“迷信”行动理解为一种农民应对特异现象的传统解释模式。在普遍接受过教育的现代人看来,迷信是一种无效的解释和解决方式,但在农民的精神世界里,它们被认为是有效的。 高丙中认为,这些传说、仪式活动,是农民在用他们熟悉的知识体系来应对非典这种灾难性的突发事件。这是中国农民传递信息的有效方式(用耸人听闻的故事、用鞭炮等张扬的方式告诉大家:麻烦要来了)。这也是他们迎接心理冲击的方式(仪式活动等):很多人对突发事件是不知所措的,一部分人因此弄出仪式性的活动,让老百姓能够按部就班地做点什么。 高丙中坦言,尽管这些行为值得理解,但它同时反映出现实农村在灾难面前各种资源的稀缺:农村医疗和卫生设施明显落后于城市,医学基本常识匮乏,对治病费用的恐惧等等。种种技术层面的匮乏,使农民对于“神秘现象”只能以这种神秘方式来解释。 据国家统计局5月7日公布的对部分农村“非典”影响情况的调查显示,目前大部分农民对于“非典”的知晓度已达到90%以上,但对于如何防治非典的基本知识了解却不高。以江苏为例,江苏农调队对1490个农村居民家庭进行了快速调查,在对预防、救治“非典型肺炎”知识了解程度调查中,回答“很了解”的仅296人,不到20%。5月6日湖南省卫生厅向社会公布的农村非典情况随机抽查的结果表明,农村“非典”防治知识了解度仅为36.2%。 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副教授方文在非典爆发以来,一直在思考在重大的公共灾难面前,困难群众的处境及国家的公共政策问题。他表现出了更多的忧虑:广大的农民群体和在北京等城市中的流动民工等群体一样,在重大的公共灾难面前,所体验的更多是无助和绝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何为?方文表示,种种的大众心理和行为如谣言,都是在不确定的社会背景中发生的。 不可否认,农民群体在有限的有关非典的真实信息面前,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容易感染、要被隔离、死亡率高、花钱多———这是他们能获得的显著信息。在这种境况下,方文认为,“农民中的‘智者’,他们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自然会构想出种种自救的策略,于是有关治疗或抵御的流言会得以产生。对于无助的群体而言,它们至少会有心灵上的安慰。” 传播学研究同样证明,谣言的制造和传播,反映出它符合社会某个或几个群体或集团的观念和利益,谣言传播的范围越广泛,速度越迅速,说明它的重要性越大,社会认同度越高,社会舆论代表面越广。 面对生命安全的威胁,人的恐惧心理会外化为一些具体行为,这些行为基于个人的知识程度、财力、性格、心理承受力、既往的经验、所处的职业群体、家族联系、接收与理解信息的程度等而会各不相同。农村地区的人群在茫然不知所措、真实信息缺失或信息虽多却无法破译时,往往会从自己熟悉的旧日民间传统中寻找可利用的资源。 “你无法想象让一个生活在南方乡野的阿婆在非典来临之时,向对她来说陌生、遥远的城市拨通心理咨询电话。”蒋非非打了这样一个比喻。 蒋非非分析认为,此次“非典”疫情引起部分人群、特别是农村民众的恐慌及谣言的迅速流传,剔除传统手段应对灾难的风俗原因,还与在防非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做法有关:其一,政府首次利用媒体详细向公众公布疫情,特别是患者数、病故人数,这种打破传统的新举措,有可能使长期处于信息严重匮乏、毫无心理准备、不了解现代公共卫生管理运作方式且远离大都市的农民产生误解,加重了恐慌气氛。其二,充斥媒体的专家解释过于专业,媒体不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将专业医学名词再加缩略,使大量不具备基本科学知识的农民难以把握事态与指导自身行为,继而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其三,各级匆忙上阵的基层防治队伍多为“外行”,难免在执行过程中“层层加码”,使部分农民产生“大难临头”之感。长期以来忽视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及科普宣传,民众普遍知识程度偏低。资源的严重失衡,又造成了农村防治非典的困难。接受记者采访的学者普遍表示,社会各界包括传媒对农民现实的生存状况缺乏基本的理解。 如何化解谣言 怎样认识和化解谣言,继而帮助人们从谣言中摆脱出来,是现代社会和政府面临的问题。 据媒体报道,湖北省公安厅已于5月6日深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在非典期间传播谣言行为及迷信活动。针对少数市民听信燃放烟花爆竹能防治“非典”和驱邪避灾的传言,5月8日,安徽省公安厅也发出紧急通知,开展打击行动,并派专人分头排查谣言来源。福建警方已开始追查谣言制造者并再次强调,对捏造或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根据《刑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一些学者对政府采取的控制行为表示理解,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道銮教授就认为,虽然迷信带来的心理暗示能够起到一定慰藉作用,但非典作为一个危机事件,也是检验人性的机会。一些不良企图的人或许会跳出来表演,如果控制不力,可能会威胁到社会安全。 “在传言满天之后,我们也要慎重地分析研究,不要简单地以科学与迷信的对立来解说,对复杂的事物不要作简单化的处理,堵与禁简便易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萧放副教授并不赞成用单一的方式解决问题。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周大鸣认为,谣言不等同于“封建迷信”,谣言的产生不可避免,如果应对不好,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媒体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一种应对机制,重视对谣言传播的处理。政府要建立起责任、理性、可信的形象,主动发布与大众攸关的公共信息。要保证这个渠道的公开、畅通和可信,使政府真正成为抵制消解流言的权威机构。 学者们普遍认为,动用行政和司法力量对一些不致威胁社会安全的传言进行干预还需谨慎。高丙中教授认为,最迫切的,还是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技术、信息方面的帮助。当这些帮助见成效的时候,这些传统的应对方式自然会退居幕后。 方文副教授则表示,谣言有其基本的传播路径,当农民不断获得一些正面、积极的信息和利益时,他们会自觉地修正那些传言直至抛弃谣言。“各级政府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切断非典传染源,宣传落实卫生措施,对一些不致危害社会的民间行为甚至谣言(如放鞭炮、喝绿豆汤之类)不宜强制取缔,应借助媒体向民众解释说明,待事态平息后,人们自会渐渐明白其无益或被人利用,营造宽松气氛反而有利。” 蒋非非亦持同样的观点,她认为,当突发性灾害降临时,底层民众潜意识中的非理性因素受外界及群体影响会加剧膨胀,此时应尽量转移人群的注意力,使人们放松心情,切不可风声鹤唳,激化矛盾。 对那些别有用心、恶意造谣惑众扰乱治安、确有证据企图制造事端者,蒋非非建议“应依法公开惩处,最好由当事人亲自当众坦白,以免以讹传讹,反而加速谣言的传播”。 反观历史,1768年那场惊动全国的“叫魂除巫”运动又是如何收场的?那一年,上自乾隆,下到官员,整个大清帝国被这个可怕的传言折磨着,终日疲于奔命寻找“叫魂”者。审讯疑犯的结果令人沮丧:所有剪辫犯即所谓的“叫魂者”均是被人诬告,所有供词也均为逼供或诱供所致。也就是说,1768年,大清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叫魂,有的只是人们的荒诞表演。 这或许是个有用的启示。(万静波、昊海刚对本文亦有贡献)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滚动新闻 > 南方周末SARS专题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 |||||||||||||||||||||||||||||
| |||||||||||||||||||||||||||||
网络营销成新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