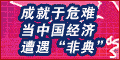| SARS考验《传染病防治法》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10日 21:32 21世纪经济报道 | ||
|
慧聪 一、法律适用与监管体制 疑问一、法律适用吗?前一阶段国内有关“非典”的各种报道的密集程度非常大,不过大多数媒体记者较少提到《传染病防治法》。媒体反映生活,也反映问题。为什么在我国 《传染病防治法》的适用范围在该法的第三条,明确列举了传染病种类的范围如下: 本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 “乙类传染病是指:病毒性肝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艾滋病、淋病、梅毒、脊髓灰质炎、麻诊、百日咳、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炭疽、流行性和地方性斑诊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黑热病、疟疾、登革热。 丙类传染病是指:肺结核、血吸虫病、丝虫病、包虫病、麻风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诊、新生儿破伤风、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除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法律列举的传染病,都是在我国已经发生过的传染病,立法以列举的方式,直接划定了传染病的种类和名称。不在范围之内的传染病不适用该法律。如果遇到今天的“非典”传染病怎么办呢?该法采取了一项授权条款来处理。该法的第五条最后一款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 因为“非典”是一种最近新发现的冠状病毒,而《传染病防治法》是1989年公布的,当时不可能将“非典”列入法律的适用范围是不难理解的。 在当前出现了“非典”传染病疫情后,是否可以适用第五条最后一款的规定呢?答案是肯定的,即完全适用。因为“非典”疫情比起《传染病防止法》中列举的甲类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传染病防治法》将增减防治传染病种类的权利授予了国务院和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卫生部)。国务院、卫生部有权决定将“非典”列入《传染病防治法》适用范围。 4月8日,卫生部发布《卫生部关于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呼吸道综合症)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的通知》(卫疾控发200384号)(以下简称为“4·8通知”),宣布将SARS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范围进行管理,并规定对诊断病例和疑似病人等可以采取的诸如隔离治疗等强制措施。 “4·8通知”开头部分是这样表述的: “根据国务院会议精神,为加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防治工作,经研究,决定将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从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超过《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重视程度,投入史无前例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防治“非典”,国务院领导将这次防治“非典”的工作同1998年的抗击大洪水的严重程度相比。当年的大洪水波及的省份还没有“非典”这样广泛,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也没有这样大;对国际影响也没有“非典”这样深刻。“非典”传染病已经足以达到法律规定的甲类传染病的程度,完全应该列入《传染病防治法》,使大病大疫当前法律得以适用。 为什么会出现不增加“非典”为甲类传染病的现象呢?还是国务院已增加了甲类传染病,而没有向社会公布?为了分析,笔者做三种假设:一是,法律的规定不适合当前防治“非典”的情况;二是,政府还不习惯采用法律来防治“非典”类突发传染病;第三,法律规定原则适用防治“非典”疫情,但实际操作时缺乏操作程序和具体措施支持。这三种假设中的任何一种存在,《传染病防治法》就不适于“非典”的防治。 疑问二、监管体制 《传染病防治法》对发生传染病后的监管模式做了明确规定。 该法第五条规定: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各级各类卫生防疫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防治管理任务,并接受有关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军队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国法定传染病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机构是“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具体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各级各类“医疗防疫机构”;二是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三是“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这种分类是按照“条条”(行业)来规定的。 这种按“条条”(系统)来分类管理体制对于当前防治“非典”工作,是否适应呢?从“非典”防治工作情况来看,防治管理是分地区的(块块)的,不是完全按照“条条”的。完全按照“条条”管理,工作起来不十分适应。 例如,在北京地区医疗单位分别属于不同的系统来管理的:有卫生部所属的医院,也有北京市所属的医院,还有在京的各部委所属的医院(如煤炭医院、冶金医院、邮电医院、铁路医院、教育部管理的医院等)。此外还有解放军所属的医院和武警所属的医院。上述医院各自都是独立系统,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是平行的,平级单位之间没有管辖权,在行政管理系统中也没有隶属关系。谁也“管”不了谁,各个医院分别都有自己的上级主管部门。 在“条条”与“块块”管理平时不衔接的情况下,在“非典”疫情发生时,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五条的规定,难以各系统发挥统一的监督管理。仅在疫情信息收集与报告方面,没有机构能够掌握在京医疗单位的所有“非典”病人与疑似患者数量的准确信息,更谈不到及时掌握与公布这些信息了。所以,这种按“条条”(系统)统一监督管理体制,对于北京地区疫情信息的迅速收集与及时发布已经证明是不适应的。 实际工作的情况是,及时组成了防治“非典”工作小组,由北京市委书记担任组长,统一调配在京地区的医疗资源,统一管理“非典”疫情的防治工作与信息发布工作。实践证明按照块块管理的体制是行之有效的。 还有一个小问题,在防治“非典”传染病的特殊时期,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五条授予卫生部的统一监督管理权,卫生部是否可能担当起这个职责呢?实践证明也是有困难的。困难之一就是北京市虽然在行政级别上与卫生部属于省部级,但是在辖区范围内北京市更容易协调本辖区的各种资源,如社区居民活动、交通安排、自来水供应、电力供应、能源供应、市政安排、卫生环保、商品供应、社会治安、大中小学教学、幼儿园儿童活动、媒体宣传、旅游活动等协调安排,北京市政府更加容易安排。 卫生部也没有申请将“非典”列入《传染病防治法》的范围,因而卫生系统也没有正当程序使用这部法律的授权来统一监督管理“非典”防治。北京市政府也没有法律的授权,统一管理防治本辖区内的“非典”。这就导致卫生部在防治“非典”的工作初期协调不力,北京市政府也没有办法协调在京各系统的医疗单位,4月20日中央的罢官决定作出之后,北京地区防治“非典”的工作统一由北京市委书记为组长,领导北京地区的防治“非典”工作。 地方以“块块”为主,全国以“条条”为主的防治“非典”管理体制,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因为“非典”作为一种新型传染病,传染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非典”开始发生在广东,后来在山西,北京等地发病数量较高。福建距离广东很近,但福建的发病数量却很少。北京与天津很近,天津发病也很少。山西与河北交界,河北的病例数量也较少。“非典”的这种地域性传染特点,造成一些地区发病人数较高,一些地区发病人数较少,还有一些地区没有发病。也正是由于这一地域性的特点,采取地方政府为主的统一领导体制,对于本地区的“非典”防治证明是有效的。 二、传染病防治具体制度 疑问三、防护措施 《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条规定: “对从事传染病预防、医疗、科研、教学的人员,现场处理疫情的人员,以及在生产、工作中接触传染病病原体的其他人员,有关单位应当根据国家规定,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 无论在广东省,还是在北京市防治“非典”的初期,被感染的病人总数中,有30%左右感染者是医护人员,现在医护人员被感染比例降低到了20%上下。一方面我们为医护人员舍己救人的忘我牺牲的精神所感动,为白衣天使的无私奉献行动而歌而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倒下了,谁来承担治病救人重任? 《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一条“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应当,设立预防保健组织或者人员,承担本单位和责任地段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和疫情管理工作。市、市辖区、县设立传染病医院或者指定医院设立传染病门诊和传染病病房”。 从目前防治“非典”的情况看,广东与北京市医院接诊初期,对于“非典”的病情不熟悉,感染了一些医护人员。过了一段时间后,医护人员再被感染倒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医护人员感染,或者医院无法防止医护人员被感染。因为一些医院没有条件、没有设备、没有病房等硬件资源防止医护人员的感染。 此外,在初期,北京的一些普通医院也没有防治病人经验和病房,采用临时改造的病房接诊。一些病人家属在医院护理病人、进出隔离区也有被感染危险,他们进出医院如出来吃饭或买东西等,也有将“非典”传染到医院外部社会的可能。这些医院位于城市人口密集的中心区,医院成为“非典”的感染源,这也是导致“非典”在广东与北京初期未得到控制的原因之一。 疑问四、疫情报告制度 该法律的第三章专门规定了“疫情的报告和公布”,有三项内容: 一是“全民报告”制度,第二十一条: “任何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报告。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发现甲类、乙类和监测区域内的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必须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限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卫生防疫机构发现传染病流行或者接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炭疽中的肺炭疽的疫情报告,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同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二是“透明报告”制度,第二十二条: “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 三是“公布疫情”制度,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 为使报告制度更加具体可行,《传染病防治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还对报告的责任人员和报告限定时间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四条规定: “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为责任疫情报告人。责任疫情报告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时限向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并做疫情登记”。 《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肺炭疽的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城镇于6小时内,农村于12小时内,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发病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并同时报出传染病报告卡。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城镇于12小时内,农村于24小时内向发病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出传染病报告卡。责任疫情报告人在丙类传染病监测区内发现丙类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在24小时内向发病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出传染病报告卡”。 《实施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责任疫情报告人应当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接到疫情报告的卫生防疫机构应当以最快的通讯方式报告上级卫生防疫机构和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发现甲类传染病和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报告后,应当于6小时内报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法律规定得已经很明确了。但是,“非典”在我国广东开始发生,发展到北京、山西、内蒙等地时,由于部分地方政府的官员可能担心“非典”影响本地经济发展,影响吸引外资,影响本地旅游、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对“非典”疫情发展的初期没有给予充分认识,也没有估计到“非典”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对“非典”疫情的法定报告制度,没有很好依法贯彻执行。 另外,法律在报告制度方面,也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在立法时没有解决。主要表现在“非典”疫情中曾经适用“五条标准”,或者是“三条标准”才能确诊为“非典”的技术标准问题。以北京市为例,在第一次卫生部召开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患“非典”人数是18人,4人死亡。一周以后,第二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北京市“非典”患者322人,疑似病人409人,死亡18人。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北京地区的“非典”患病人数增加了几乎近十倍,死亡人数增加了4倍多。外国记者对此感到不理解,不相信。 根据《实施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在诊治中发现甲类传染病的疑拟病人,应当在2日内作出明确诊断”。但是防治“非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确诊的标准是什么呢?当医学问题进入这样具体的技术层次,医学技术标准问题也许会变得非常敏感。 例如,北京地区在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间,采用的确诊“非典”的标准可能比较高,一周后标准降低了。标准降低一点点,患病人数就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标准幅度的取舍也许不仅仅是医学专家单独可以确定的,而且还要经过卫生行政部门的决定,或者地方行政部门的参与决定。类似北京地区“非典”数字的变化幅度较大,用技术标准来解释:一周前确定的确诊标准过高了,超过了实际防治疫情的客观合理的需要。 医学是客观的,标准是科学的,但是采取什么标准是由人来选择的。选择标准的价值取向,不但是医学的,还可能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政治学等社会学科的理论了。在《实施办法》中是否要将医学确诊的标准考虑也规定进去,当时立法没有这么细化地考虑。以后是否这么考虑呢?情。] 三、传染病防治相关保障措施 疑问五、污染的垃圾处理 在城市里,接诊“非典”的医院的垃圾处理曾经一度出现问题。由于担心被感染,负责每日处理医院垃圾的部门不敢到医院来运垃圾了。部分医院的垃圾堆放在原来的地方已经放不下了,越堆越大。医护人员担心带有病毒的垃圾二次污染周围的空气,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 遇到这种问题,《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七条已经作出了规定: “被甲类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卫生防疫机构的指导监督下进行严密消毒后处理;拒绝消毒处理的,当地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被乙类、丙类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处理”。 上述规定中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该是指城市环境卫生部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法定义务人机构的具体工作人员,可能是担心被“非典”感染,不到接诊“非典”病人的医院处理垃圾了。医院里的垃圾越来越多,一旦遇到下雨,垃圾被水冲走就会扩大污染范围,后果会更加严重。但是,《实施办法》中没有规定,法定义务人不来处理垃圾,是否属于“玩忽职守”呢? 如果法律认定属于这种行为是“玩忽职守”,该法的第三十九条有处罚性规定: “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和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对此罪规定了较重的处罚:“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上述规定的主体不适用于环境卫生机构的人员,环境卫生人员不是“卫生防疫”人员。所以,不可以采用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所以,对于第十七条规定没有落实的环节,这一条款变成了原则性的条款,难以在实际中使用。 疑问六、财政预算 《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都没有规定防止传染病的财政预算问题。但是,财政预算是开展任何工作的基础条件,现在财政预算问题在防治“非典”过程中非常值得研究。因为没有财政预算的预期,医院和有关防疫单位是在没有底数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采用临时性的财政手段来对付可能是较长期的防治工作。 研究“非典”防治预算发生过程,最先发生超额预算的机构是医院,医院有义务接诊任何病人,包括无力支付医疗费的病人。其次,医院要改造普通非传染病房为“非典”传染病房,医护人员要装备专门的防护服,专用防护眼镜、专用防护口罩、医院专门消毒用品、专门预防药品等,都会加大医院的预算。医院的做法是先用自有资金垫支,或用每天收入“坐支”(用每天收来的钱直接支付花费的钱)。尽管财务纪律上对坐支行为是禁止的,但是,由于处于紧急特殊情况,又没有专门外部资金,院长批准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其次,是全社会各企业事业机构的预防预算。如果这些单位是国家的,所有预算都是国家拨款的,原来的拨款没有预防“非典”传染病的预算,现在只能先从账上有钱的科目里先付账了。社会上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普遍发给职工预防“非典”中药、口罩、体温计、消毒液和预防非典的手册。这些物品都是从外部超级市场上购买来的。 这些预算将来如何使财务平账呢?应该有两种选择: 一是,国家财政给国有企业、事业机构这部分预算外防治“非典”的财政开支给予拨款。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已经在4月20日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财政是他的强项,因为他长期在财政部担任副部长。他说卫生部合理的申请的财政拨款,各级政府财政都将批准。 二是,政府财政拨款不足时,已经发生了的费用只能由各个单位自己解决了。现在政府下令医院不得拒收非典病人,号召各单位自己采取预防措施,各单位财务只能从其他账户上的其他项目的钱先用到防治“非典”项目上来,当务之急,防治非典是重中之重。当“非典”疫情过后,再考虑其他。 类似这种临时措施是正确的,但是,今后经过了防治“非典”的实践,我们在立法上应该考虑在政府财政里建立专门的应急基金或预算。否则,由此带来的财务制度方面的负面影响也很大。 疑问七、控制商品物价 在《传染病防治法》和《实施办法》中,均未规定控制预防传染病商品的物价问题。这些内容也许在《物价管理条例》中规定,但是,经过查询《物价管理条例》中也没有类似的规定。这个问题成为法律的空白。 广州和北京的市场上都曾出现过一些商店乘机哄抬物价的现象。由于没有法律,有关政府不得不发布临时禁令,禁止市场乘机涨价的行为。我国在1982年颁布过《价格管理法》,其中没有对特殊时期抬高物价的处罚条款,只是对一般情况下抬高物价的处罚。在防治“非典”的工作中,属于特殊时期,应该采用比平时更加严厉的法律禁止不法商店抬高物价,制造市场恐慌的情况。这种法律条款应该在《传染病防治法》或《实施办法》中规定一个条款作为《价格管理条例》的特别法。同样在发生自然灾害或战争期间,也应该在有关的法律中规定限制涨价的特别法规定。 结论:法贵于行 据悉,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卫生部,已开始组织有关专家起草并将于近日火速推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处置等,纳入法制化的管理。此举旨在进一步强化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统一领导与指挥,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职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笔者感到起草新的,专门对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规是必要的,从目前防治非典的工作来看,如果有了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条例,防治工作也许会更加有效。 但是,笔者同时也在想,1989年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已经生效了14年了,“非典”就是一种传染病,而且已经在全国大多数的地区发生了,已经威胁着公众的生命和健康,影响了正常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也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什么《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实施办法》不可以适用呢?只要有关政府部门宣布增加“非典”为甲类传染病,或者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就可以了。如此简单的程序也许几分钟就解决了,现成的法律就可以适用了,何必现起草一部行政法规呢?退后一步考虑,即便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就是赶时间制定出来了,如果在适用方面出现了《传染病防治法》那样的情形,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不是同样不能适用吗? 从防治“非典”的情况看,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法律不适用,或者是我们还没有习惯使用法律,或者法律虽然写得不错,但是在实际操作环节不配套,难以执行。 法贵在于行,有了法律不等于就有了法制,法制存在于执行。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无法可依的时代了,而是进入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时代了。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滚动新闻 > 21世纪经济报道SARS特刊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 |||||||||||||||||||||||||||||
| |||||||||||||||||||||||||||||
网络营销成新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