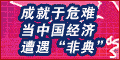| 外来客的煎熬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10日 10:05 经济观察报 | ||
|
本报记者 黄茂军 北京报道 东五环外围的定福庄显然位于北京的边缘,在定福庄西街甚至至今还能看见通县的界碑,也就是说,现在属于朝阳区的定福庄在早年间还是通县的辖地——在通县更名为通州区后,定福庄成为不折不扣的“都市里的村庄”。隔着朝阳路,定福庄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和第二外国语学院等著名学府比邻,这多少让它添了些许书卷气。据说定福庄曾经是诗人、流 随着城市的蔓延,定福庄地面渐次出现一些物业楼盘,加上原有的几个企事业大院,这些门口有保安站岗或者居委会大妈打坐的院落,透着一种草木皆兵的矫情,倒是条条小巷通大街的定福庄,因为它的不设防而显出本色。张日辰 5月里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风过后,有花瓣纷纷扬扬,偶尔的一树泡桐花用它艳俗的浓香搅扰了槐花的清香,这在今天的北京实在算得上是一种奢华与铺张。可空气中还是有着太多的消毒水的味道,就是定福庄也不例外。 张日辰认为现在消毒水的味道比花香更能让人放心呼吸。和这个村庄里众多的外来户一样,来自江苏常熟的张日辰其实也是一位租房者。“5·1”期间,与他住在定福庄北街同一院落里的23位房客只有一位回了老家。在不足150平米的空间里居住着包括房东一家在内的28口人,其间的逼仄可以想象。 据说因为他是最有文化的房客,他租住着这个院子里最好的一间房。房靠天井,采光很好,与房东一家门对门。所以,尽管那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明显残存着不新鲜的空气,张日辰还是对自己的居住环境表现得心满意足。“防非典嘛!就是要保持空气的通畅,我们常通风的。”他指了指被封闭的天井上方,那扇由一根木棍支着的窗。 2001年,在完成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的三年进修后,张日辰滞留在了北京。两年里,他换了11家单位,搬了7次家。他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家杂志的摄影记者,据说这本杂志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平时给员工支薪都显得捉襟见肘,“更别说什么医保、福利了。” 据张日辰自己说,在他现在的服务对象中,有一些是中国目前最具身价的名模。“我可不能感染SARS,不然谁还敢找我拍片呢?就算政府会支付全额的医疗费用,我也病不起。”话说到最后,张日辰目光漂浮,几近呢喃。唐倌儿 夜幕下的定福庄曾经有“鬼市”的封号,和所有高等院校周边地带一样,这里餐馆、酒吧、游戏机房和网吧林立。繁华、喧嚣、灯红、酒绿,处在城市边缘的定福庄一样都不缺。当然,在SARS的打压下,曾经的万丈红尘现在都毫无悬念地归于沉寂,绝望的食客能够从各式各样的门脸上,看见用各种字体写成的千篇一律8个大字——非典时期,暂停营业。 唐倌儿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即便是经常光顾“渝乡居”的熟客也没弄明白,大家都学着那些服务员的吆喝,用川音扯一嗓子:唐倌儿!一张似乎永远油汪汪的笑脸就立刻出现在你的桌边——然而,现在那张笑脸表现得有些气急败坏。 “渝乡居”的几位服务员吵着要回老家,她们冲唐倌儿要自己的工钱,为此唐倌儿正在做思想工作,试图让这几个女孩打消回家的念头。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张报纸,逐字逐句念给那几个员工:从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传出的信息,来京务工的劳工、东南沿海和中部来京经商者、外籍商人和学生正成为近期北京出城客流的主体。这个非常时期的流动潜藏着对全国各地的巨大威胁。念完报纸,唐倌儿又添油加醋地渲染:就算你们上得了回家的火车,政府也会派人在火车站等着你们,先关你半个月的禁闭再说! 那几个女孩毫不理会老板的这套言辞,还是坚持要工钱走人。唐倌儿就火了,扬着手中的报纸冲那些女孩喊了起来,旁观的人听不懂唐倌儿嚷嚷的是什么,隐约听出“负责任”被重复了好几遍。 这场争执发生前唐倌儿和女孩们正在“斗地主”,一场原本是为了排遣非典时期无聊的游戏就这样给搅了,的确是件扫兴的事。唐倌儿问:“钟南山说北京的疫情会在这个月中旬得到控制,这话有没有谱?”这位经营者显然有些熬不下去了,他借着数落那几个丫头,向旁观的人大吐苦水:“房租占了大头,这是不能少的,水、电、气的开支能少一点,厨下的油盐酱醋可以少一点,但不是还有十几个人要吃要喝吗?卫生费该交的已经交了,多出的消毒、劳保费用一点也不能少……” 5月4日晚上,还应该算是青年的唐倌儿突然老气横秋地变得宿命起来,“这场瘟疫是我注定难过的一道坎,我不该从拉萨下来,唐倌儿不属于北京。”陈可 定福庄最大的超市是二外对面的天客隆,天客隆的一楼有间麦当劳,这让陈可和她的“同事们”喜出望外。5月初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陈可在这间麦当劳一个临窗的位置上不管不顾地和谁通着电话,“这哪儿是乡下呀?有麦当劳,还有啊呀呀。”陈可说的“啊呀呀”是间连锁性质的时尚精品店。据她自己说,从上月底搬到定福庄,她们几乎每天都会上“啊呀呀”逛逛。 “我以后要开一间这样的店。”陈可很肯定地说。 这位从小兴安岭一个叫铁力的地方来的女孩是典型的“话痨”,说一件事絮絮叨叨而且手舞足蹈: “我们原来住在东直门外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室。上月底,居委会的人来通知说,市里有文件,地下室不让住人了,怕我们染上非典。话说得还很急,今天通知的,明天就不让住。五叔说:‘我在定福庄还有个院子空着,你们就搬那儿住一段时间吧!等非典过了再搬回来’。大家一听这定福庄都出五环了,小脸都绿了。五叔又说:‘你们看报纸了吗?感染非典的都是四环以内的人,城里有钱人都住到城外去了’。五叔这么一说让我们都很舒服,感觉自己很有钱似的。” “可等我们搬来一看又都傻眼了,有钱人能住这样的地方吗?门前那小胡同简直就是个‘一线天’,幸亏我们个个窈窕淑女,只要来个肥肥就得造成交通阻塞;后面是条臭水沟,全村人的污水都打我们窗下淌,旁边还有间茅房……房间里的味儿实在是太大了,消毒水也不好使,盖不住……我们现在就是在扛着,熬着,等着这阵子非典过去。” 追问陈可她们的职业似乎是件困难的事,好在陈可出人意料地坦然:她们是小姐,我不是,我是公主。所谓“公主”,就是KTV包房的服务生。陈可承认,这的确不是份体面的工作,但丢人也丢不到哪儿去——在北京我实在找不到一份比这更能来钱的活儿。 现在SARS闹得这么厉害,害怕吗?陈可回答说不怕。想家吗?陈可摇头。她的眼圈开始发红。她有意掩饰,扭脸看窗外,似乎对某处街景发生了兴趣,最后转回来很肯定地说:“不想家!铁力除了木头啥也没有,吃个麦当劳得上哈尔滨。”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滚动新闻 > 《经济观察报》:SARS不应将我们隔开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 |||||||||||||||||||||||||||||
| |||||||||||||||||||||||||||||
网络营销成新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