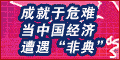| 揪心疫情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10日 09:59 经济观察报 | ||
|
本报记者邵颖波(执笔) 戴佩良黄一琨北京报道 太阳升起又落下,昼夜仍像往常一样轮回,但是突然间,北京人似乎已经无法分清现实与梦境的边界。一个多月来,SARS的梦魇,盘踞在首都的上空,让人们体会到空前的紧张、恐惧和烦躁。 不管是被吓破胆躲在屋里拼命休息的人,还是那些耐不住寂寞出来当街跳舞的人,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都必须要在每天傍晚的时候知道那个数字——69,或者是96。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数字代表的确切涵义,也没有多少人了解其中的故事,只是,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都不得不在心底盘算一下,自己会不会在哪一天成为那个数字的一个组成部分。更让人难过的是,如果真的不幸成为其中的一个“1”,在一场集体性的灾难中,在个人心中无比珍贵的生命,可能只剩下统计学上的意义。为什么关心疫情 如果我们自问,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所有的人如此一致地关心疫情的变化,可能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你是平民百姓,那你必须根据这个情况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是政府官员,那你也必须根据这个情况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如果你的工作与疫情没有关系,那你的注意力可能更多地放在特殊时期的形象安排上面;当然,如果你是个生意人,下一步是赚钱还是赔钱你就得花更多时间来进行考量,疫情的发展变化是最重要的根据之一。 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一件事,所谓疫情,绝对不是仅仅指疫病本身在当时当地的情况——确诊多少,疑似多少,治愈多少,死亡多少,病毒如何生长又怎样传播。事实上,对于SARS,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非常之多,它的过去和它的未来,本地与外地,交通和天气,政府的管制与宽容。它的外延无比宽广,你要了解的事情非常之多,甚至包括警察与军队的动向。你或许无暇判断政府已经实施的措施是不够严格还是已经超过了限度,但是你可以根据这些情况来猜测疫情的发展,如果疫情的发展本身是按照一种我们谁也弄不懂的规律在进行,这依然不妨碍你根据政府或者社区的措施来思考自己的行动。就是说,虽然在现时这个阶段,你无法弄懂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必须知道的,那就是在这一场灾难到来之时,你已经身处被动,于是,你必须了解更多的信息,而所有你想知道的,都是疫情。 这是人之常情,人之本能。因为违反了这种最为基本的意愿,4月20日,张文康、孟学农被免了职,关于“疫情已经被基本控制”的说法也随风而去。 但是,我们又陷入了另外一种疫情信息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仅源于因为某些官员前期表现不佳所带来信任危机,更主要的是出于我们对疫病本身的无知。不仅我们平民百姓对此一无所知,包括我们所仰仗的专业人士,他们分别进行研究,采取不同方法,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也得出相互一致或者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这些信息面前,我们无所适从。 我们最最想要知道的就是北京的疫情会在什么时间结束?临危受命的代市长王歧山先生说得好,任何对疫情的判断都像是在进行一场赌博,这是他第一次和公众交流时对疫情本身所下的最为清晰的一个判断,但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判断,它丝毫不能减弱人们强烈的求知本能,“赌博”仍在进行,有些机构和个人参与进来,提出自己的看法,更多的平民百姓必须努力找到一种打算要认同的主张。 但现在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瘟疫乱情 我们基于事实而能够相信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迄今为止,北京现在是全球SARS病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北京的疫情发展不仅关系这里的1300万人的生活,也关系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做到的不仅是动员所有力量来控制这里的疫情发展,也要让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这里的每一个细微变化。 感谢政府的责任感和法律的要求,现在我们每天可以获得疫情的核心内容,但缺乏可靠的权威的解读仍使我们心中存在着太多疑惑。我们可以听到草丛里蛇的肚皮划过草尖时悉悉索索的声音,但是我们不能知道这条蛇的毒性有多么大,它将游向哪里。 具体来说,现在我们还不能得到有关感染人群的详细资料,不知道他们染病的具体细节,难以判断谁处于高危人群,不知道到底有哪些传染渠道,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治愈者可能复发,不知道北京的疫情与先前广东和香港有多少不同,病毒又发生了什么变异?因为我们对于流行病学的基础知识了解太少,不知道哪些数字或者图表对于呈现疫情转变更为关键,甚至,我们对于某些调查机构说95%的北京人满意的结论如何得来也不得而知,就像我们不知道流调队有多少人在工作,去了哪些地方,问了哪些问题,发现了什么结果一样。于是,我们也和所有的人一样拼命地搜集信息,或者不停地看那些零七八碎的报道,脑海也就呈现一种无法梳理的乱象。 5月4日,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的有关SARS病毒最新研究报告显示,这种致命病毒的韧性,比原先想象更大,甚至可以在人体外存活长达数周。可是先前我们听到的说法只有3-4个小时。这份报告里还说,这种类似流感的瘟疫,并不一定要直接接触已感染的病人,只要碰过已污染的物质,就可能被感染。 但是香港、日本与德国进行的实验室研究结果又不一样,他们认为SARS病毒在人体以外的任何表面,可能存活数小时;而在人体排泄物中,它可以存活四天。 关于病情诊断标准的改变也让人感到紧张。前不久WHO更新了SARS病例的定义,规定疑似病例的抗体、病毒核酸或病毒培养检测结果,只要任何一项是阳性,就认定是SARS。这意味着WHO在鼓励病原学检测方法尽快投入临床一线使用。而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的医生在诊断SARS时,主要依靠的还是量体温、做胸透、查血象等临床检查。 研究似乎在证明病毒可能越活越长,传播越来越容易,而且毒性也越变越凶,但是由这种病毒所引起的疫情如何发展却始终不明。当我们需要受到鼓舞时,我们会看到乐观的专家被请上台来,他们说这种病可防可治,而且情况正在好转;当我们需要进行更加严格的政府措施时,我们又会听到相反的说法。情况就是这样让人无从判断,5月3日,我们听到钟南山院士预测说,北京可能在5月中旬以后进入下降期。但是在7日,我们又听到WHO表示:现在说北京SARS疫情已达高峰,还言之过早,目前仍无法判断北京整个疫情走向。多变的病死率 在这非常时期,死亡成了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高频出现的词汇。而在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上,病死率的高低之争也在科学家与政府官员们之间进行。关注这方面的不同说法,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北京疫情呈现出的模糊景象。 所谓病死率,又称病例死亡比Death-to-case ratio,是某病患者中的死亡频率,是观察期内因某病死亡人数与同期某病患者数之比。这个一般以百分数表示的指标说明疾病严重程度,反映疾病预后,反映医疗质量。 在人们尚未完全掌握有多达六种变种的冠状病毒的时候,切断传染源与降低死亡率成了减少恐慌、增强信心的保障。前者是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最怕媒体提到的问题,至于后者,至今仍是一个让人揪心的谜团。他在5月2日检查疫情防治工作时援引专家意见称,1998年爆发的流感受感染的人数比这次多,病死率也达到8%,为此希望民众能够坚定信心。 就在有人指出北京疫情当中病死率高于其他地方的时候,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员朱宗涵教授公开提出,北京非典患者死亡病例中近10%死因与非典无关。而从广东临时抽调来京的广东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肖正伦,面对本报记者提问时也表明了这一观点,认为不应把过多的精力集中于现在的病死率数据,更重要的是看到趋势;但他也向北京市有关方面提出了集中收治重病病人的建议,这一建议的重要目标就是降低北京的病死率。 但是另外一些国际同行们对此并不很乐观。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的研究表明,SARS的死亡率是20%。这是根据从2月20日到3月15日对香港1425名怀疑患有SARS病的住院病人的统计分析得出的。这项研究采用参变量分布的统计手段,6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率是43.3%,60岁以下的是13.2%。 WHO负责SARS研究的Klaus Stohr博士认为,对病死率计算的统计学手段有很多种,并取决于不同的情境。WHO正在考虑改进他们的数据获取和统计学模型。而在5月6日,该组织认为香港的SARS新增病例正在稳步下降,目前的病死率为11.7%。 《柳叶刀》杂志组织的研究认为对该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SARS的死亡率可能要高于官方卫生机构对它的估计。随着疫情的继续,死亡率会有不断变化,但是除非有极为显著的变化,否则SARS将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 肖正伦认为北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一些,确实看到北京的疫情有一些特点,原来有基础病历,年龄比较大的患者多一些,目前专家们也在努力寻找规律,并在考虑是否可能是北京病毒变得比较“毒”一点? 他认为其中的因素很复杂,不能单纯说治疗上有问题,关键是要调动所有的医疗力量上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朱宗涵则表示,随着SARS疫情趋于平稳,加上医务人员诊断、治疗抢救的经验不断积累和对重症病人的早期识别及抢救条件、力量的改善与增强,北京的非典死亡病例会逐步下降。 国外专家认为有可能有的病人感染病毒却未发作,或是有的人症状很轻微,没有就医。如果这些因素确实存在,那么疾病的死亡率可能还会降下来。但在5月6日,WHO总干事布伦特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表示,SARS在中国还没有到达发病高峰,现在谈论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消退为时尚早。疫情延展之后 一场SARS疫情的突发,让很多人有机会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的瘟疫发生史。的确,瘟疫本身历史久远,相伴而生的人类关于疫情研究、控制以及相关的科学发展也同样源远流长。流行病学调查已经成为了这一学科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为了摸索传染病发生的原因和传播的条件,以便及时采取合理而有效的防治措施,人们总是伴随着瘟疫的发生而进行科学的调查,这些调查可以查明传染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诸如传染源、传染媒介、传播途径、易感动物、影响传播的因素和条件、疫区范围以及发病率与死亡率等。在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人们也总结出了一整套分析方法,可以保证人类可以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发现规律,并对有效的措施作出正确的评价。 现在,人们在很多问题上存在争论,比如北京市的防治措施是不够,还是太过了,还是恰到好处。如果真实信息是在4月13日,而不是4月20日发布又会是什么样子?北京市还会产生多少病人?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极限是不是媒体报道的6000人?超过这个数字会怎样?老百姓该不该上街买菜?被推迟的集会该什么时候进行等等。无谓的争论往往更使人感到无奈,只有真正的科学精神才应当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所谓科学又绝不仅仅指医学、流行病学和自然科学,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系统的学问体系都是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尊重的。就像我们对付SARS病本身必须依靠全球的医学科学家以及他们所在机构一样,对付SARS疫情,我们也必须依靠所有的相关学科的专业人士共同研究来确定我们的综合方案。所幸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志于为此做出贡献的人并不少见。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客座教授曾强先生的一份建议。曾强先生认为,政府现在公布的每日疫情数字和累积数字,仅仅反映了城市SARS的历史状况,这些资料是根据政府已经控制的病人的情况做出的,但对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危险并不能做出直接的反映。这位应用数学专业出身的人士建议通过数学模型的计算,建立起一套“城市传染源危险指数”体系。从而科学地反映疫情变化的趋势。曾强先生自己已经初步进行了这项研究。 当然,我们还知道,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在各自的领域内进行着有关研究,和曾强一样,他们都各有所长。这些人的智慧应当是我们可以依赖的最大最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只是,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建立起彻底尊重科学的意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也许永远都弄不清楚疫情的发展。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滚动新闻 > 《经济观察报》:SARS不应将我们隔开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 |||||||||||||||||||||||||||||
| |||||||||||||||||||||||||||||
网络营销成新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