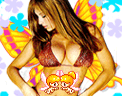|
李萍
近日,屡有关于某些地区统一城乡户籍制度的消息。媒体除了对这一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措施给予关注外,更多地把目光投射到实实在在感受这项措施的“新城镇居民”们身上。令人不无失望的是,这些“新城镇居民”并没有对身份的转换表现出太多的欢欣鼓舞,相反却对这个新身份没有享受到相应的配套措施感到无可奈何。
去年偶然之间在《第一财经日报》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指出,片面强调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项消除城乡差别的措施,难免会让改革流于形式,演变成一项政府官员作秀的“政绩工程”。今天的改革“实效”正在印证着这个观点。如果我们把这次改革继续作一深层次的分析,会发出这样一些疑问:政府在城乡统筹工作中究竟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这个角色是否会因为区域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市场导向下的适当倾斜
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问题,主要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或主要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机制安排以及“城乡分治、重城轻乡”的政策效应所致。鉴于我国城乡发展失衡的特殊成因及其机理,特别是其现实影响,“解铃还须系铃人”,城乡差距还是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缩小。
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等于采取完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是在尊重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尊重市场导向的城乡融合与城乡互动的规律基础之上,政府适当采取倾斜的制度供给、体制创新、政策创新、发展战略创新的具体措施,使长期以来处于相对落后的农业、农村、农民得到补偿性的发展,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乃至城乡的协调、平等发展。
“三农”问题解决容不得浮躁
笔者认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存在“外化解决”、“内化解决”和“一体化解决”三种方式。所谓“外化解决”方式是指“三农”外向的转化,走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农业非农化的道路,这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大趋势。所谓“内化解决”方式是指“三农”内在的提升,即要探索如何建设新农村、塑造新农民、发展新农业。所谓“一体化解决”方式则是“外化解决”与“内化解决”方式同时并举以及城乡优势互补、交融整合地发展。
不过,目前我们觉察到在实际工作中,对待“三农”问题,有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和浮躁情绪,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实际工作部门,不考虑各地的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条件差异,存在着只讲“外化解决”方式,忽视“内化解决”方式,并把“一体化解决”方式作为体现政府政绩的一项工程来抓的倾向,试图通过设几个“试点区”,搞几个“样板点”,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做高”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数字指标,就匆匆作出了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结论。然而,物理学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的定律,尤其是我们过去的历史教训表明,今天投入了多大的热忱“作秀”,到头来就会受到多大的、甚至更大的惩罚。
对此,笔者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一定的过程,也需要区别对待。对东南沿海或城郊等经济比较发达、城乡生产要素流动性高、经济联系紧密、城乡差别不大的地区,可以先行重点实施“外化解决”方式和“一体化解决”方式,同时,重视采取“内化解决”方式;而对内陆腹地的农村,特别是边远落后的乡村,城乡之间在经济上缺乏联系,地理、交通上联系也有诸多不便等,则要更多的在“内化解决”方式上下工夫。
制定与反哺“三农”相配套的城乡协调发展政策
具体地说,总体上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的不同时期,又有一个作用、定位的转换问题。就近期而言,政府首先要“补位”,通过制度创新、制度供给、创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机制。换言之,通过政府掌握的财政资金、土地、贷款、组织人事等资源,加大对农业非农化的相关投入,加强土地使用及转让制度、户籍制度、农业劳动者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有效地推进“三农”的外向转化。同时,政府还应按照WTO所允许的“绿箱”政策,大力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保险、农民教育等方面,积极推动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现代化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采取和推广多方筹集培训经费的办法,实行国家、地方、乡村、个人分担培训费或以联合办学等形式发展农民培训,对农民开展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培训,培养大批知识技术农民,使农民从传统体能型转换为智能型、技术型的新农民;增加对农业科研和推广、质量安全和检验检测等方面的投入,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形成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的新农业,有效地促进“三农”的内在提升。此外,政府还应对过去城市偏向、工业优先的发展政策进行调整,制定与反哺、扶助“三农”相配套的城乡协调发展政策和措施,在保存和发展城市与乡村鲜明特色的前提下,改善城乡结构和功能,协调城乡利益和利益再分配,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平等发展,积极寻找城乡互融、互补、互惠、良性互动的“一体化”新型发展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