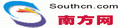|
|
农垦改革原地转地租之重猛于虎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0日 10:28 南方周末
 大兴安岭农垦区实行统一规模化种植之后,大兴安岭农垦集团公司的效益显著增加,当地农场职工的收入却显著下降 图/CFP 农垦改革原地转地租之重猛于虎 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 发自 内蒙古呼伦贝尔 农场工人究竟是一群什么人?是农民?享受不到中央的惠农政策;是工人?一辈子种地,一半的收成要上交,还没有工资。在他们的支持下,农垦公司迅速完成资本积累,成为产业巨人,但他们的生活却每况愈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减轻他们的负担,却遇到政企不分的农垦系统的阻力 2007年6月初,57岁的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扎赉河农场的杨大木给农业部农垦局领导写了一封信,感慨农垦职工“昔日扛活给地主,今日种地为谁劳?” 他在信中提到,自2006年以来,压在农民头上的种种税费已经得到有效地清理,但在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下辖的8家农场内,这些名目繁多的种种税费还压在农场职工头上。 50多年前,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众多青年奔赴边疆开垦戍边,他们把青春全部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也是这个背景下成立的。1979年,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正式从黑龙江划归内蒙古,并成为全国七大国家直供农垦局之一。 和许多拥向这片荒原的人一样,1975年,25岁的杨大木从辽宁出发,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管辖下的这片黑土地。 就是这样一批人,成为几十年来中国农业安全的最得力支持者,到1999年,全国农垦系统已经发展成拥有438万职工、2101个国营农场的庞然大物。 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农场工人的收入不仅与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承担的赋税也越来越重。 为此,2006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为此专门公布了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的意见,要求国有农场也取消农业税,同时免除农场职工承担的民兵训练、乡村公路等杂费。2006年12月底,农业部农垦局局长杨绍品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农垦专业会议上表示,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必须“确保农工较重的社会负担减下来,确保农工负担减轻后不反弹”。但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并没有认真执行。 土地就是一切 柜子的油漆慢慢开始脱落,白石灰刷的墙壁蒙上了一层灰土,这是东方红农场远近有名的小康文明示范户孙国胜的家。东方红农场是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下属的8家农场之一,位于大兴安岭南麓,拥有9000亩土地。 7月4日,67岁的孙国胜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显得有几分拘束,很难想象,他曾经是农场里的一个生产队长。 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孙国胜对这片土地感情深厚。“这可是黑土地啊,多好的土地。”孙国胜指着屋外感慨道。大兴安岭农垦区土质肥沃,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 这里是种植大豆的黄金地带,每亩大豆产量可达240-260斤。孙国胜向农场承包了183亩地,种植大豆。 去年孙国胜把一半的大豆作为地租交给了农场,再扣除农药3000多元,化肥6000多元,最后孙国胜每亩地只挣了70元。 今年东方红农场把地租从每亩119斤大豆降为114斤,孙国胜依然觉得太高,但这由不得他。东方红农场还替每个农场职工家庭制定了致富计划表。 在孙国胜家的2007年致富计划表中,孙家要种植大豆183亩、万寿菊3亩,养鸡20只。孙国胜家中现在一只鸡都还没有养。 孙国胜很怀念过去的日子。“以前最好的时候,我们一家有3万多元的收入。”那是1980年代中期,农场实行承包制,每个农场工人有40亩地,“种什么品种、作物都是自己决定”。但1990年代后期,农场就统一实行规模化种植。 在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东方红农场时,当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孙国胜很担心今年的地租缴不了。 孙国胜并不埋怨目前的生活。毕竟农场替职工交了养老和医疗保险,像他这样年满60周岁的男性根据工龄可以每个月领到退休金,他现在每月的退休金是760元。但绝大部分农场的职工在退休之前,只能租种农场的土地获得微薄的收入。 失去土地之后 杨大木的日子不如孙国胜好。他住在距东方红农场50多公里远的扎赉河农场里。扎赉河农场的草甸、豆田和东方红农场一样令人心旷神怡,但杨大木却感受到一片悲凉。 57岁的他住在10年前买的三间小屋里,房子是用泥土夹杂着柴草建筑而成,房顶则是草毡覆盖,在狭窄的房屋内,炉子将墙壁熏得漆黑。扎赉河农场里一半的农场职工都是住这样的房子,杨大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甚至有的都赶不上这种水平”。 杨大木一直在等待自己的“身份”。2002年3月,他和扎赉河农场的1000多职工因为没有缴纳19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2100元的人头管理费,被“开除”出职工队伍。自此之后,杨大木就不断争取恢复自己的职工身份。 2007年6月1日,杨大木终于等来了呼伦贝尔市政府的复核意见。但这份意见并不支持杨大木的要求。现在,杨大木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他成了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的农场职工。 这意味着他不能拥有农场分配的15亩员工田。2007年,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实行了“两田制”改革,农场职工每人可以耕种12亩或15亩不用缴纳地租的“员工田”,其余就是归农场所有,需要竞价承包,交纳承包费的“规模田”。 杨大木既没有“员工田”,也没有钱承包“规模田”,他已经无田可种,实质“下岗”了。在大连、青岛工作的儿子和女儿负担了他的生活费。杨大木只能麻木地忍受目前的生活,平时写一些讽刺现实的打油诗成了他的精神寄托。 扎赉河农场其余“下岗”的农场职工为了谋生,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因为农场地租过高,被迫租种附近农村的土地,算下来每亩地的地租还比农场低20元,“受了灾也可以谈,而且种植也不受限制”。 但这只能保证吃饱穿暖,解决不了教育、医疗等大事。杨大木的一位“下岗”邻居,为了供养在湖北上大学的孩子,已经欠下了3万元的高利贷。 而一些读书毕业后返回农场的子弟,现在也是茫然——他们没有职工的身份,没有土地,能够做的就是从父辈手中承包土地,或者选择去附近农村承包土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国有农场劳动力就业率仅为79.57%,待业和失业人员大多聚集在垦区内部。 杨大木在给农业部农垦局领导写的信中如此写道:被除名的职工及近些年回场务农的青年约万余人,他们都没有得到“员工田”。 地租为啥这么高 黄西峰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个颇能折腾的人,因为他带头和农场谈判地租。皮肤黝黑的他现在是巴彦农场的一位职工。之前,他是农场的一个队长。 1999年开始,这个最基层的官员,一直在各种场合呼吁减轻农垦系统的负担。1999年,巴彦农场小麦欠收,在当年的秋粮收购中,作为队长的黄西峰并没有按照上级指示收小麦,而是让农场职工用黄豆顶替,此举受到上级的斥责。 一气之下,黄西峰递交了辞职申请。自此,他成了一个只种粮食的职工,而这也让他更尝到了种粮的艰辛。 2003年,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下属的十多家农场接连遭受了旱灾、涝灾和冻灾。巴彦农场的大豆平均亩产还不足40斤,但是当年的地租却是106斤。 黄西峰和其他农场职工一致要求农场管理局减少地租,最终地租改为87斤。农场管理局为了鼓励农场职工交租,甚至将卖猪交粮作为典型案例广泛宣传。 在很多职工看来,当时的大豆价格已经从1.15元每斤上升到1.7元每斤,即使交87斤大豆也是让农场有赚无赔。 “农垦的赋税太重了,”黄西峰感慨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1980年代农场改制后,家庭农场迅速发展起来。但是随着农垦地税的增加,这些家庭农场纷纷濒临破产。以前,附近农村的姑娘都愿意嫁给农场的小伙子,现在农场的姑娘却纷纷愿意嫁到附近的农村去。 1990年代中期,随着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的“社会性支出”增大,农场地租的收费标准由原来的每亩十几元,一跃上升到每亩一百元。农用物资的价格也一路暴涨,而大豆的价格却一直在1980年代中期的水平线上徘徊,加上春寒秋冻等自然灾害频繁光顾。 今年年初,黄西峰和农场职工去和农场管理局谈判时,管理局拿出巴彦农场每亩土地各项费用支出表,解释了农场的地租为何如此之高。这份费用支出表详细列出了巴彦农场的12项社会性支出费用,其中包括财务费用、劳动保险费、学校公安医院经费、营业费用、科技经费、离休人员药费支出、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医疗卫生防疫等费用。如此合计下来,一亩地的合计费用高达98.29元。 停滞的农垦改革 7月4日,59岁的东方红农场职工艾国强刚刚拔草回来,布满老茧的双手一片漆黑。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苦笑说:“我们只想把地租降下来。” 这位老实巴交的农场职工介绍,他们在2004年、2005年曾多次向上级提出合并农场,减少行政人员的想法,“这样就可以减少开支,减少地租”。不过,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回应。 其实,农垦体制的改革已经成为农业改革的一个难题。全国农垦有的属中央管理,有的由省市管,有的由地县管,有的在同一省市下又有不同的管理体制,为此,农业部曾经多次派出专家前往全国各个垦区调研。 2002年,农业部专家在黑龙江、湖南、四川和重庆等垦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研后认为:农垦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总体相对滞后。职工家庭农场大多数还没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面临的体制性障碍还很突出;作为农垦系统主体和基本单元的国有农场的整体改革尚未有大的突破,政企合一体制依然是农垦企业负担沉重的关键因素。 很多省份也曾经提出,让农垦系统政企分开,把农场行政系统交给地方管理。 1995 年底,黑龙江省在虎林县进行“还司法行政权于政府、还生产经营权于企业”的农场改革试点。不过,到1998 年6 月,这种改革试验就停止,原因在于,行政权划归地方政府后,虎林县难以承受不断增加的财政开支。 2006年年底,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农垦专业会议上表示,2007年必须进一步加快农垦管理体制改革和经营机制创新。一是进一步完善以职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二是进一步完善垦区管理体制。三是进一步推进国有农场体制改革和布局调整。四是进一步加快分离社会职能。 然而,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地方政府来说,并不愿意接受农垦的“半社会”系统,而对农垦系统来说,有了行政职能也就意味着可以继续享受国家的各种补贴政策。特别像大兴安岭这种国家直供农垦局。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王欣在今年内蒙古第9届政治协商会议上表示,大兴安岭农垦管理局仅2005年就得到中央财政各种拨款3000万元。“十一五”期间,通过中央财政预算内投资、农业部扶贫资金、国家优质粮工程投资、动物防疫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路网建设、高油大豆种子补贴等渠道,农垦区每年将得到8000万元的国家投资。 王欣在会议上还透露,2003年大兴安岭农业管理局转制成为农垦集团之后,不但摆脱了亏损的局面,还赢利数千万元。 目前,施行较多的改革模式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这也被认为是农垦企业实行政企社企分开的过渡形式。 但农场的职工并不关心这些。“我们乐于当真正的农民。”东方红农场的一位职工说。在他们心中,毕竟周围农村的村民还有25亩的口粮田。
【 新浪财经吧 】
不支持Flash
|
||||||||||